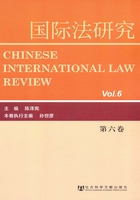
五 从与外交关系法的比较看国际组织豁免的职能性限制
在国际法上,有关职能豁免的表述本身就意味着这种豁免受到职能的限制,“职能”就意味着“职能性限制”。国际组织的职能豁免如此,外交和领事关系法中的职能豁免亦如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外交和领事关系法中有关豁免的职能标准的探讨,来论证国际法上职能豁免的限制性内涵。
虽然同样是一种职能性的限制性豁免(functional restrictive immunity),但人们对外交与领事关系法中职能豁免理论的讨论不是很多。实际上,对于职能豁免的范围的解释问题,外交和领事关系法可能会提供某种启示。对国际组织而言,职能豁免就意味着保护国际组织履行职能,在外交和领事关系法中,职能豁免就意味着使馆不受妨碍(ne impediatur legatio)和必须保障外交和领事官员完成其任务。当然,外交豁免是非常广泛的一种豁免形式,相对而言,领事豁免更接近职能性限制的标准。[36]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对两类人员作了明确区分,一类是享有完全豁免的外交官,另一类是只享有职能豁免的领事官员和执行一定外交使命的某些外交人员。但实际上,即使是享有完全豁免的外交官,其豁免亦受到某些职能标准的限制。对于不具有一定外交职衔的人员和领事官员,他们只是就其履行职能的公务行为享有诉讼豁免。[37]这被认为是一种极端限制性的豁免形式。[38]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条所列的外交职能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5条所列的领事职能,任何不符合其规定的其他行为都被认为是非职能性的,因而不能享有豁免。尤其对于非法的和侵权的行为而言,不受豁免的保护。有关联合国职员或派驻联合国的外交使团成员的间谍案,很能说明此问题。比如,在United States ex relatione Casanova v.Fitzpatrick案[39]中,美国法院认为,派驻联合国的古巴代表团成员,只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5条第2款享有职能豁免,而阴谋针对美国政府从事的破坏活动不是派驻联合国的任何使团或使团成员的职能,因而不能享有豁免。[40]在Arab Monetary Fund v.Hashim and Others案[41]中,英国上诉法院以类似的语气作出裁决:豁免的抗辩仅仅适用于公务行为。Hashim私下同意并为自己的私利而非组织利益收受贿赂的行为不属于为阿拉伯货币基金(AMF)工作的公务行为,因而拒绝其应该享有豁免的主张。[42]
外交官的豁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完全的或绝对的豁免,但事实上也受到职能方面的限制。作为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治外法权说早已不再受到推崇,代表性说也并非外交豁免的唯一理论依据,[43]而职能必要理论,即使馆不受妨碍原则(ne impediatur legatio),已被普遍接受。外交法对那些不属于职能必要而不享有豁免的行为明确列出。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1条第1款列出了这些不享有豁免的行为,即继承和商业行为不属于公务职能。与领事官员豁免的职能性限制相比,外交官诉讼豁免的例外十分狭窄且不太重要。但是,对于国际法上的豁免理论而言,人们对非职能性行为不享有豁免的基本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从前面的有关论述可以得知,外交豁免与国际组织豁免虽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甚至国际组织豁免现在依然与外交豁免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外交豁免与国际组织豁免是两种不同的豁免类型,两者之间不能进行简单的对比和类推适用。但是,在职能必要理论上,也只在这一个方面,外交豁免与国际组织豁免是具有可比性的,而且,在职能必要理论作为豁免的限制性标准方面,两者是一致的。那就是,职能必要是决定豁免的范围的标准,职能性豁免(functional immunity)即意味着限制性豁免(restrictive i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