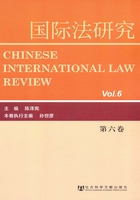
三 职能性限制是国际组织豁免发展的历史结果
从国际组织豁免的发展历史来看职能性限制,虽然可能显得冗长和无趣,却能最为真切和客观地体现出职能性限制的形成轨迹。
国际组织豁免最早出现在19世纪,在总体上一直朝着限制性豁免的趋势发展。虽然国际组织的全面繁荣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但国际组织自19世纪中叶就开始出现了。许多早期的国际组织如万国电报联盟(Universal Telegraphic Union)和普遍邮政联盟(General Postal Union)等都只处理非政治性的和纯技术性的事务。由于政治尚未介入组织的工作,成员国一般将组织的行政管理委托东道国的公务员来承担。因此这些行政联盟及其人员不需要也没有获得任何豁免。但随后国家缔造的一些具有某些政治性职能的国际组织,为了防止其落入任何特定国家的控制之下,成员国授予这些组织以管辖豁免(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21]这些具有一定政治性职能的组织在实践中一般都被授予外交特权与豁免。后来,国际联盟盟约继续采取这种方式,规定“从事联盟事务的职员得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22]从“从事联盟事务”的措辞可以看出,联盟的职员仅就其公务行为而非私人行为享有豁免,虽然这种解释始终未获得普遍接受。但有一点共识,即盟约授予联盟职员以全部的外交豁免,只是限定其适用仅仅及于职员的任职期间。
到1930年代,授予国际组织及其职员以外交特权和豁免已经演变成了国际习惯法。但是,将外交豁免适用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成员国拒绝将外交豁免授予在本国管辖下为国际组织工作而具有本国国籍的组织职员。根据传统的外交豁免理论,这是无可厚非的。外交代表不能豁免于本国的管辖,因为外交代表不能向自己的本国要求豁免。外交代表的母国保留管辖权,其目的也在于确保外交代表不会为了私人目的而滥用其豁免。外交代表的公务行为和大部分的私人行为都豁免于驻在国当地的管辖。派遣国否认其驻外外交人员的豁免,派遣国的法院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权力,外交人员必须对其私人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虽然在实践中这种责任追究机制的作用被高估了,但学者们认为,如果将外交豁免扩展适用于在其母国工作的国际组织职员,会导致这些职员对自己的私人行为完全不负责任。这种情况将造成对司法正义的否定。
因此,在与国际联盟的交涉中,瑞士认为其不能将外交豁免扩展适用于具有瑞士国籍的职员。虽然瑞士承认国际联盟盟约将外交特权与豁免授予所有的联盟职员,但瑞士主张在个人与母国之间不存在外交特权与豁免。对此,国际联盟的秘书处断然拒绝。根据秘书处的观点,管辖豁免是为了保护国际职员免受成员国的不当影响和攻击。而且,国际职员在其母国也同样要求享有豁免,因为来自其母国的不适当的压力与来自其他地方的压力是一样大的。事实上,国际职员要求他们的母国给予特殊保护,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母国的影响。[23]最后,作为权宜之计,国际联盟与瑞士达成了一个协议,即,第一类和第二类瑞士籍职员就其公务能力范围内的行为享有豁免。瑞士口头承诺,作为一个法人,国联只能通过其职员来从事活动。因此,瑞士籍的国联职员对其代表国联所从事的公务行为不承担责任。这些行为被视为组织自己的行为,受组织自身豁免的支配。
从某种意义上说,达成这个协议是国联的胜利,因为它为其瑞士籍的职员提供了某些保护。但是,瑞士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即与外交人员一样,国际职员在其母国不能享有个人的豁免。这就建立了一个糟糕的先例,即国家在授予国际公务员豁免的情况下,却可以歧视本国国民。这样,将外交豁免类推适用于国际组织已经产生了一个不良后果,即在最需要豁免保护的地方却只给予最低程度的保护。[24]简而言之,将外交特权与豁免适用于国际组织,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理论难题。[25]一方面,在国际职员与其母国之间,将产生这样的危险,即外交特权与豁免的适用使得国际职员对其私人行为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传统外交法的适用又会造成母国对国际职员施加影响,从而损害国际职员的公正地位。到了1940年代,将国家豁免的概念类推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呼声很大。但鉴于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巨大差别,使得国家豁免也不能适用于国际组织。
因此,《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避免使用外交豁免的概念,而是选用一个全新的标准,即授予联合国及其人员为保持其独立和有效履行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豁免。[26]其成果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第105条:组织在其每一个成员国内得享有达成其目的所必需之特权与豁免;组织职员得享有对其从事与组织有关的独立履行职能所必需之特权与豁免;大会得作成建议,以决定适用本条第1款和第2款之具体内容,或为此目的而向各成员国提议协约。因此,《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使得国际组织豁免成为建立在职能必要理论基础上的、一种限制性的豁免类型。根据职能必要理论,一方面,国际组织不得要求对于达成组织目的所不需要的豁免。另一方面,如果国家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则必须授予其达成目的所必需的豁免。[27]这种逻辑使得职能必要成为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基石。[28]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职能必要理论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在没有相反的条约规定的情况下,国际组织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内都享有必要的豁免。
从上述分析可知,从《联合国宪章》开始,国际组织豁免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身,即被缩减了。当外交豁免作为国际组织豁免的标准时,国际联盟与其第一类非瑞士籍的职员享有完全的外交豁免,第二类非瑞士籍的职员和所有瑞士籍的职员就其公务行为享有豁免。国联及其职员当时享有的豁免极其宽泛。但是,当职能必要理论成为国际组织豁免的基准时,联合国及其所有职员仅享有对于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豁免。可见,国际组织豁免并非获得了增加,相反,是实质性的缩小。这与国际法上的豁免日趋受到限制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这对于那些国际组织豁免的绝对性主张,是一种最好的驳斥,也符合当时各个国家的基本理性。因为经历了二战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后,从心理上讲,人们不可能愿意缔造出一个享有完全豁免而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型的国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