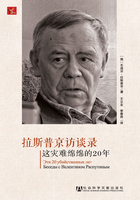
第二章 20世纪正走近末日
我们这儿是库里科沃原野,他们那儿是“奇迹发生之地”
维克多·科热米亚科:亲爱的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20世纪就要结束了。曾经,当所谓的改制正如火如荼之时,我们,您的读者,被您发表的一篇《火灾》给着实烧伤了。您将我们当时所经历的一切用一个非常准确的形象做出了概括,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您本人的心理状态。您能不能用一个同样丰富的文学形象来概括一下俄罗斯目前的状态?在您看来,20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
瓦连京·拉斯普京: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个悲剧性的而又可怕的世纪。任何一个民族恐怕都承受不了我们的人民所经历的挫折、损失、压力,我相信。不管是鞑靼的统治,还是17世纪的大骚乱都不能与20世纪俄罗斯所经历的灾难岁月相提并论。除了外部的突变和损失,更可怕的是发生在人本身——信仰、理想、道德和精神准则——的转变上。在过去的艰难岁月里这一准则从没有改变过。就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失败的德国和日本,这一准则都从未被改变过,这帮助它们很快地重返发达国家行列。受伤的民族感情——受伤的,而不是遭诅咒的,也不是被毒死的——成为激发这些国家能量的触媒。
而在我们这儿,被杀害的不仅是死者,就连生者也都被杀害了。我指的是最近十年,而且这头号杀手并非贫困——虽然贫困也“像镰刀割麦子一样”杀死了很多人。更可怕的是由于俄罗斯陷入了异常的、糟糕的环境中而使人产生的心理上的萎靡,人变得毫无价值并失去意义,到处都是破坏和不可忍受的发臭的空气。俄罗斯正在死去,人们被抛进了异质的、致命的氛围当中,毫无救赎的希望。由此滋生了各种瘟疫:自杀、无家可归、流浪、酗酒、疾病以及悄无声息的死亡——一无所有,带着心灵的哀号。
我毫不怀疑,这些是“改革者们”意料之中的事。持异见者转入了对立阵营,不停地与新秩序对抗;还有一些人对于残酷而屈辱的条件更加敏感,他们不知所措,在生命中看不到一丝光明,正在提前走进坟墓。
至于可以用什么文学形象来标志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是不能给出答案的。我想,这是因为现实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能力范围。甚至可以说,整个时代都是在生命范围之外的。这个时代只有一个形象——使徒约翰神启中的启示录。
即将结束的不仅是一个世纪,而且还是一个千年。这个千年是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千年。很快就要迎来基督诞生的第二个千年。这是多么具有历史性的纪念啊!我们今天不能不思考一下东正教的命运,在我看来,东正教现在正经受着最艰难的时期。我指的当然首先是俄罗斯。一方面,国家的无神论时期似乎已经结束了,教堂正在恢复和重建,人们可以自由地给孩子做洗礼,在教堂给年轻人举办婚礼,为死者做安魂弥撒;而另一方面……
您当然比我更清楚,是什么引发了对于我们信仰的担忧。在我看来,我们的信仰今天经受的考验要比对教会实行官方迫害的时候还要严重。比如,电视面向全国播放了在克里姆林宫宫殿中举办的“阿拉·普加乔娃[1]圣诞(!)联欢会”,这其中播出了一些完全被禁止的、撒多姆式[2]的东西。这位歌后用最下流的方式在舞台上跳来跳去,胸前还挂着东正教的十字架(!),快要结束的时候,她站在圣像壁(!)前又开始嘶喊,喊叫的内容与人类心灵最美好的情感根本无关——您说说,这究竟成什么样子呢?
要知道这只是整个肮脏、无耻、垃圾的大杂烩中的一个小片段,这种大杂烩被美其名曰大众文化,而且经常(多么可怕!)是在东正教神圣的标志下示之于众的。NTV电视台播放亵渎神灵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件事,我想,非常明显地表明,在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中在搞些什么东西,对我们在搞些什么东西。如果再加上咄咄逼人的普世教会运动,前所未有的各种教派的猖獗,对于很多人极具诱惑性的、用各种各样的迷信偷换东正教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太有必要感到担忧了。
可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国家的最残暴的仇恨者之一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3]发出了毫不掩饰的威胁。他直截了当地宣称:“现在,在摧毁了俄罗斯的共产主义之后,主要的任务转为摧毁东正教。”在我看来,之所以如此认为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和东正教虽然看上去是水火不容的,但实际上都从精神上巩固了俄罗斯:东正教——一千年,共产主义——近一百年。而且近一百年来,东正教排除万难,一直都存在于国内、存在于人们心中,甚至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于“共产主义信仰”之中。那么东正教能否承受住“民主”改革时期的各种狡猾而无情的手段,继续真正而深刻地存在呢?
是的,这是个问题:哪个对于民族精神更好些——是一个表面上宣称无神论,实质上坚守福音书训诫的无神论国家,还是一个表面上无限自由,允许任何信仰存在,而事实上却盛开着罪恶的罂粟花,不仅违背信仰,而且违背道德的自由国家呢?
这两个当然都不好。如果进入教堂的路被封闭,信徒立马变成不可靠的公民,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更坏的情况是通往教堂的路被“自由”的粪便弄脏,玷污了每个想要去教堂的人的鞋子。如果教堂爆炸了,或者受到玷污,而信徒们离开了上帝,这当然很不好;但是假如教堂楼顶上重新响起钟声,然而工厂却纷纷倒闭,失业的人没有了生计,被迫离开生命,这难道又能好到哪去吗?教堂不再荒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祈祷来寻求慰藉,这固然是好的;但要知道,与此同时,站在教堂门口乞求接济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啊。
从一个反上帝的政权中摆脱出来,教会不由自主地对反人民的政权给予了支持。教会摆脱了束缚,却受到了一切被它妨碍的人的折磨。教会就像克麦罗沃州和沃尔库塔市的矿工一样被人利用(包括在最近的总统大选中),等待教会的也会像是矿工们所得到的那样的“报答”。您说得没错:“文明的”西方社会向东正教宣战了——那么,难道那个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当局会袖手旁观吗?!总统已经废止了对数百个教派团体进行限制的法律,而这些教派首先是针对我们的教会的。他已经像头野兽那样对主教公会嘶吼,因为后者胆敢质疑皇室遗骸的真实性。现在教会更加为当局所需要了——以便安抚不幸的人们,这,或许是为了今后的加冕礼。很快就会讨论土地买卖法了。如果这部法律被通过,那么就剩下消灭民族俄罗斯的唯一障碍——东正教了。他们在想方设法地用“自由”对教会进行分裂、腐蚀、丑化。现在这项工作正干得起劲,而且会继续投入一切力量来针对东正教下手。
在俄罗斯当前所处的这个肮脏的世界,想要保持我们教会的纯洁和神圣是异常艰难的。没有哪个修道院或者保护区能够与这个世界相隔绝。但是除了东正教之外,俄罗斯人再也没有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支撑、免受污染的支柱了。上帝保佑,不要让这最后的精神支柱也被剥夺了吧。别忘了瓦·舒克申的话:“人民什么都弄明白了。”实际上当时人民还没有弄明白。这是舒克申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感。现在,一旦这个精神的维系力量被剥夺,甚至是被削弱,那就完了,就再也没有可借以凝聚的力量了。
您知道吗,有时候我会想:或许,我们真的是有些夸大其词了,或者我们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并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或者,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也许反对者对我们的指责是公允的,我们确实在煽动激愤,浓缩黑色?要知道,有很多人就算不能说是很满意,但确实很平衡、很平静。更何况比起抱怨和抵抗,忍耐似乎更符合东正教的本质和东斯拉夫人的性格……
我倒是很愿意相信,我们确实快变成职业的哭灵人了,事实上当代俄罗斯的情况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糟糕……我倒很想是这么回事,可是……看看周围就知道了。
就拿我的家乡,安加拉河上的一个村庄来说吧。现在那儿建了一个布拉茨克水库。您说,这算什么?大约40年前,我们村被从水库区迁到叶兰镇,一同迁过去的还有邻近的五个村庄。原来的集体农庄变成了林业合作社。如今这个合作社在激烈的市场战争中英勇倒下了……偌大的一个村子连一个就业的岗位都没有。商店和面包房都关张了,学校被烧毁了,柴油没钱买,电力早晚限量供应,现在恐怕已经完全停电了。但这还不算完。“海”里不能取水,因为水污染很严重,特别是汞含量超标。闹得鱼也不能吃了。邮件一个星期才送一次,有时候要一个月一次。两年前(那时候林业合作社好歹还在经营)春天的时候,我的乡亲们饿得不行,就到地里挖刚刚埋下的土豆吃。今年春天会怎样,以后会怎样,我不敢说。
处境如此悲惨的村庄又何止我们一个村呢?在安加拉河、勒拿河、叶尼塞河上有的是。这种惨烈的状况不仅仅是战争所不能比的,就是任何灾难也都没法与之相比。
尽管如此,我也不打算开始做送终祈祷。就连人在被宣告死亡之后还能起死回生了,同样的奇迹照样可以出现在国家身上。当然,若想发生这种奇迹,就必须要站起来真正地去拯救祖国,而不是去破坏它。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个非常严重(而且很迫切!)的问题。1998年年关,您祝愿“爱国的、‘第二种’的俄罗斯公民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勇气去共同坚守祖辈的疆土,保护俄罗斯家族的名誉和尊严,以便得到道德和精神上的救赎”。但是,今天还有人在“共同坚守”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广大人民是否明白需要共同坚守、需要鼓足勇气,必须为神圣而珍贵的事业奋斗?
我下面要引用的这些话,来自于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和您的新年贺词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的同一期上。这封信的作者是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20岁姑娘丹娘·奥尔洛娃,她的言语直截了当、开诚布公:“那个曾几何时雄壮、强大、坚强不屈的民族,它的骄傲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我感到心痛,因为所有人,只要不是懒得出奇,都在努力地侮辱、贬低、糟蹋俄罗斯人。但是如果深思一下的话,正是我们自己愿意让别人嘲弄和侮辱的啊。是时候停止这一切了。我一点儿也不同情那些敲着安全帽绝食抗议的矿工,以及很多很多在1991~1993年用自己的权利、名誉和有尊严的生活换来一块面包的人。那年我才14岁,但那时我就看明白了,正在发生着一些无可挽回的事情。可是,那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呢?你们在欢欣鼓舞地为叶利钦高唱颂歌吧?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你们自作自受。现在没有人会凭着良心把所有这些送还给你们。只能再次通过斗争获取——如果你们还剩下哪怕一点点的记忆、自豪和勇气。”
在这封信中类似的尖刻话很多。细想一下,这些话都是在说谁呢?人民。难道有哪个人有权利这样说人民吗?
作为这一想法的延伸,我想和您谈一谈我的一些发现。一直以来,政客骂政客已成传统。你骂他,他骂你,互相骂。可是现在,所有的政客都开始越来越多地骂人民。比方说,盖达尔一直骂人民是惰性物,导致改革不畅;而一些爱国的、反对阵营的报纸则口口声声说人民是——“绵羊”。这实质上也是在指责人民的消极和惰性,除此之外,还有指责人民近乎愚昧的极端轻信:人家赶你去屠宰场了,你还在那儿咩咩叫呢……
我们不知道人民是怎么了。现在他们成了最让人捉摸不透的了。我们对阿尔巴尼亚或者伊拉克的人民可能都比对俄罗斯人了解得更多些。一会儿我们像念咒一样带着希望叫喊:人民,人民……人民不允许,人民不会忍受……一会儿又大加指责,说人民什么都允许,什么都忍受,并且相互达成共识,判定人民已经不存在了、退化了、沉睡了,变成没有意志、一无所用的东西了。
这才是当前最危险的——痛斥人民,用不肖子孙的咒骂去侮辱人民,使“人民”这个词表现出不现实的、我们自己臆造出来的形象。最近十年,各种民主喉舌对人民的伤害和侮辱从来就没间断过。你们以为,人民会像鸭子抖掉身上的水那样轻易地忘记这些侮辱吗?不,所有的辱骂都会留下痕迹的。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只知道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对人民进行盘剥,那么试问,人民怎么可能会受到鼓舞,产生信心,变得团结?
我们需要理解人民,而所有人都背叛了人民。人民开始怀疑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原本掌握着巨大的能量——人民所创造的,然而却毫不抵抗地缴械投降了;那些威武的将军们,一边操着浑厚的男低音,用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煽情,一边像农奴时代买卖奴隶一样买卖着人民,以便夺取权力;那些来自人民的世界级名人,比如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4]和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投靠了明摆着把人民送去屠宰的当局。
那么今天所谓的人民到底指谁?我坚决不同意把人民理解为全体公民或仅仅指老百姓。人民是国家最精华的部分,是矿体,其中蕴含着上天赋予这一民族的最主要的秉性和品质。而矿岩轻易不露出地表,它总是将自己保存起来,直到在数百年的压力累积之下才适时地自然隆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不要爱我,而要爱我的……”——人民也会这样跟你说,以便检验你对人民的爱的真挚程度。这种坚守自我的生活,这看不见的堡垒,这民族生活的精神和道德的“装饰”就是衡量一个民族的尺度。
所以,不要对人民妄加指责——因为这些指责很可能与人民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人民,与总人口相比,可能数量并不多。但是,这是千挑万选的近卫军,在关键时刻能够引领很多人。但凡能被美元和承诺收买的——都被收买了;所有会背叛的——都背叛了;只要能同意过舒服而屈辱、快活而淫乱的生活的——都同意了;一切能够卑躬屈膝的——都屈服了。剩下的那些,不会离开俄罗斯,不会用任何的糖饼来交换俄罗斯。这些最精华的部分,我称之为“第二种”俄罗斯,以区别于“第一种”接受了外来的无耻生活方式的俄罗斯。我们要富有得多:在我们这儿,有库里科沃战场,有鲍罗金诺战场和普罗霍夫斯卡战场,而在他们那儿呢?只有一个“撞大运的地方”[5]而已。
说真的,要我去诋毁自己的民族我真是开不了口。对于我来说,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仍然是亲近的——虽然有其各种不足和弱点。就我个人而言,宁肯被欺骗,也不肯去欺骗人。
但这是在人际关系和个人层面上,如果事关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呢?当我和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6]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十分刻薄地,甚至是恶毒地评论道:“太容易轻信了,不是吗……您可别这样轻信啊!”
难道说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的民族性格吗?而他们,我们的敌人,可是不会客套,不懂羞耻的!他们狡猾、卑鄙、富于侵略性。或者反倒应该让我们的民族变得更加强硬,不再逆来顺受?一些人意味深长地引用基督的话:“我带给你们的不是和平,而是剑。”或许他们是对的?一些年轻的文学家批评老一辈作家——哪怕是其中最优秀的,包括您——说他们一味宣扬俄罗斯人的容忍和耐心,而不是积极地反抗和斗争,或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的?毕竟在我们的历史中,既有过谢拉菲姆·萨洛夫斯基[7]这样的苦行僧,也有过佩列维斯特修士[8]这样的战斗英雄……请您说说,您是怎么看的: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和社会需要英雄斗士吗?我想起了谢尔盖·布尔加科夫[9]的著名文章《英雄主义与苦行精神》,其中把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放在英雄主义之上。但是在当下的条件中,在我看来,二者都是需要的。
我同意您的看法:二者都是需要的,而且是互不影响的。苦行僧式的精神好比稳固而广阔的大后方,是巩固精神、逐渐排挤外来势力的必然需求。英雄主义是前线,这里进行着最直接的力量交锋。没有英雄主义,我们的民族就不会涌现优秀的个体、统帅,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0]、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1]、格奥尔基·朱可夫等。
捍卫我们神圣之物的斗争当然在进行着。也有一些精神斗士值得我们深深景仰。您就是冲在前列的一个。但是效果如何呢?当然,如果没有这些斗士的拼搏,我们所有人恐怕都已经被扔到黑暗的更深处了。但我们还是常常遭遇失望、懊恼,甚至是绝望!我指的恰恰是我们这些斗争所起到的作用,我们的努力常常会无果而终。我指的是,比方说报刊文章,这是我个人参与的。现在记者和作家的文章收效甚微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
您知道吗,我感觉,任何信念都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寻常的真理:话说三遍淡如水。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但凡长着耳朵和眼睛的人都听到和看到了。大家都分别站到了各自的立场上,政治口号已经让人腻烦了,对于社会中毫无羞耻的抢掠和下流的批判毫无效果:那些小偷和大盗,各自得手,正在得意地笑着看我们白费力气。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实干。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像你我这样的谈话只在两种情况下是需要的——要么能对局势作出具有启发性的深刻分析,要么能够给人带来希望。希望,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希望——而希望是有的,只不过需要指出来。
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并没有失去任何一个在内心深处藏有对于历史的俄罗斯的热爱,只是因为我们的宣传不够这种爱还没有被唤醒的人、公民和爱国者。爱国主义不是被灌输的,而是被确认的——如果我们连怎么用俄语思考和说话都需要别人教的话,那我们还算什么呢?我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但那个时候就已经对生我养我的故土心存感激,为自己属于俄罗斯民族而感到庆幸。想要消除这种感恩,只能把我一同毁灭。
那些抛弃俄罗斯、有意无意地与俄罗斯形成对立、与俄罗斯与生俱来的天性发生冲突的人,他们没办法不这样做。20世纪80~90年代的俄罗斯民主主义者是一个很特殊的类型,他们不是由某种信念形成的,而是由于某种毛病和故障(精神的或心理的),某种不完整、不平衡、无根基性所导致的。现在这种情况越发明显。尤里·阿法纳西耶夫[12],初始民主派的领袖之一,后来也坦承,他实际上不是建设者,而是破坏者。小有名气的维塔利·科罗季奇[13]从自己“活动”的成果中逃到美国,在波士顿大学做关于俄罗斯的讲座,题目是“仇恨作为社会意识的基本范畴”。作为俄罗斯的仇恨者,他把自己的小肚鸡肠冒充成被自己弄脏的俄罗斯心灵。这种事正常人是干不出来的。
我说这些的目的是要弄清楚,我们在和谁打交道。想一想布尔布利斯、盖达尔、科济列夫吧——这些人都如同果戈理笔下的人物!而现如今却一个个冠冕堂皇的。总统因为撒谎的声音太大,上帝只容许他说几个字,可是他竟然连这么几个字也不好好说。
说到对撒旦势力的抵抗鲜有成效,我还可以举个例子,而且完全是另一个级别的。当作为一个全国性电视台的NTV决定公开放映《基督最后的诱惑》之后,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专门向电视台的领导层发出了呼吁。可结果怎样呢?对他的呼吁毫不理睬!这还不算,当大肆放映这一亵渎神灵的电影,很多人的心灵都被深深刺痛后,牧首又向总统叶利钦和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提出请求,呼吁他们不要对亵渎全民宗教情感的事置之不理,不管这种亵渎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结果呢?在我看来,总统甚至根本没有公开回应牧首!
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连这么高层面的呼喊都变成了空洞的声音,无人回应,难道还指望我们的话能起什么作用吗?
《基督最后的诱惑》这部电影张扬的首映式是对整个俄罗斯的侮辱和挑衅。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之流对我们心灵的嘲弄,已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种挑衅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是这一次尤其卑鄙。必须承认,反抗是无力的。而NTV由于没有受到有力的阻挠,对“这个民族”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客套。
总统能怎么回应牧首呢?他没法回应。正是古辛斯基及其同伙让他当上了总统,他到死都欠着他们的,到死都要努力还债。整个权力高层都纠缠在这种关系中:一个欠着一个的,所有人都陷在彼此依赖、共生共荣的关系网中——难道他们这些人会顾得上俄罗斯、顾得上人民、顾得上人民的基督教信仰和道德情感吗!这件事已经不单单是让人气愤了,而是被深深地伤着了:要知道啊,先生们,你们就折腾吧,总有一天基督教的耐心也会到极限的。自作孽,不可活。三四年前,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私刑热,那些母亲们,不再信任那些被收买了的“人道”的法官,自己动手对玷污了她们年幼女儿的暴徒进行了审判。现在,各种工人团体,也把那些贪污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扣为人质。虽然私设刑堂并不可取,但是要让我去指责这些工人团体,我实在张不开嘴:如果国家不能保护人民的话,人民就不得不奋起自卫。至于电视台所做的——那是对所有我们的子辈和孙辈的经常性的残酷施暴。如果国家的刑法律条不能约束这些行为,那么必然会有人民的法条逐渐形成。不要太过分,先生们!这里是俄罗斯。大家应该还记得1993年,那时第一个爆发公愤的地方就是在奥斯坦基诺[14]。每个名字,据说,都有其宗教的含义。
您就说吧,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哪怕有一次被请去电视台做客了吗?除了“俄罗斯之家”之外,我没有在任何一个频道上看见过您,一次也没有。这也证明了我们的努力是多么徒劳,其成果是多么微小。电视台对于俄罗斯最优秀的作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是关闭的,关于这种状况不知说了多少遍,可是到现在仍然是关闭的。那么,今天我们这里究竟谁说了算?如何改变现有局面?而我们的人民是否希望局面得到改变呢?
说老实话,我有时会觉得,大多数人已经喜欢上了这样的电视节目。游戏、竞猜、肥皂剧、美国大片——一切都好得很。不想要别的!毒品已经渗入血液,开始发挥效力。
说到这儿,正好又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人说,共产主义培养新人的企图失败了。对于这个“新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我看来,这里首先指的是道德层面的教育,而其实质是基督教式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准则!)。可是现在呢,道德教育做得如何?我们是不是退步了太多?想想看,今天人们看的是什么,读的又是什么……话又说回来,或许人的本性本来就不喜欢福音书、普希金,或者瓦连京·拉斯普京,而更加倾向于什么“激情帝国”和“淘金热”?而我们却一直絮叨不休,想让人们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可是这些东西人们根本不感兴趣,也不需要……
我这个人比较怪,历来都不喜欢电视。即便是当年电视节目还很正统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足不出户”地去接受一切东西。看剧目就要到剧院,读书就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看足球就得去球场观赏。坐在一个发光的角落,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别人做什么,你就看什么,这不仅是反自然的,而且还有些傻气。打一开始你就应该想到,电视的巨大能量会给人带来伤害。就像有些女人水性杨花一样,有些艺术也是邪恶的,生来就是畸形。今天俄罗斯的电视节目是世界上最肮脏、最罪恶的。我早就不再看了,只是偶尔看一下新闻,而且我也不想掺和进去。
不过您说得没错:也没有人请你啊。最近六七年以来,只有两次邀请我去参加不知所谓的节目,被我拒绝了。那儿的人都是“自己人”。他们都抱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组成一个谎言和淫乱的阵营。戈培尔[15]的煽动与之相比简直就是文雅的布道;女妖五朔节[16]与“圣诞晚会”和“关于这个”之类的节目相比几乎就是圣女聚会。我都懒得再说了。
在《基督最后的诱惑》这部电影播出之后,俄罗斯作家协会决定将NTV电视台作为一个反俄罗斯、反国家的电视台加以封杀。准确点儿说,它就像是一个管子,排放着毒物和脏污。我们的封杀对于NTV电视台来说自然是不痛不痒的,本来它与我们也没有什么来往。但是,作家协会和东正教教会合在一起是可以代表一部分力量的。挑战已经提出了,挑战也被接受了,哪边会让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恶魔与上帝作战,而战场就是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是关于人生的永恒诠释。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灵魂:一个卑劣、兽性;一个崇高、神性。人向哪个妥协,他就是哪个。没错,很多人都适应了电视反刍,电视整天从早到晚填鸭式地向他们灌输东西。很多人都很喜欢。充满枪战和流血的动作片,所多玛和蛾摩拉城[17]一样的嘈杂和淫乱,日瓦涅茨基和哈扎罗夫[18]的庸俗下流,普加乔娃的乖谬越轨,“撞大运的地方”,等等。有什么办法呢?张开网就是用来捕捉那些幼稚的头脑的。我只能说:他们很可怜,不是坐在钩上,就是坐在针上。
现在已经很难对什么事情感到奇怪了。不过有份报纸上刊登的关于老鼠实验的消息还是让我印象深刻。这些老鼠学会了用爪子按按钮以获取快感。按钮控制微弱的电流刺激老鼠负责快感的神经枢纽(这种构造人有,动物也有)。这些仪器被安装在笼子里,旁边放着食物。结果,老鼠都快饿死了也不肯放下为它提供快感的按钮。你看吧,就是这么回事!
今天我们的谈话主要是关于精神和道德问题的。但是不得不同意,这些问题也经常与物质问题交织在一起。或者这么说:物质问题常常会反映出道德层面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今天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骇人听闻、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小撮巨富和一大批被劫掠一空的贫民……这样的社会难道能认为是道德的吗?您曾经说过:“今天做一个富人是一种羞耻。”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并非人人都这么想啊!有些人根本不觉得羞耻,恰好相反。“是啊,良心不纯洁的人是可怜的。”但是前提是要有良心才行,而看来却并不是人人都有良心的。
我的思绪,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常常会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俄罗斯人民自古以来就富有正义感。在我看来,这是俄罗斯灵魂最重要的特点。正是对于正义感的追求号召俄罗斯人起来反抗、闹革命。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拉辛和普加乔夫异常鲜明地反映了俄罗斯灵魂的特定方面。而现在有人正是在试图消除人民心中的正义感。就像曾经消除了我们的团结心和集体主义感一样。要知道,有些人口口声声宣传所谓的忍耐和沉默,实质上是要人们承认和默许已经确立的极端不公正的秩序。难道俄罗斯会接受这一点吗?您怎么看?
即便现在不接受,不管损失多么惨重,我也担心,再过个两三年,如果一切都没有改观,当局继续服务于别国利益,那么俄罗斯就会被强迫接受资本主义的“占领”,而到那个时候这种占领会变得更加凶狠残暴。现在就已经没有人再去考虑俄罗斯了,以后会越来越忽视它。有意识地进行自残的国家在世界上还从未有过。现在对于这个越来越衰弱的国家已经有人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们不会甘心失去俄罗斯这样一个附庸国,也绝不会让它重新回归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的。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交谈了,我常常想:图什么呢?说给谁听呢?想证明什么呢?经济学家们认为,凭目前的经济状况,俄罗斯已经撑不下去了,想要勉强维持,只能是通过掏空前几代的家底并透支本应留给后代的资源。俄罗斯像一棵小椴树一样在被人剥着皮,有“自己人”,也有外国人,而且不知道这种行为什么时候会停止。对于西方而言,开采俄罗斯的资源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有了俄罗斯,西方至少又能确保几十年的高水平生活。而数不清的家贼,像从一堆堆孽卵里孵出来的一样,彻底搬空了触手所及的一切。而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为了一小块面包,也帮他们一起搬。
他们像一群野兽,将祖国掀翻在地,争先恐后地扑上来——多么令人悲哀的情景,前所未有!
十年前那个拥有统一政权、统一经济、统一信仰的世界大国,现在想来如海市蜃楼一般。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被一帮“民主”的无赖攫取了政权,他们喜不自禁地向美国总统汇报着破坏俄罗斯的成绩。在几年时间内,世界在种族歧视主义方面扩张的程度超过了之前几十年。民族多样性和独特性借以支撑的堡垒轰然倒塌。在美洲被发现并在其上成立了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主义国家之后,攻入俄罗斯成了即将结束的千年的后半期最主要的事件。这是个大胜利,攥到手里的成果是不可能再松手的。现在西方好歹还会在意,俄罗斯内部在发生着什么?再过个两三年,就该像对待伊拉克和马尔维纳斯群岛一样对待我们了。
我们的社会现如今失去了主导的、能将其统一起来的思想。您怎样看待“自上而下”创造这一思想的努力?总统不是给一个学者团队下了命令要他们“研究出民族思想”来吗?
政府的报纸《俄罗斯日报》搞了一个最佳民族思想竞赛!您难道不认为这是荒谬的吗?
还有,我们所提到的公平难道不应该算作我们真正的民族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吗?
挑选民族思想,就好比挑选生母一样,这种荒谬的想法,只能是属于那些存心混淆视听、扰乱人心的人。实际上,当局寻找统一思想的企图是欲盖弥彰,其目的无非就是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想要全俄罗斯对其宣誓效忠。他们是不会得逞的。现在俄罗斯的两极分化已经基本完结,不仅分化为富人和穷人,而且分化为对于今天这种乌烟瘴气完全接受的人和坚决不接受的人。这种分化比1917年的阶级分化还要严重得多。
民族思想是不用寻找的,它是一直就在那里明摆着的。民族思想——这就是代表我们国家,而不是代表其他国家利益的政府;复兴和保护传统价值观;驱逐所有那些腐化、愚弄人民的人;使用俄罗斯姓名,因为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现如今被否定了的力量;适用于所有联邦主体的统一的国家赋税。民族思想——这就是停止像猴子一样模仿别人的生活方式;遏制外来丑陋“文化”的入侵;建立一种有助于而非有害于我们的历史和精神建设的秩序。革命前夕的政论家米哈伊尔·梅尼希科夫[19]是对的,他说,我们永远不可能有自由,除非我们拥有了民族的力量。我们还可以说,人民永远不可能信任国家,只要这个国家还被那些油滑而无耻的异己分子统治着!
而有些人想远离这些真理——这就是寻找“思想”的实质。政治骗子做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人民所珍视的根本性的民族思想替换为外族思想,或者将其阉割为无民族性的思想。
当今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青年,因为这毕竟是国家的未来啊。在您看来,青年受的毒害有多深?这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转变?
我的感觉是,青年恰恰还没有“离开”俄罗斯。尽管对于青年有种种诟病。即便青年真的被完全毒害了或者完全疏离了祖国精神,那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自打“改制”一开始,青年就成长在一种对祖国一切东西进行诟骂的氛围当中,而且他们既没有得到祖国的关心,也没有得到祖辈和父辈的爱护,因为这些人在忙着相互倾轧、争权夺利。
我凭什么下这样的定论?就凭我和大学生以及中学生的见面和交谈,凭我的观察;就因为青年人现在去教堂的、考大学的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人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兵役;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图书馆了。您以为,谁最喜爱“肮脏”文学,谁最热衷“肮脏”的电视呢?是那些30岁到40岁的中年人。这些人不知为什么不能坚守自己的人格。而更年轻的人却更加在意俄罗斯所蒙受的耻辱,他们心中已经在萌发对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的热爱了,尽管还不是很坚定,而且是自发的。
今天的青年已经和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更加张扬、更加开放、更加精力充沛,他们想更广阔地了解世界,这些不同有时被我们斥为另类。其实不然,他们对于不公正更加敏感,而我们却丢掉了这一良知,这个优点可能会比任何的爱国宣传都能更好地教育他们。青年人不可能不明白,电视上那些“育人者”已经无耻到了什么地步,这些人会反过来促使他们找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们的青年人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像其他很多国家的青年人在社会动荡时期所做的那样,但这也是好事,因为当鼓吹“自由”的大军在他们周围纠缠不清的时候,青年人还没有受到这些人的挑拨离间。
我再重复一遍:那些受蛊惑、被毒害、被剥离了本民族思想的青年人不在少数。但是那些完成了或者正在进行救赎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这些人几乎完全是自我拯救,没有依靠来自我们的任何帮助。这些人一定会在祖辈的帮助下,重振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