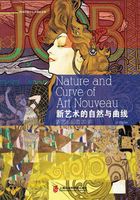
巴黎,艺术之城
说起巴黎,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浪漫。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曾在他的《欧游杂记》中这样描述他对巴黎的感觉:“从前人说‘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气,巴黎人谁身上大概都长着一两根雅骨吧。”“雅骨”,多么美妙的词语:中国古典的六朝烟水气的雅致,或许还只是浮泛在肌肤之上,而巴黎人的雅致却已是渗入到骨子里去了。与六朝的卖菜佣一样,巴黎人也是沉浸在烟水气中的,几乎像呼吸空气一样浸润在艺术的气息之中。

《梦之门II》
法国画家、设计师乔治·德·弗埃尔1898年创作的画作,采用手工彩色蚀刻工艺。
巴黎之浪漫气质的养成,既受益于法兰西民族人文精神的滋养,也得益于法兰西土地自然条件的恩赐。法国具有内陆与海岸二者兼备的地理优势,丰饶而多样的土壤条件为葱郁的植被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条件。法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公园,而巴黎则是凝聚了这个大公园中所有精华的微缩景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元素之外,巴黎还是一座鲜花之都。置身于巴黎,无论普通居民家的阳台上、庭院中,还是大小商店里和宽窄马路上,都很容易见到盛开的鲜花,嗅汲迷人的芬芳。遍布于巴黎市区的五彩缤纷的花店和花团锦簇的公园,常常令人驻足观赏而流连忘返。由鲜花所开示出的自然的气息在巴黎迷蒙散开,而自然意蕴正是新艺术思潮的内在品格之一。

插图
由法国艺术家保罗·路易斯·约瑟夫·伯顿绘制的彩色石版画,画面上绘制的是牧羊女神和鸢尾花。
巴黎不仅具有鲜明的自然风情,更具有丰厚的人文底蕴。一座城市的人文气息的涵养,往往和这座城市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关系。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探究,“巴黎”(Paris)这个词源于欧洲古代高卢部族一个分支的称谓——巴黎西人(Parisii),而根据文学史家的考证, Parisii一词又与欧洲古典文化之经典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的名字有着莫大的渊源。这些历史性的考证结果,大大开阔了我们对于巴黎的无限想象空间。关于巴黎,还存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巴黎这座城市存在的历史,远远早于法兰西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是说,是先有“巴黎西”,后有“法兰西”;先有巴黎城,后有法国。这一前一后,足足相差了两千多年。

《睡美人与罂粟》
由法国新艺术雕塑家茅里斯·鲍瓦尔设计,青铜镀金工艺搭配大理石。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生往往都与河流的存在有着必然的关联。对于法国和巴黎来说也是这样。正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黄河、德意志的母亲河是莱茵河,养育了法兰西的母亲河是塞纳河。童年时代的巴黎地区,就是位于塞纳河中间一个小岛上的小渔村。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代高卢部族巴黎西人就来到这一带聚居生息,揭开了巴黎乃至整个法兰西文明史上最初的一页。随后,巴黎便被深深地裹挟进了整个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到纪年之初,巴黎地区被罗马人所征服;大约两个多世纪之后,随着古代欧洲建造技术的发展,罗马人以其强大的帝国力量为依托,在塞纳河附近开始大规模建造宫殿,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将这一段时期视作肇建巴黎城的真正开始。这座城市最初也不是叫作“巴黎”,而是被当时的罗马人称为“鲁特西亚”(Lutetia),意思是“沼泽之地”。这一名称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巴黎与水相关的地貌特征。这个名称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4世纪左右才改名为“巴黎西”。当时的巴黎只是一个在罗马的庞大势力笼罩之下的小地方,算不上是什么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在城市和人口规模上也并不值得注重。直到508年,当时新生的法兰克王国定都于巴黎,从此揭开了巴黎历史的新篇章。此后经过西欧中世纪近千年的历史进程,巴黎城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扩展到塞纳河两岸,并最终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水边》
由法国昆虫学家皮埃尔-希波吕忒·卢卡斯绘制。

胸针
法国新艺术珠宝设计大师乔治斯·福克1900年设计的兰花胸针作品,红宝石材质,珐琅工艺。
以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标志,巴黎这座城市及其文明的命运又开始随着近现代历史的变革而起起落落。既然是革命,就一定意味着对传统的破坏性背离。作为近代政治革命的结果之一,古典巴黎城市中的很多原有地名都被更换了:路易十五广场被更名为协和广场,巴黎圣母院被更名为理性堂。比遭遇改名换姓更为不幸的,是很多古典建筑被彻底摧毁:杰出的哥特风格建筑圣雅克教堂被夷为平地,以法王亨利四世(Henri IV,1589—1610年在位)和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为代表的巴黎封建时代的国王铜像都被推倒。有破必有立。在古典城市风貌遭到摧毁的同时,巴黎城也被添加了诸多新元素。大革命之后,一代枭雄拿破仑(Napoleon,1769—1821)对巴黎城进行了扩建,重点兴建了古罗马风格的凯旋门,并扩建了卢浮宫。此外还修建了大批具有浓厚古典主义风格的宫殿、大厦等。由此可见,这场法国革命并非一味地否弃传统,对于拿破仑来说,古典与革命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端。

台灯
由法国新艺术雕塑家茅里斯·鲍瓦尔设计,青铜镀金工艺搭配模制玻璃,曾在1903年在巴黎的艺术沙龙上展出。现藏于美国纽约麦克洛画廊。

《面纱》
法国象征主义画家路易斯·韦尔登·霍金斯创作的纸上蜡笔作品。
近代的法国似乎与革命总有着难解的牵连:1789年之后,法国又历经了1830年和1848年两次大革命,而革命活动的主要发生地都在巴黎。由于战事频仍,到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1852—1873年在位)时期,原有的巴黎城已经破败不堪。时任塞纳大省省长、巴黎警察局局长的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1809—1891)受命对巴黎进行大规模改造。这次更是彻底,很多古城墙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现代样式的街道,巴黎旧城区开辟了许多笔直的林荫大道,此外还建设了为数众多的新型广场、公园、住宅区、医院、火车站、图书馆、学校、公共喷泉以及街心雕塑等设施。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改造还充分利用了巴黎地下矿物地质结构的天然条件,建造了结构复杂而性能卓越的城市给排水系统。对于巴黎人来说,这些公共设施的改造和建设,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改变,更是生活方式的更新;对于巴黎城来说,这次改造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告别古典走向现代的响亮序曲。但不久之后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随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使得巴黎城再次遭到大规模破坏。尽管如此,此时的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现代之音”已经基本完成了序曲阶段,准备转入到高潮的乐章了。我们对于巴黎新艺术运动的关注,也主要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海报
法籍瑞士裔画家菲利克斯·爱德华·瓦洛顿1896年为“新艺术之家”所做的海报,彩色石版画,高65厘米,宽45厘米。
1889年,为了纪念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法国政府决定在巴黎举办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博览会,以彰显法国自近代革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作为与举办这场博览会同步的配套项目,法国政府决定在巴黎修建一座纪念性建筑,为近代的法国精神树立一个标杆,这就是后来成为法国国家标志和巴黎地标性建筑之一的埃菲尔铁塔。此外,与上述举动相类似,在埃菲尔铁塔建成之后,法国为了迎接于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又一场世界博览会,又大力改造了巴黎地铁。无论是这两次世界博览会,还是埃菲尔铁塔,抑或是巴黎地铁,都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新艺术运动的重要标志,它们一起构成了新艺术理念和艺术实践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邪恶之音》
法国画家、设计师乔治·德·弗埃尔1895年创作的布面油画,高65厘米,宽59厘米,现由私人收藏。
如果说到巴黎的标志性建筑,至少有两处是为人所熟知的:一是凯旋门,一是埃菲尔铁塔。前者是典型的古罗马风格建筑,后者则是典型的新艺术风格的重要作品。埃菲尔铁塔是以其设计师的名字命名的。埃菲尔能以巴黎铁塔而传名于世,其中也颇有几分别样的意趣。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1832—1923)本是一名桥梁工程师,一般来说,桥梁的结构形态是横向跨越,沿着地面的二维向度展开的,但高塔却大大不同,它是脱离了地面的二维向度而沿着竖直的纵向维度伸展的。因此,无论是对审美意趣的研判,还是对力学问题的处理,在桥梁与高塔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饶有意味的是,以桥梁设计作品而为业界所认可的埃菲尔却不是由于他的本行桥梁设计,而是由这座巴黎铁塔的横空出世而名闻天下的。不过,除了巴黎铁塔之外,他还参与过另一个世界闻名的建筑设计,那就是矗立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自由女神像。
巴黎铁塔肇建于1889年,距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无论就其构造规模之宏伟或其艺术特征之鲜明来说,它都堪称法国所有新艺术风格作品中最为辉煌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巴黎铁塔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品,它是物质文明的一种彰显;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座铁塔却又算得上是一个顶级的艺术品,它的品格是真正的“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物质精神复合体,在其中既能见到世俗之欲望,也能见到神圣之信仰。我们在这里虽然将之界定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新艺术风格作品,但换一个角度对其作出另一种界定似乎也无不可:巴黎铁塔有着浓郁的哥特意味。铁塔总高达300多米,其主体结构由4根与地面成75度角的巨大弧形支柱支撑,成抛物线形架起高耸的塔身直入云天。铁塔的“身体”虽然极为庞大沉重,但看上去却不感觉笨拙,且反而透露出十足的轻灵,法国人给它起了个非常贴切的雅号——“云中牧女”。而事实上,巴黎铁塔所消耗的金属建材之多是建筑史上所罕见的:全塔共用巨型梁架1500多根,配备大小铆钉250多万颗;铁塔总重量达8000多吨。巴黎铁塔作为一种“文明的标杆”,其含义不光限于精神和艺术层面,还包括了物质和技术层面:它雄伟地象征了现代科学文明、机械威力与艺术创新思维的相互承认与和谐结合;它一方面诉说着一种艺术风格的更新,另一方面也昭示着作为一种文明特征或生活方式的钢铁时代的来临。

图纸
这是茅里斯·克齐林最初对于铁塔的构思草图,图中不但构建了铁塔的外形,还对铁塔与其他建筑之间的比例关系给出了标注。

埃菲尔铁塔
法国建筑设计师埃菲尔杰出的新艺术风格作品,建于1889年。铁塔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得极佳的声誉,后来俨然成为法兰西精神的象征。图为铁塔最初矗立在巴黎时的情景。

招贴画
法国画家皮埃尔·勃纳尔1894年为《白色评论》所作。现藏于英国布莱顿艺术画廊和博物馆。
埃菲尔铁塔的成功矗立,对法国人来说具有双重价值和意义,一是它为法兰西建立了一座丰碑,同时也是一个坐标:丰碑的意义是为了向别人展示自己,坐标的含义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如果说博览会是这个坐标的横轴,那么建筑物就是这个坐标的纵轴;如果说举办一场博览会是一种具有时间局限性的纪念形式,那么建筑物就是一种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而具有恒久含义的纪念形式。
关于铁塔的设想,并非最初就有的。对于这座纪念性建筑应该为何物及何种样式,官方筹委会的最初想法是:建造若干个古典风格的建筑单体,最终共同组成一个包括雕像、碑刻、园林等形态在内的组合式纪念群落。1886年5月,巴黎世博组委会就上述两项活动进行设计方案的招标。设计师埃菲尔作为桥梁建筑师也参与其中。在为数众多的设计方案中,最终是埃菲尔拔得头筹。他的方案是建造一座全部由金属构成的凯旋高塔。对此,埃菲尔特别强调“金属”和“凯旋”两个元素所代表的含义:高塔既是在精神上与巴黎的凯旋门相呼应,又是以钢铁技术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力量的象征,以“金属”和“凯旋”两个元素的结合,来彰显法国近代以来的人文成就和科学成果。他认为这座样式独特的金属凯旋塔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必定会给人以独特的艺术审美和视觉震撼。它不仅象征着机器文明的巨大力量,还可以使巴黎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见,因而有效地助力于法兰西精神自我认同的增强。

面具
法国雕塑家让·迦利斯创作于约1890—1892年,陶瓷质地,上过盐釉。迦利斯1875年起制作了大批历史人物的陶瓷头像,此为其中之一,面部表情甚为生动。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巴黎铁塔结构异常复杂,但却是“杂而有章”。都说擅长于精密机械设计与制造的德国人做事“严丝合缝”,深具浪漫情怀的法国人则凡事不太讲究严格性和精确性,但这一认识在这座铁塔的建造上却并不适用。或许埃菲尔是一个具有德国人严格缜密特性的法国人,他为这座铁塔共绘制了6000多幅工程图,涉及铁塔的18038个部位。建造铁塔所用的每一段金属材料,都是依照严密的计算,根据图纸提前精确制造的,然后再根据图纸作出严格的编号,最后再在工地现场一点一点地组装。一根根沉重的金属部件被液压装置提升到合适的高度和位置,再由高空人工安装烧红的铆钉,挥舞铁锤一锤一锤铆接固定。1888年春天,当作为主体结构的4根倾斜塔柱支撑开始合龙,据说塔身上的所有孔洞竟然都相当精确,以至于铆接时都不用锉一下就可完全契合地对接起来。对于这样的庞然大物,在组装之前能事先计算到如此精确的程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屏风
由法国画家、设计师乔治·德·弗埃尔设计,采用金属丝镶嵌工艺。
在现代艺术门类中,有一种类别称为“装置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铁塔就是一个最为壮观的现代主义装置艺术作品。它的建成所彰显的含义是多维度的。它在早期设计、技术分解、零件标准化和整体组装等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经济而有效的高超技术和方法,显示了资本主义初期工业文明的强大威力。同时,这座铁塔还显示了在法国人的浪漫情趣之外所深藏的丰厚的创新魄力。有艺术评论者认为,巴黎铁塔是“在不和谐中探究和谐,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它对于19世纪末新艺术思潮与实践的意义,决不能仅仅肤浅地从塔尖到塔基那4条宏大的数学曲线(支撑铁柱)中去寻找,也不能从塔身上由当时的新型技术所锻造出来的图案花样中去总结。它已经突破了技术层面和艺术层面的含义,成为一种新型文明的宏大表征,代表着当时欧洲所处的由古典和近代向现代过渡与转换的特定时期,以及与此相应的人类精神的高度与品格。
黑格尔曾经说,历史进程的本性是“狡黠”的,意思是说,人在一时一地对于事物的认识往往是难定的,只有经过折冲反复之后方能获取现象背后的理性和逻辑。这一论断似乎也可用来解说人们对于巴黎铁塔的历史性认识过程。
巴黎铁塔的建造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埃菲尔的思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早在其设计方案出炉时就遭到了诸多业内人士的尖刻批评。不仅业界专家和普通民众,还有文学艺术家们敏锐而顽固的立场,都发出了反对之声。反对的声音如此之众,以至于英国《泰晤士报》等外国媒体也参与到争论中来,这倒提前应验了埃菲尔对于建造该铁塔的意义的期待:它还没开始动工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事件。反对者质疑的焦点是:巴黎的精神是这样的吗?革命的特质就是高高在上的征服吗?法兰西的浪漫精神与死板的金属高塔合拍吗?

《苦恼》
法国画家、设计师乔治·德·弗埃尔创作于1897—1898年,是当时许多以自然作为情色载体的绘画作品之一,表现了波德莱尔式的理想女性成为邪恶的化身。

花瓶
法国艺术家道姆兄弟设计的玻璃花瓶,鸢尾花纹样也是新艺术运动中艺术家偏爱的主题,现藏于日本。
关于巴黎铁塔的轰轰烈烈的争议,对于巴黎所要举办的世博会来说无疑是一次极佳的广告宣传。1889年3月31日,随着铁塔主体建筑部分的完工,设计师埃菲尔与世博会高官一起登上塔顶,发射21响礼炮以示庆祝。随后由埃菲尔亲自升起了一面法国国旗,并庄严宣告:现在世界上只有法国能让她的国旗飘扬在300米的高空。巴黎铁塔为法国世博会带来了无尽激情与滚滚财源。我们甚至可以这么发问:如果没有这座巴黎铁塔,这场博览会是否还能看上去如其所是的那么成功?1889年5月6日,随着巴黎铁塔上的一声炮响,世博会正式开幕了。展览会期间的每天早晨,都会在铁塔上鸣放礼炮,晚上则在铁塔上打开五彩灯光——电灯的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1847—1931)本人就参加了这届博览会。巴黎铁塔不仅成了世博会上的一道亮丽景观,更俨然成了巴黎人都市浪漫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登上铁塔一睹巴黎全貌成了巴黎民众和世博会参与者们的重要活动,成为一种时尚。

角柜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埃米尔·伯纳德与高更于1888年联手设计的家具,主体为木质,以雕刻和漆彩的手法述说宗教的话题。现由私人收藏。
尽管在铁塔光芒的比照下逊色了很多,但这届世博会仍被视作当时新艺术思潮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据统计,总共有200多万人次参与了这次盛会,在当时堪称前所未有的盛况。在同年11月6日的闭幕仪式上,世博会明星爱迪生用他的另一新发明——留声机,播放了提前录制下来的埃菲尔宣布闭幕的声音,以此作为博览会的闭幕节目。
由于在世博会上获得广泛好评,巴黎铁塔所面临的反对意见遂从此逐步减少。人们开始以冷静的态度看待巴黎铁塔,重新对它进行价值评估。这座铁塔着实融合了许多在当时难以明确界定的新型建筑元素,其大胆独创的造型所蕴含的直冲天穹的力量,在张扬中充溢着浪漫和轻盈,当时没有哪一种艺术理论能够对这一切作出一个确切的定义或解释。它作为一种实用美学作品,在满足人们审美意趣的同时,后来也起到了多方面的实实在在的作用:它既是法国广播电台的中心,又是气象台和电视发射台,在战争期间,还曾经作为电话监听台截获过德军的重要情报,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贡献。岁月荏苒,百岁铁塔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它的时尚之美,它浪漫的丰韵和张扬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威力早已成为法国内在性的标志。

《秋》
法国象征主义画家路易斯·韦尔登·霍金斯1895年创作的布面油画作品。

巴黎地铁入口
吉玛德所设计的地铁作品中,被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如下三个站点:阿比斯站、道菲门(王妃门)站和夏特雷站。
巴黎的美学意趣与世态繁华不仅仅体现在地面上,也体现在地面下。如果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给人以崇高感,那么巴黎的地铁则给人以悠远感;埃菲尔铁塔所隐喻的是某一种纵向的精神维度,巴黎地铁所隐喻的则是另一种横向的精神维度。如果在别的地方乘坐地铁,也许你感触最深的只是方便快捷,但在巴黎乘坐地铁,除了方便快捷之外,给你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它的审美意趣。毫无疑问,地铁是巴黎所有公共设施中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也许有人会问:地铁还能被赋予丰富的艺术含义吗?我们要说:是的。对于艺术家和设计师而言,这个疑问本身就不是一个真命题,因为在艺术家的眼中,生活无处不需要艺术,生活无处不是艺术。地铁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设施,当然需要投入深度的艺术考量。
巴黎地铁的诞生和人们对地铁的审美意趣的提升,是和欧洲近代生活方式的更新紧密相关的。经由19世纪末期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生活方式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已经成为欧洲各大城市发展的总趋势。在当时,诠释现代性之雏形的文明含义的重要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机械动力的广泛使用,对城市中人们的活动方式来说,动力的改进促进了铁路和地铁轨道的建设;二是对生活节奏快速化和便捷化的要求。一般来说,上述两个方面都纯属实用范畴,与艺术审美的关系不大。但是对于深具浪漫情趣的法国人来说,无论是动力技术抑或是对便捷性的追求,都并非与审美意趣截然对立,这正如宽泛意义上的实用性并不与宽泛意义上的艺术性相背离一样。巴黎地铁就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它正是融实用性、便捷性、美观性、艺术性于一身的艺术典范。
虽然上述艺术与生活之关系的理念一般来说是无分国界的,因而是由各国所有艺术家和设计师们所分有和共享的,但是将这种理念落实于实践,却又是法国做得最为到位,毕竟在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很难发现对于地铁设施所做的如此精致的艺术设计。
在法国建筑师赫克托·吉玛德(Hector Guimard,1867—1942)所设计的地铁作品中,被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如下三个站点:阿比斯站(Abbesses)、道菲门(王妃门)站(Porte Dauphine)和夏特雷站(Chatelet)。这三者之中,又以位于巴黎著名的艺术活跃地带蒙马特区(Montmartre)的阿比斯站最受人们喜爱。这里的地铁出入口与周边浓烈的艺术氛围以及巴黎老城的古典气息融为一体,如同一幅绝美画作中的神来之笔。这个地铁站口的栏杆和主体框架都是由生铁浇铸而成的,在造型上主要采取了蔬果的纹样,以及由透明的玻璃和锻铁制作而成的坡面顶棚,下部两端上翘形成一个M造型,其前端坡顶则微微地倾向空中。巴黎市后来所建的地铁出入口和标牌设施,大致都是对阿比斯站出入口经典样式的模仿和改造。1970年,阿比斯站出入口被列为法国一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