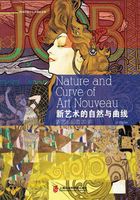
历史意识的崛起
历史主义是19世纪以来艺术人文理念的一个重要尺度。在工业文明得到迅猛发展之前,人类社会基本上处于封闭性的生产和生活状态,社会结构长期稳定而缺少变化和革新意识,任何一个地区不但与外界甚少关联,就是对本地区域内部而言也很少与过去的经验产生关联。但19世纪末陡然出现的现代社会模式改变了这一切。在一种急速变化的生活状态中,“历史”成为文化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不仅生活在单单属于某一特定时间节点的“现在”之中,同时也生活在虽然已经逝去但依然与现在关联切近的“历史”视阈之中。这种文化意识也反映在艺术家们的思维和实践中,他们试图以历史元素来表述现代意识,以现代意识反观历史问题,在现代与历史之间嫁接其精神的桥梁。
在此,我们可以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新艺术之“新”作出进一步的丰富和补充。这一角度上的新艺术之“新”,至少可以包含如下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实在”之新,二是“观念”之新。
所谓“新实在”,是说19世纪晚期的艺术家们所生活的历史时空环境,相对于以往而言发生了深刻的物质技术变革;所谓“新观念”,是指在上述大历史背景下人们的人文精神内在地发生着线性扬弃与横向更新。这里对新艺术之“新”所作的一分为二的理解,不仅仅是一种“量”上的丰富和补充,实际上也涉及对艺术本质的一种界定:实在性与观念性问题,历来是人类最深刻的哲学思考中最突出的课题,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于“存在与虚无”的命题。这些课题不单单是哲学家们的专有领域,也是艺术家们的深层次领域。如果说学院派哲学是试图以理性和逻辑的方式对这些课题作出探索,那么艺术和艺术家们就是试图以感性和映像的形式对同一命题作出回应。

《菲利克斯·菲涅恩画像》
法国画家保罗·西奈创作于1890年的布上油画,表现的是关于男性人物的另类肖像。艺术的更新,首先在于对人自身认识的更新。现由私人收藏。
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强调新艺术之“新”的同时,也要承认艺术精神中的“旧”元素对于新艺术精神所起到的前缘性奠基和背景性支撑的作用。根据德国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等人的艺术现象学理论,人类的任何思维认识和解释活动都必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语境笼罩效用的束缚。事实上,作为告别了蛮荒状态的文明社会之人,从其落地初生之始便已被“置入”到历史语境当中,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事先选择或事后挣脱的。哲学家们将人类的这种境况称为“被弃入世”的无奈境地,一个“弃”字道出了其中的命定与凄凉。哲学命题的含义是普遍性的,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家——他们作为人——也必然是“被弃入世”的,由不得哪一个人自由选择。然而艺术家与非艺术家的区别并不因此而抹煞:前者由于能够意识到其天生被抛弃的处境而能有意识地力求以最多的可能性来反观世界,并进而力求突破这种被动的束缚;后者则一般来说普遍缺乏此种意识。这就是艺术对于人类终极精神的意义所在。

《海葵》
德国博物学家厄内斯特·海克尔的著作《自然的艺术形态》中的插图。原作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壶》
法国画家保罗·高更的陶艺作品。创作于1886—1887年。采用红褐色陶土和彩色上釉手法。现藏于丹麦哥本哈根丹麦装饰艺术博物馆。

《奥菲莉亚》
法国画家奥迪隆·雷东1900—1905年创作的粉彩作品,是以象征主义手法创作的传统题材作品之一。
如上所说,新艺术精神与历史的关系并非纯粹的否弃关系,也不是单向的背离关系。在“新”与“旧”之间向来就不能划分出截然清晰的界限。投身于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在吁求新的历史存在形式的同时,对过往的历史也抱有宽厚的自由开放态度。然而宽厚并不意味着批判精神的萎靡。新艺术活动者们能够意识到深入历史资源之中萃取其所需所爱元素的必要性,但他们更有着在深度涵泳之后进而奋力发掘一块精神新大陆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