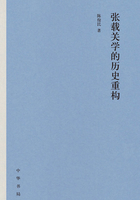
二、关学研究的“精神家园”
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秋季,在张岱年会长指导下,由于汤一介、萧萐父、庞朴、方克立、金春峰等学者的全力支持,我主持在西安成功举办了“全国中国哲学范畴学术讨论会”,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至今唯一一次有海外学者参与的“中国哲学逻辑范畴研究”全国性学术高端会议,会后结集的论文集《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是明证。2006年,我为汤一介八十华诞撰写的纪念文章《既开风气也为师——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启示录》,详细论述了这段被认为“具有现代学术史价值”(1)的亲身经历。今天回顾这段“范畴研究”的历史,可以说它同“关学论争”一样,虽以学术争辩的形式出现,其实背后都明显地存留着“唯物—唯心”、“理学—反理学”对立斗争的政治思维阴影。正是在这两次具有独特意义的学术论争中,我自身已处于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学术群体”之中,这就形成了我尔后朝夕与共而“相忘于江湖”的“精神家园”。1997年在新加坡“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上,我同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的唱和诗,就是这一时期最好的见证,我吟:“十年沉寂西湖畔,学界相交结善缘。年年相逢笑谈日,精神何处是家园?”李和道:“昔年结友长安道,重聚星洲亦有缘。西子湖头韬晦日,应知随处是家园。”(2)
1985年夏,国家教委(今教育部)以不公开组团的形式,首次派遣以汤一介为“团长”、我和萧萐父为成员的“中国哲学代表团”,应邀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参加“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这是“文革”后中国哲学家正式参加“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学术活动的开端,我集结了五年关学研究的成果,向大会提交了《张载关学导论》专著,这是我负责创办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的“内部试行”本,我万万未想到国外学者对这种“区域文化”专题研究,甚至比一般“通史”、“通论”性研究更有兴趣,且倍加赏识。记得当时大会主席、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柯雄文(Antonio S. Cua)教授还特别索要一本送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费城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中之《张载》一书,还将它列入“主要参考书目”。这促使我于会后尽快作了修订,于1986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以“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为书名正式出版,并列入当年香港书展书籍。随后,台湾学生书局以“张载哲学与关学学派”为题,列入“中国哲学丛刊”第26册,相继又出了“增订本”。张岱年、张恒寿二位前贤还为本书作“序”写“评”,称它是“近年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是“一部创见迭出的理学史专著”(3)。陈荣捷先生读了拙著后,从匹兹堡特地托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友人(王煜)带给我充满期待的勉励书信,并以他的《传习录详注集评》回赠。就在同年,张岱年先生提名推荐我给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生讲习《正蒙》,并把他收藏的雍正本《正蒙初义》赠送我研读,寄希望于我整理出新的《正蒙集释》标点本,这正是《关学经典集成》读本第二册“正蒙集释”卷编纂之缘起。由此我真正感受到,中外前辈学者给予后学从事“关学”研究的殷切厚望和同情理解。这种一世难得的学术鼓励和真诚友谊,便成为我以后继续关学研究的精神动力。
从1986年起,我除经常受邀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会之外,还先后长期或短期以“客座教授”、“高访学者”的身份讲学、研究、访学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和美国哈佛、斯坦福、耶鲁、夏威夷、普林斯顿诸大学,以及德国慕尼黑、特里尔、马尔堡、哥廷根等大学,从而比较广泛地结识了海外一大批学界同行友人,不知不觉又营造了我又一海外“学术群体”。正是这些内外“学术群体”友人之间的经常交流,给我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不断唤起我学术创作的灵感,激发着我的求知探索欲望,促使我自觉置身于学术研究的前沿,始终不敢懈怠。也促使我不断汲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得”的学术路径。
(1) 孙尚杨:《如切如磋,砥砺相生》,《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1期。
(2) 李锦全:《思空斋诗草》,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41页。
(3) 《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张岱年“序”;张恒寿、马涛:《一部创见叠出的理学史专著——读〈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