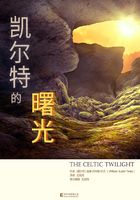
第11章 尘埃合上了海伦的眼
一
我最近去了戈尔韦郡吉尔达坦教区的一个小居民区,那里房子很少,少得不足以称为一个村落,但它的名字巴里利在整个爱尔兰西部却名闻遐迩。那里有座方形的古老城堡,巴里利城堡,城堡里住着一个农夫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住在一间村舍里,那里还有一个小磨坊,里边住着老磨坊主,老柳树在小河和巨大的石级上投下浓绿的阴影。去年我去了那里两三次,和磨坊主谈到比蒂·厄利(一个几年前住在克莱尔郡的聪明女人)说过的话:“在巴里利的两个磨轮之间有一种抵抗万恶之药”,我想从他或者其他人那里知道她指的是流水之间的苔藓还是其它什么草药。今年夏天我去过那里,秋天来临之前我会再去那里,因为玛丽·海恩斯,一个美丽的女人,六十年前死在那里,她的名字至今依然在篝火边的闲谈中被啧啧称叹。我们总是愿意徘徊在美丽的生命曾经悲伤地驻足的地方,以让我们自己明白至美和这个世界天生无缘。一位老人从磨坊和城堡那里带我走了一会儿后,便走下了一条狭长小路,小路几乎淹没在黑莓和刺李灌木丛中,他说:“这是那座房子残留的一点老地基,但它的大部分用来建墙了,山羊一直吃长在上面的灌木,直到把它们吃得再也不长了。人们说她是爱尔兰最俊美的女孩儿,她的皮肤像飘落的雪花一样,”——也许,他是想说她皮肤雪白——“她的脸颊上有两朵桃花。她有五个英俊的哥哥,但现在都不在了!”我和他谈起了爱尔兰著名诗人拉夫特里用爱尔兰语写的一首关于她的诗,诗中有一句“巴里利的酒窖坚固无比”,他说,那个坚固的酒窖是河水沉入地下的一个大洞,他把我带到一个深水池旁,一只水獭在一块灰色的巨石下仓惶跑开,他告诉我,许多鱼在清晨从黑暗的水中浮上来,“品尝从山上流下的清泉”。
我是从一个住在河上游大约两英里处的老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这首诗的,她记得拉夫特里和玛丽·海恩斯。她说,“我从没见过像她这么俊美的人儿,这辈子我也不会再见到了。”而拉夫特里几乎完全失明了,“没有生计,只好到处游走谋生,他以房子作标记指出要去的地方,然后所有邻近的人都会聚到那里聆听。如果你善待他,他会赞美你,如果你不善待他,他会用爱尔兰话挖苦你。他是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如果他刚好站在灌木丛下,他会为灌木丛即兴作歌。有一次他站在一片灌木丛下躲雨,他吟诗赞美它,过了一会儿,当雨水从灌木丛中流下时,他又作诗贬斥它。”她用爱尔兰语给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吟唱了这首诗,她唱得字字清晰流畅而且意味深长,就像那些在音乐盛气凌人地喧宾夺主之前的老歌那样,它的韵律随着歌词的气势而起伏波动。这首诗并不像上个世纪最好的爱尔兰诗歌那样自然,因为它的思维方式明显地过于传统,所以,那个贫穷半瞎的可怜老人听上去像是一个阔绰的农夫向所爱的女人呈献所有最好的东西,但它的语句天真无邪而且柔情似水。和我在一起的朋友翻译了这首诗的一部分,其它部分是乡民们自己翻译的。我认为它比大多数其它的翻译更具有爱尔兰诗歌中的那种简朴。
遵从上帝的旨意去做弥撒,
那一天风雨交加;
在吉尔达坦十字路口,我遇见玛丽·海恩斯,
我即刻一见倾情地爱上了她。
我亲切有礼地向她问安,
人们说她本人就是这样的友善;
她说,“拉夫特里,我从来为人简单,
你今天就可以到巴里利来饮酒用餐。”
听到她的提议我毫未迟疑,
她的话令我欢心不已。
我们只需走过三片园地,
黄昏前就会到达巴里利。
桌上摆出了酒杯和美酒一夸脱,
她坐在我的身边,秀发令人着魔;
她说,“喝吧,拉夫特里,一百个欢迎你,
巴里利的酒窖坚固无比。”
哦,星光!哦,秋收的太阳!
哦,金发!哦,我的世界的耀眼之光!
你可愿在礼拜日与我共聚,
直至我们在众人面前誓言不弃不离?
每个礼拜日的夜晚为你歌唱是我的心愿,
潘趣酒或葡萄酒任由你选;
啊,荣耀的上帝,清除我面前的泥泞沟坎,
让我抵达巴里利一路平安。
当你从山上俯瞰巴里利,
山坡上有股甜蜜的气息;
如果你在山谷间采摘坚果和黑莓,
你会听到仙人的音乐和仙乐中的鸟语。
还有什么值得视为伟大,
当你沐浴在身旁这朵鲜花的光芒之下?
世上没有神灵可以将它否认或掩藏,
她是天堂的阳光,令我承受爱情的创伤。
我游遍了整个爱尔兰,
到过所有的河流和山川,
甚至深藏不露的格蕾湖畔,
我从未见过美人如此令人惊叹。
她娥眉闪亮,秀发耀眼;
她面如其人,嘴巴甜蜜而和善;
我向她献上橄榄枝,以她为傲,
她是巴里利的鲜花,闪光的荣耀。
她就是玛丽·海恩斯,一个沉静随和的女人,
她不仅貌美而且心纯;
即使一百个舞文弄墨的人,
也描绘不出一半她的美丽绝伦。
有一个老纺工(人们纷传他的儿子在晚上会到仙人之中)对我说:“玛丽·海恩斯是有史以来最美的人儿。我母亲过去常常告诉我关于她的事情,她喜欢曲棍球,一场都不漏。无论她去哪里,她总是一身洁白。有一次,一天之内就有十一个男人向她求婚,但她一个也没答应。一天晚上,吉尔比坎地那边聚集了很多男人,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谈论着她,其中一个人站起身,决定立即前去巴里利拜访她;但是那时候克龙沼泽地正张着深口,当他经过那里时,他掉了进去,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而她在大饥荒前的那场伤寒中死去了。”另一位老人说,他见过玛丽·海恩斯,他那时还只是个小孩子,但他记得“我们当中最强壮的一个人,一个叫约翰·马登的小伙子,为她送了命,他因为夜里渡河去巴里利得了伤寒。”这也许和前面那个老纺工讲述的是同一个人,因为一件事情会在传说中演绎出多种不同版本。在埃奇奇群山之间的德里布里恩,有一位老妇人也还记得她。这片荒芜辽阔的土地,景色依然犹如古老诗歌中的描述:“埃奇奇寒冷山顶上的雄鹿听得到狼的哭嚎”,而它也依然传承着许多诗歌和古语的庄重。她说:“太阳和月亮从来不曾照耀到一个如此俊美的人身上,她的皮肤白得泛蓝,她的脸颊上有两朵小小的桃花。”住在巴里利附近的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仙人的故事)说:“我经常看到玛丽·海恩斯,她确实很俊美。她的脸颊边垂落着两绺银色的卷发。我见过淹死在那边河里的玛丽·莫洛伊,也见过阿德勒汉村的玛丽·格思里,但她让她俩黯然失色,她是一个天资丽人。我为她的葬礼守过灵——她已经看厌了这个世界。她秉性善良,有一天,我穿过那片田野回家,我累得不行,知道是谁走了出来吗?除了那朵闪亮的鲜花,还能是谁呢,她递给我一杯新鲜的牛奶。”这位老妇人所说的银色不过是指一种明丽耀眼的颜色。尽管我认识的一位老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认为这个老妇人可能像仙人一样知道“对付这个世界上所有邪恶的解药”,但是她大概从没见过金子,所以不知道它的颜色。因为住在金瓦若海边的一个年纪很轻、不可能记得玛丽·海恩斯的男人说:“每个人都说现在找不到像她那么漂亮的人了,据说她有一头漂亮的秀发,犹如金子的颜色。她虽然贫穷,但是她每天的衣服都穿得像礼拜天一样,非常整洁。不管她去参加什么集会,人们都会拼死见她一面,很多人对她钟情,但她死得太早。据说,一个人一旦被写进诗歌,就会寿损夭折。”
那些被人过于欣羡和宠爱的人,据说会被仙人带走,仙人善于利用人们放纵的感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一个父亲的溺爱——一位老草药医师曾经这样告诉我——会把他的孩子送到它们手里,或者丈夫对妻子的过分宠爱,也会让它们带走她。那些被人们欣羡爱慕的人,只有当人们见到他们的同时会说“上帝保佑他们”,他们才会安然无恙。唱这首歌的老妇人也认为玛丽·海因斯是“被带走了”,她是这样说的:“既然它们连很多不漂亮的人都带走了,它们怎么会不带走她呢?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她,也许有些人没有说‘上帝保佑她’。”一位住在杜拉斯海边的老人毫不怀疑她是被带走的,“还有一些活着的人能记得她参加圣人节时的样子,他们说她是爱尔兰最俊美的女孩儿。”她红颜命薄是因为神也爱她,仙人就是神,也许我们忘记了这个古语的字面含义,它已经预示了她的早亡。这些卑微的乡间男女,在信仰和情感上,比我们这些学者更接近古希腊的世界,他们把美视为神圣。是她“看厌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些老人们,当他们说起她的时候,责怪的不是她而是其他,虽然他们可能会苛刻强硬,但这时他们变得温柔,就像当海伦从城墙上走过时,特洛伊[23]的老人们变得温柔了一样。
那位使她名闻遐迩的诗人在爱尔兰西部享有盛名。有些人认为拉夫特里只是半盲,他们说“我见过拉夫特里,一个失明的人,但是他的视力足以看见她”,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但有些人认为他彻底瞎了,这在他生命的晚期是完全可能的。神话里的所有事物就其本身特质而言都是极尽完美的,所以神话中的盲人也当然从来不曾见过世界和阳光。有一天我正在寻找一个有人见过仙女在其中沐浴的水潭,我遇到了一个男人,我问他,如果拉夫特里完全失明,他怎么可能会对玛丽·海恩斯如此崇拜?他说,“我认为拉夫特里是个盲人,但盲人有他们自己看见事物的方式,比起有视力的人,他们有能力知道更多,感受更多,做得更多,也能猜测出更多,他们天生具有独特的机灵和智慧。”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他确实灵智非凡,难道他不仅是个瞎子,也是个诗人吗?那位之前谈论过玛丽·海恩斯的老纺工说:“他的诗是上帝的礼物,有三样东西是上帝的恩赐——诗歌、舞蹈和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一个没上过学的山民会比现在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更有学识和教养,因为那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在库尔,一个男人说,“当拉夫特里的手指触碰到他自己的头部,一切都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就像一本书一样。”吉尔达坦的一个老人说,“有一次他站在灌木丛下面和灌木丛说话,它用爱尔兰语回答他。有人说是那丛灌木在说话,但那一定是灌木里的一个精灵,它让他了解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后来灌木枯萎了,它就在从这里到拉哈辛的路边上,现在还可以看到。”拉夫特里写过一首关于灌木的诗,我还没有看过,这个传说可能就是从那首诗经由神话的熔炉炼造成型的。
人们说拉夫特里是孤独地死去的,但是我的朋友海德博士曾经见过一个在他死去时和他在一起的人,那个叫莫尔丁·吉兰的人告诉海德博士说,整个晚上他看到一束光从他躺着的房子的屋顶升向天堂,“那是陪伴着他的天使”,而且,小屋里整晚闪耀着一束强烈的光,“那是来唤醒他的天使,他们给他这个荣耀,因为他是个如此杰出的诗人,吟唱了无比虔诚的诗歌。”也许再过几年,在经过凡人神化的熔炉后,传说中的玛丽·海因斯和拉夫特里会成为“美丽的忧伤”和“梦想的辉煌与困窘”的完美象征。
1900年。
二
不久前,我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和一个小时候住在邻近乡村的男人聊了很久,他告诉我,当一个异常美丽的女孩出生在一个其貌不扬的家庭时,她的美貌被人们认为是来自于仙人,因此凶多吉少。他列举了几个他知道的美人名字,说美貌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过幸福。他说,美貌是一件既让人骄傲又令人恐惧的东西。我很遗憾当时没把他的话写下来,因为那比我记忆中的这些话生动多了。
19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