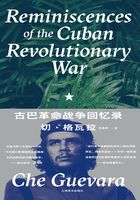
第6章 埃斯皮诺萨高地遇袭
在遭到前面所说的出其不意的空袭后,我们放弃了加拉加斯山头,打算重返我们熟悉的地区,因为在那里我们能和曼萨尼略建立直接的联系,从外界接受更多的援助,并能更好地了解国内其他地区的形势。
我们掉转头,渡过阿希河,穿过大家熟悉的地区,最后来到门多萨老汉家。一路上我们必须沿着多年人烟罕至的山脊用砍刀开辟出一条条小路,所以行军速度很慢。那些日子都是在山里过的夜,几乎没什么吃的。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就像是我一生中的盛宴一样,乡巴佬克雷斯波带来了一个四根猪肉红肠的罐头——这是他以前省下的——说他要用这个罐头款待朋友。虽然红肠数量少得可怜,可是乡巴佬、菲德尔、我还有另一个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好像在享受一顿奢侈的大餐。队伍一路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了加拉加斯山头右侧的那间茅房前。门多萨老汉为我们准备了吃的,尽管他心里很害怕,但是他身上的那种农民的忠心耿耿的品质本身就表明每次我们路过时他都会来欢迎。我们部队中的克雷森西奥·佩雷斯以及其他一些农民是门多萨老汉的朋友,门多萨老汉对我们的态度也是看在他们的情面上。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极为痛苦的行军,因为,我的疟疾病发作了,是克雷斯波和让人难忘的胡利奥·塞农·阿科斯塔同志帮助我完成了这次痛苦难熬的行军。
在那个地区我们从不睡在农民的茅屋里,但是,我当时身体极度虚弱,加上那位出了名的“加利西亚人”莫兰总是一有机会就病它一场,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同睡在一个茅屋里,其他人就在附近担任警戒,只是在吃饭时才进屋。
我们被迫缩减部队的编制,因为有些士兵士气非常低落,还有一两个伤势严重。重伤员中有现在担任内务部长的拉米罗·巴尔德斯和克雷森西奥的儿子伊格纳西奥·佩雷斯,伊格纳西奥后来英勇牺牲了,牺牲时是上尉军衔。拉米罗的膝部受了重伤,同样的部位在一九五三年攻打蒙卡达兵营时就曾受过伤,所以我们只能把他留下了。另外还有几个人也离开了队伍,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记得其中有个人神经受了刺激,动辄便在荒漠的群山里或在游击战士中间大呼小喊起来,说原来曾答应他住在食品丰富防空设施齐全的兵营里,现在却天天遭敌机跟踪,没有住的,没有吃的,甚至连饮用水都没有。他的抱怨大体上就是游击队新兵对战争生活的印象。那些没有离队的、经过前期考验的战士对这种肮脏的环境和缺食少水、没有兵营、没有生命保障的生活已经适应,对这种仅仅靠步枪、靠小股游击队内部凝聚力和抵抗精神支撑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了。
西罗·弗里亚斯带着一些新兵来了,还带来了我们今天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当时让我们感到很迷茫的消息。消息说迪亚斯·塔马约[2]马上就要倒戈,要和我们革命部队“打交道”了;还说,福斯蒂诺已经筹集了成千上万比索。总之,颠覆骚乱正在全国上下蔓延开来,政府一片恐慌,手忙脚乱。此外,我们还听到一个略带凄惨却很有教育意义的消息。几天前的逃兵塞尔希奥·阿库尼亚跑到了他亲戚家,当着他表兄弟的面吹嘘说自己在游击队立下大功,不料被一个叫佩德罗·埃雷拉的人无意中听到了,便到乡村警卫队告发了他。臭名昭著的罗塞略下士听说后便抓走了他,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后又朝他连开了四枪,看样子最后把他绞死了。(杀人凶手的身份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证实。)这件事教育了我们的战士,一定要维护游击队的团结,任何企图逃离集体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同时,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必须转移营地,因为,这个年轻的逃兵很可能在被杀前什么都供出来了,他知道我们当时就住在弗洛伦蒂诺家中。
当时还出现了一件怪事,只是后来我们核对证据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欧蒂米奥·格拉告诉我们,他前一天在梦里曾梦到塞尔希奥·阿库尼亚的死,杀死他的人竟然也是罗塞略下士。这就引发了一场持久的哲学讨论:究竟梦境能不能预测未来?对战士进行文化和政治教育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苦口婆心地向大家解释,梦里的事是不可能用来预测未来的。那么格拉做的梦作何解释呢?只能说是一种纯粹的巧合: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都认为塞尔希奥·阿库尼亚本来就该遭遇这样的下场,而他又恰好撞上了当地那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罗塞略。还是乌尼韦索·桑切斯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他暗示说,欧蒂米奥是个“爱说谎的人”。前一天,当他离开营地去搞五十罐酸奶和一盏军事用灯时,有人显然已经告诉他塞尔希奥·阿库尼亚被杀的事了。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四十五岁的文盲农民胡利奥·塞农·阿科斯塔就是一个“预感论”的坚定信仰者。他是我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第一个学生,学习文化非常努力,每遇战斗间隙,我都会教他几个字母,当时,我们正在学习元音。胡利奥·塞农学习决心大,从不埋怨自己过去底子差,总是乐观地朝前看,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今天他的榜样对许多农民、对于战争年代他的许多战友、对于了解他身世的人来说是很有教益的。胡利奥·塞农·阿科斯塔是当时我们事业又一位坚定的同伴。他干工作孜孜不倦,熟悉当地情况,始终乐于帮助有困难的游击队员,帮助城里来的还无力摆脱困境的游击队员。用大车从远处拉回泉水的是他,下雨天找到干燥的引火柴迅速生起火的是他,凡事冲在前面甘冒风险也是他。他确实是我们的队伍中样样都会干的多面手。
在欧蒂米奥的变节行为暴露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他抱怨说没有毛毯,问菲德尔能否借他一条。山里的二月正是最冷的季节。菲德尔说,自己的毛毯借给他,两个人过夜都得挨冻,不如两人盖同一条毛毯,再盖上他的两件上衣就暖和了。欧蒂米奥·格拉就这样挨着菲德尔睡了一夜,身上还带着卡西利亚斯赏给他的用来谋杀菲德尔的那把0.45英寸的手枪。他还带着两颗手榴弹,是掩护他从山顶撤退时用的。当时我和乌尼韦索·桑切斯一直紧随着菲德尔,欧蒂米奥就和我俩聊起菲德尔警卫的事,他说:“我非常担心那些警卫员,警卫工作太重要了,千万马虎不得。”我们解释说,附近安排站岗的就有三个人。我们自己,加上“格拉玛号”上的老兵以及菲德尔的贴身保镖,整个晚上都轮流换岗,保卫菲德尔的安全。就这样,欧蒂米奥紧挨着我们革命领袖的身边过了一夜,始终把菲德尔的生命置于他的枪口上,伺机实施暗杀。但是,他还是没敢下手。整个晚上,古巴革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内心的风云突变,取决于勇气和恐惧的交锋,很可能也取决于一个人的良知,或者一个叛变者对升官发财的欲望。幸亏欧蒂米奥对内心邪恶的抑制力占了上风,天亮了,总算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我们离开了弗洛伦蒂诺的家,在一个干涸了的溪谷扎营住了下来。这里离西罗·弗里亚斯的家不太远,他回家搞了几只母鸡和一些吃的回来。虽然雨下了一夜没停,大家也没有避雨的地方,但总算在早晨时得到了补偿,吃上了饭,喝上了热腾腾的鸡汤。有人说,欧蒂米奥也来过这里,他在这里来去都很自由,因为大家都信任他。先前他发现我们住在弗洛伦蒂诺家时就解释说,他离开部队去看望生病的母亲后,就看到了加拉加斯发生的情况,他尾随着我们是想看看还会发生什么其他情况。他还解释说他母亲现在病好了,当时他看望母亲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我们驻扎在埃斯皮诺萨高地,离埃尔洛蒙山、布罗山和加拉加斯山都很近,敌机经常到这里来扫射。欧蒂米奥摆出一副预言者的面孔说:“我可以肯定,今天他们一定会来布罗山扫射的。”果不其然,敌机来了,对布罗山进行了一番低空扫射。欧蒂米奥高兴得跳了起来,为他灵验的预见自鸣得意。
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西罗·弗里亚斯和路易斯·克雷斯波像往常一样外出搜罗粮食,一切都很平静。早上十点,一个叫埃米利奥·拉夫拉达的农民新兵在附近抓到了一个俘虏。此人原来是克雷森西奥的一个亲戚,在莱昂·塞莱斯蒂诺的店铺里当伙计,卡西利亚斯的士兵就驻扎在这个店铺里。他告诉我们他们那里住了一百四十个士兵。其实,从我们的阵地上能看到他们就在远处的一座荒山上。而且,这个俘虏还说欧蒂米奥和他聊天时就告诉他第二天这一地区会遭到轰炸。卡西利亚斯的部队现在已经走了,但是这个俘虏不能准确说出他们的去向。这时,菲德尔起了疑心。最后,欧蒂米奥反常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种种猜测都冒出来了。
下午一点半,菲德尔决定先撤离这个地区。我们爬上山头,等侦察员回来。过了一会儿西罗·弗里亚斯和路易斯·克雷斯波回来了。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一切跟往常一样。我们正在交谈着呢,西罗·雷东多觉得他看到一个黑影在移动,便立即招呼大家安静下来,他随即扣上了扳机。只听见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刹那间枪炮声四起,天空中弹片横飞,敌人又发起攻击了,火力集中在我们原先驻扎的营地上。我们赶紧又从新营地疏散转移。后来我才知道,胡利奥·塞农·阿科斯塔将永远安息在那个山头上了。这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知道革命胜利后还会面临艰巨的任务,为此他正在学习字母武装自己,可是,他再也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了。我们其余的人都慌忙地撤退了,我的背包原本是我最得意的、能给我带来欢乐的东西,因为里面装满了药品、储备口粮、书籍和毛毯,现在也只好扔下了。可是,我还是抓起从巴蒂斯塔政府军缴获来的一条毛毯以及拉普拉塔河战斗的战利品钢盔,拔腿就跑。
不久,我又和一群战友会合了,他们是:阿尔梅达、胡利奥·迪亚斯、乌尼韦索·桑切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吉列尔莫·加西亚、西罗·弗里亚斯、莫托拉、佩桑特、埃米利奥·拉夫拉达和雅约·拉耶斯。(还有一个人,不过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是谁了。)为了尽力避开枪弹,我们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撤退,也不知道其他同志的命运怎么样了。零星的爆炸声一直尾随着我们,要跟踪我们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撤退仓促,根本来不及掩盖留下的踪迹。当我的表指向傍晚五点十五分时,我们终于走到了林子的尽头,抬头一望,四周山石嶙峋。犹豫了半天,我们决定还是在这儿停下等到天黑再说,因为如果大白天穿过前面的开阔地的话,就会被敌人察觉。一旦敌人现在沿着我们的脚印追上来,我们的位置自卫起来也有优势。不过,敌人并没有追上来,我们在向导西罗·弗里亚斯的带领下趁天黑继续赶路。不过他带路也没有什么把握,因为他对这一地区也只是大致了解。有人建议分成两个小分队,一来行军方便利索,二来留下痕迹也少。但是,为了保持队伍的完整性我和阿尔梅达反对这么做。我们认出了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叫做利莫内斯的地方,这地方我们熟悉。由于有些人想继续往前走,队长阿尔梅达上尉犹豫了片刻,便命令我们向埃尔洛蒙山方向前进,因为那是菲德尔指定我们会合的地方。有人反对说埃尔洛蒙山是欧蒂米奥熟悉的地区,因此政府军会在那等着我们。这时我们对欧蒂米奥叛徒的身份已经没有一点怀疑了,但是,阿尔梅达还是决定服从菲德尔的命令。
在我们被打散三天以后,二月十二日我们在埃尔洛蒙山附近一个叫德雷查-德拉卡里达德的地方与菲德尔会合了。在那里欧蒂米奥的叛徒身份得到了确认,整个情况的来龙去脉也搞清楚了。事情要从攻打拉普拉塔兵营之后说起,在那次战斗中,他被卡西利亚斯抓获,敌人不但没有杀他,反而用一笔钱收买了他,让他谋杀菲德尔。我们这才知道,就是他把我们在加拉加斯的阵地的情报送给了敌人,他还下令空袭布罗山,因为那是我们行军中的一个必经之地(只不过我们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计划)。他还组织了对我们在小峡谷藏身的小山洞的袭击,但由于菲德尔命令我们及时撤退,才保全了队伍,只伤了一个人。此外,胡利奥·阿科斯塔牺牲一事也在这里得到了确认。敌人至少一人被击毙,数人受伤。我必须承认,没有一个敌人死伤在我的枪口下,因为我只不过组织了一次快速“战略撤退”。我们十二个人(除了走散的拉夫拉达以外)和队伍中的其他人——劳尔、阿梅赫拉斯、西罗·雷东多、曼努埃尔·法哈多、胡安·弗朗西斯克·埃切维利亚、“加利西亚人”莫兰和菲德尔——再次会师了,总共十八人。这就是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二日的“重新会师的革命军”。我们有些同志被打散了,有的新兵擅自逃离,还有一个名叫阿曼多·罗德里格斯的“格拉玛号”上的老战士也做了逃兵,他还带走了一支汤姆逊式冲锋枪。在他开小差前的最后几天里,只要一听到远处枪声向我们逼近,他就一脸的恐惧和痛苦。后来,我们就说他那张脸是“逃犯的脸”。所以,后来只要有人因恐惧而脸上显出我们这位“同志”在埃斯皮诺萨高地遭袭击前那些日子里同样的惊弓之鸟的神情时,我们立刻就能预感到情况不妙,因为“逃犯的脸”和游击队的生活是完全不协调的。用游击队的新口头禅来说就是,有这么一张脸的人肯定是“无心恋战”了。罗德里格斯的那支冲锋枪后来在不远的一间茅屋里被我们发现并追回了,他的两条腿倒是有福气跑得快,没有被我们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