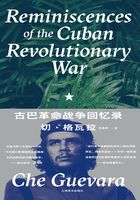
第10章 锤炼新兵
一九五七年三月和四月是起义军整顿和习武的两个月。自从在德雷查接收增援部队以后,我们的起义军就扩大至八十人左右。部队组织如下:先头部队由卡米洛指挥,下有四名战士;接下来是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的排,下有三名中尉:胡利奥·迪亚斯、拉米罗·巴尔德斯和纳诺·迪亚斯,每人指挥一个班。(这俩名叫迪亚斯的同志后来都在乌韦罗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并没有亲缘关系。其中一个是圣地亚哥人,圣地亚哥的迪亚斯兄弟炼油厂就是为了纪念纳诺和他在圣地亚哥阵亡的兄弟的。另一个是阿特米萨人,曾参与攻打蒙卡达兵营,也是“格拉玛号”上的老战士,在乌韦罗战斗中完成他最终的使命。)豪尔赫·索图斯上尉指挥的另一个排也有三名中尉,他们是西罗·弗里亚斯(后来在“弗兰克·派斯”第二东方阵线牺牲)、吉列尔莫·加西亚(现任西部军区司令)和雷涅·拉莫斯·拉图尔(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时晋升为少校军衔,后在战斗中阵亡)。接下来是总参谋部,或称指挥所,由下列人员组成:卡斯特罗总司令、西罗·雷东多、曼努埃尔·法哈多(今天是革命武装部队的少校)、克雷斯波(少校)、乌尼韦索·桑切斯(少校)和担任军医的我。
按照纵队习惯的排列顺序,接下来就是阿尔梅达上尉指挥的那个排。他手下有埃尔莫中尉、吉列尔莫·多明格斯中尉(他在皮诺德尔阿瓜战斗中牺牲)和培尼亚中尉。整个纵队殿后的是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中尉和其他三名战士组成的后卫部队。
根据我们部队的规模,现在需要按班各自开伙解决吃饭问题,粮食、药品和弹药也都按班分配。几乎在所有的班里(自然也在所有的排里)都有老战士手把手教新战士野外炊事技能,教他们粗粮细做,烧出最好的味道,教他们打背包以及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行军的技能。
德雷查、洛蒙和乌韦罗之间的山路坐车只要几小时就能跑完,但是我们要在这三地之间进行长达数月的缓慢而小心的行军训练,主要是让战士们为随后的战斗和生活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就这样,我们再一次行军路过埃斯皮诺萨高地,在不久前牺牲的胡利奥·塞农的墓地前,老兵们组成仪仗队肃立志哀。我还发现自己的一条毛毯仍缠绕在刺藤上,不免使我又回想起了那次全速的“战略撤退”。我收起毛毯装进背包里,暗下决心再也不能像那样丢掉自己的装备了。
一个叫保利诺·丰塞卡的新兵被派给我当助手,帮我背药品。这就稍稍减轻了我的工作,所以每天长途行军以后,我就可以抽出几分钟时间照料部队的战士。我们再次翻越了加拉加斯山峰,当初由于格拉的叛变,我们曾在这里和敌人的飞机有过一场不愉快遭遇。这次我们发现了一支步枪,那是攻打拉普拉塔兵营后,根据轻装撤退的要求,被我们的士兵扔下的。可是现在我们不但没有多余的步枪,反而是枪支短缺了。我们正处在一个新阶段,战争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敌人现在害怕和我们遭遇,所以整个这一带地区他们都不敢随便闯入,不过说实话,我们也不想与他们发生冲突。
当时的政治环境孕育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帕尔多·利亚达[6]、康特·阿圭罗之流以及他们那些企图浑水摸鱼、趁势捞一把的同伙,专门制造蛊惑人心的叫嚣,在躲躲闪闪地批评政府的同时,又鼓吹走和平和调和的道路。政府也奢谈和平,新上台的总理里韦罗·阿圭罗表示,如有必要,他将亲赴马埃斯特腊山区来为国家谋求和平。然而,几天以后,巴蒂斯塔就宣称没有必要与菲德尔会谈,马埃斯特腊山区没有发现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人,因此,没有理由去和“一帮土匪”谈判。
就这样,巴蒂斯塔独裁集团是决心想把这场战争打下去,在这一点上双方轻而易举就达成了一致,因为我们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打下去。当时,独裁政府任命佩德罗·巴雷拉上校为新的作战部长,此人因侵吞军费而闻名。后来,他在加拉加斯的古巴驻委内瑞拉使馆当武官时,眼睁睁看着巴蒂斯塔被赶下台,也无可奈何束手无策。
当时我们队伍中倒是有几位不可多得的人物,说起向美国人大规模宣传我们的革命运动,他们的作用不可小视。当然,其中有两个人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三个小美国佬从他们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父母那里逃了出来,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其中两个人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还从未听到过枪炮声,恶劣的天气和贫困的生活就把他们拖垮了,最后只能让新闻记者鲍勃·泰伯[7]把他们俩带走了。第三个小伙子参加了乌韦罗战斗,但是打完仗后他也因病离开了,但总算还参加了一次战斗。这些美国青年对参加革命在政治上准备不足,只是想在我们部队里满足一下他们渴望冒险的心理。看着他们离开,我们还真有些依依不舍,但也觉得还是走了好,省得麻烦。尤其是我,因为他们受不了这里的苦,作为一名军医,我肩头的一项重任就是要经常去照顾他们。
在此期间,政府也请一些新闻记者登上他们的军用飞机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上空转来转去,以证明这里不存在游击队的一兵一卒。这种奇怪的举动并没有让任何人相信他们的鬼话,但是表明巴蒂斯塔政府借用这种方法在欺骗公众舆论,他们的帮凶就是把自己乔装打扮成革命者却成天向人民撒谎的康特·阿圭罗之流。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终于得到了一张帆布吊床。吊床是很珍贵的东西。由于游击队有严格的规定,为了克服懒散享乐的情绪,帆布吊床只能发给那些自己用麻袋布缝制过吊床的人,所以,以前并没有发给我。其实任何人都可以用麻袋布缝制一个吊床,然后就有权申请帆布吊床。可是,我根本无法在麻袋布吊床上睡觉,因为我有过敏症,麻袋布对我刺激很大,只能睡在地上。既然没有缝制麻袋布吊床,我就无权申请帆布吊床。这些日常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每个游击队员独自面临的烦心事,但是,被菲德尔注意到了。他破例作出决定,发给我一张帆布吊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没抵达帕尔马莫查,正驻扎在此前刚路过的小山脚下的拉普拉塔河畔。我得到帆布吊床前一天,我们刚宰杀了游击队的第一匹马以度饥荒。
马肉不仅仅是一种美味佳肴,也是对战士适应能力的一种严峻考验。当时,我们队伍中的农民个个都义愤填膺,就是不吃分给他们的那份马肉。有些人还指责曼努埃尔·法哈多跟刽子手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和平时期,他就是个屠夫,现在又是他下手把游击队的第一匹马给宰杀了。
这游击队的第一匹马原本是住在拉普拉塔河对岸的一个名叫波帕的农民家的牲口。一九六一年古巴的全国扫盲运动之后,波帕一定也能读书识字了。他要是看了《橄榄绿》杂志,一定又会想起那天晚上,三个凶神恶煞似的起义军战士嘭嘭嘭地猛敲他家的门,错把他当成了告密的奸细,硬是把那匹背上还带着沉重马具留下的伤痕的老马拉走了。几小时后,这匹马就命中注定地成了我们可怜的口粮。马肉对有些人来说是一顿精美的大餐,但是对于一些农民战士的有偏见的肚子来说倒成了一种考验,因为,他们认为:大口咀嚼着人类老友的肉,不就是犯了同类相食的大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