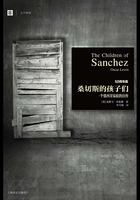
第10章 罗伯托(1)
我很小的时候就从家里往外偷东西了。只要我看见喜欢的东西,都会偷偷拿走,根本不经他人同意。就是这么样子。我一开始是偷鸡蛋。并不是因为饿,明白吗?因为我母亲都让我们吃得饱饱的。就是觉得小偷小摸好玩儿,把那些东西跟一个院子里的朋友们分享,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小的时候,大概也就五六岁吧,偷了母亲两毛钱。那个时候的两毛钱跟现在的十比索差不多。我父亲每天只给我们五分钱,可我这辈子都还想多要点,所以当我看见衣柜上放着两毛钱,而周围又没有别人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拿去用了再说。我买了点糖果,运气不太好啊,找给我的尽是零钱,而且是分币。
所以,我兜里就装满了钱,对不对?晚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就问那个硬币跑哪去了。我想:“糟了!要是他们搜身的话,不就发现我口袋里的钱了吗?那我不得挨一顿好揍,永生难忘?干脆去一趟厕所吧。”
靠房间最里面的厕所只有半扇门,所以当我把那些分币扔进便盆的时候,发出的响声简直震天,他们也就知道了我的鬼把戏。即便如此,我还是放水把那些硬币冲走了,这他们当然知道啦。到此为止,这还不算什么事儿吗?正如我自己说的,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坏蛋。所以,那天我被教训够了,我的母亲、父亲、外婆——愿她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都教训了我,我今后再也不敢了。
母亲把我们照料得很好。她对我十分喜爱,但她最爱的还是曼努埃尔。她很少打我。我知道她爱我,是因为她不管去哪里都会带上我,带我的情况多于其他几个。她经常对我说:“罗伯托,走,我们去买蛋糕配料。”
“好的,妈妈,走吧。”
我的父亲和母亲一向相处和睦,只有一次争得不可开交,让我好久都不能忘怀。父亲对着母亲——愿她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大吼大叫,呵呵,他吼得越来越声嘶力竭。我的外婆,还有瓜达卢佩姨妈都拉着他不让他动手。拉扯的过程中,他的钥匙链掉到地上,我一把抓起来就跑了出去。钥匙链上有一个剃须刀片,因为父亲脾气暴躁,我当时以为他想用它来收拾母亲。
我的姨妈、外婆帕契塔和用人索菲娅都连忙跑进来拉住了他。等我回到屋子里,架已经打完了。父亲带着我来到神殿向圣母祈祷,看见他哭了,我也跟着哭了起来。冷静下来之后,他给我买了些点心。
1月6日是一年一度的三王节,在栽种着母亲最喜爱的植物的花瓶架子上,我们总能找到几样玩具。可有一年的1月6日,三王没能造访我们的寒舍,我由此觉得自己是世界上运气最不好的人。跟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们几个小孩那天很早就起了床,然后到处找玩具。我们先去花瓶架子上找了一阵,接着又去火盆里看了看,万一三王们把玩具放在了木炭和灰烬里呢。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于是,我们只好跑到院子里,看着其他小孩玩玩具。当有人问“三王给你们送了什么玩具”的时候,我和曼努埃尔都只能这样回答:“什么也没有。”
那是母亲去世前跟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1月6日。那之后,我一连几年都要大哭一场。
我们当时住在特诺奇蒂特兰大街上的一套一居室房子里。我的父亲和母亲睡一张床,曼努埃尔、康素爱萝和我睡另一张床。玛塔大了一点之后,也跟我们睡一张床。我们几个并排而卧,曼努埃尔挨着康素爱萝,康素爱萝过来是玛塔,然后是我,这样的顺序一成不变。
我有个现实问题,经常尿床,一直持续到九岁或十岁的样子,他们说我是全家的尿床冠军。尿床的不止我一个,曼努埃尔和康素爱萝有时也会尿床。就因为这个坏毛病,不知道父亲母亲把我揍了多少次,而且威胁说起床后要把我泡在冷水里。母亲还真这么做过一次。当然了,我不能怪她,她这么做也是为了改掉我的毛病,不过我确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忘不掉这件事情。
我六岁时的一天凌晨,母亲死在了父亲的怀抱里。她的去世对我震动很大,对我一辈子都是个折磨,因为我觉得她的死应该是我的错。她去世的头一天,我们一大家人还去了大教堂。同去的有姨妈、阿尔弗雷多舅舅和何塞舅舅,我们一大家子玩得非常开心。亲爱的母亲总会庆贺我们的圣徒节,我们因而能吃到猪肉之类的东西,当然,你也知道,这样的东西对人没什么好处,会传染疾病,我母亲就因为我而染上了疾病。
实际上,那天稍晚些的时候,她还叫我去把屋顶上的鸟笼子拿下来。我母亲很喜欢鸟儿,知道吧?她在几面墙上都挂满了鸟笼子,就因为她喜欢那些小生命啊。我于是爬上房顶,可弄了些灰尘到邻居那边去了,那个女人就用水来泼我。
“小兔崽子,你也不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儿?”
我母亲跑出来维护我,就跟邻居吵了起来。如果不吵这一架,我妈妈也就不会死。反正,不管我有没有错,那就是事情的原委。
他们在凌晨两点钟叫醒了我。我不想起来,因为我又尿床了,很担心他们会责罚我。可我们看见父亲在那里哭,也就战战兢兢地爬了起来。我感觉到事情不妙,因为我看见父亲把母亲抱在了怀里。医生进来的时候,我们全都站在床头哇哇大哭,亲戚朋友们想把我们拉到外面来,可我就是不走。
我不相信母亲已经死了。他们把她停放起来,那天晚上我还偷偷地爬上去挨着她睡了一觉。他们到处找我,可我就挨在母亲身边睡着,盖的也是她身上那张床单。在那个年纪,我已经知道死亡就意味着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我还是这样安慰哥哥和妹妹:“别哭,妈妈只是睡着了。”我凑过去对着妈妈说:“妈妈,妈妈,你睡着了,对不对?”我摸了摸她的脸,可我知道,她再也不会醒来了。
我不止那个时候思念母亲,现在仍然十分想念她。从她去世那一天我就知道,我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别人把这样的烦恼倾诉一遍就会有所缓解,可我跟很多人都说过这件事儿,仍旧于事无补。只有离家出走,游手好闲,一个人跑到乡下,或者跑到山上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平静一些。我相信,如果母亲还在,我的日子会大不一样。我或许会变得更坏。
母亲去世后,外婆差不多成了我的第二个母亲。我随时随地都跟着她。我叫她小妈妈,其中的感情跟我喊自己的妈妈时一模一样。她对我们很好,但有点严厉。她毕竟是个老人,又在旧环境下长大,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正统。
她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负责照看我们。她在广场上卖蛋糕渣,我时常去看她。我愿意跟她在一起,因为她了解我,经常提醒我。家里的其他人,就连跟我们最亲近的瓜达卢佩姨妈都经常叫我“黑娃儿”、“鬼脸”。我原来不知道“黑娃儿”是什么意思,但那同样让我感到不舒服。所以,我总是黏在外婆身边。
曼努埃尔从来不愿意跟她去卖面包或蛋糕渣。愿意陪她去的人是我。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毕竟只是个孩子嘛,不过我觉得如果她一大清早出门有我陪伴的话,她就什么事儿也不会遇到。多亏了老天,我们真没遇到过什么坏事儿。有一次,曼努埃尔跟我们走了一趟,他把外婆惹得非常生气。一个小贩扛着木桩正在售卖糖葫芦,边走边喊:“山楂,山楂,一分钱一串。”曼努埃尔经常喜欢揶揄外婆,此刻也跟着喊起来:“外婆,外婆,一分钱一位……一分钱一位咯……”嗨,她骂了他几句,接着就要去抓他,当然抓不住呀,他跑得可快了。他只是想取取乐,可那一次他把外婆惹哭了,让我也跟着难受。
我们那时居住在古巴大街,对,就是古巴大街,因为我爸爸刚结识了艾莱娜,外婆于是离开我家,搬去跟瓜达卢佩姨妈同住了。我因此更觉得孤单,非常思念母亲。外婆在的时候,我还没觉得母亲已经离我而去。
艾莱娜做了我的后妈之后,我常常去外婆帕契塔那里告状,说艾莱娜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些日子,外婆就是我的擦泪巾,是她让我感到轻松了许多。我还偷过树苗,呵呵,这也不算偷,因为那本来就是母亲的东西,我不想艾莱娜碰它们,于是就把它们搬到了外婆或姨妈的家里。然而,可怜的外婆很快就没有了,因为没过多久,她也去世了。
从一开始,后妈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我和年轻的后妈相处得一点都不愉快。在我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妈妈,即便有一百个一千个人想要成为你的妈妈,那也完全是两码事儿。再说,朋友们经常提醒我,后妈都不是好人。
我猜想,艾莱娜大概有十八岁。不管怎么说,她就是太年轻,对于照料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完全没有经验。她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怎样才听她的话,尤其是我,因为我最野。如果她跟我好好说,我也许会任凭她摆布,可她老想着控制我、命令我、左右我。从小开始,我就不喜欢除了爸爸妈妈之外的人指使我做这做那。只要艾莱娜敢碰我,我肯定会跟她干架。身体上的防卫我一直都知道,只是言辞上的防卫我从来不懂。
我经常跟艾莱娜打架,原因之一是有了她之后我和曼努埃尔就得睡地板。有一次,我听见爸爸和艾莱娜在说话,她说我们睡床上的时间够长了,两个女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于是,父亲就要求我们去睡地板——也不是真的睡在地板上,因为父亲给我们买了草席。我猜,父亲那个时候连床都买不起。
我哭过好几回,但从没跟父亲说过。我的心里既感到痛苦,又觉得烦闷。我得像狗一样睡地上,这让我觉得很伤心。那个时候,我十分想念妈妈。要是她还活着,我们会睡在床上,会好得多。即便她去世了……在艾莱娜没来之前……我们也是和爸爸一起睡床上,位置被艾莱娜占了。
挨着父亲睡,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曼努埃尔占了紧挨父亲的位置,我不知跟他打过多少次架。我们会一直争得不可开交,直到父亲说:“大家都闭嘴,赶紧睡觉。”啪!灯关了,父亲脱了鞋,脱了裤子放在凳子上,一切才开始平静下来。
一开始,还有一件事我很不喜欢,艾莱娜曾经有过一个男人。我很替父亲担心,因为她的前夫可能会报复或者什么的。
父亲经常骂我打我,因为后妈往他的脑子里灌输了很多东西。她并没有完全胡言乱语,但总是要添油加醋,抹杀真相。有好多次,她都差点惹恼了我。要是我上床的时候把灰尘带了上去,她会说:“下来,黑娃儿!”那样的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会顶上一句:“你个丑八怪,怎么也敢叫我黑娃儿?就算我黑,也是老天的原因。”这么一来,她就会打我,我也会还击,而且把她弄哭。
父亲一走进家门,她不是先打招呼说“哈啰”,而是先数落我的不是。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早已怒不可遏,根本不听我的辩解。他只知道打我。第二天,我照样会跟艾莱娜拧着干。
父亲真可怜!就因为我跟那个女人之间的矛盾,他花了不知多少钱。他拿了不知多少个五十比索、一百比索、三百比索,买了不知多少件衣服、多少双鞋子,只为了满足那位小姐。这让我十分抓狂!她把那些钱全都存了起来,有时候我也会偷偷地拿走一些,因为那钱反正是从我爸爸那里得来的。
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出来,但我不仅仅深爱我的父亲,甚至视他为偶像。我小的时候,曾经令他引以为傲,引以为乐。他对我的爱,甚于我的哥哥,因为他不管去哪里,总会首先带上我。有很多次,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大教堂、看电影,或是在夜里散散步。他现在依然同样深爱着我,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因为我已经不值得他那样爱我了。
父亲对我们几个一向寡言少语,他不说话,我们遇到麻烦也不跟他商量。我曾经尝试过亲近他。我想让他像别人家的父亲那样对我们特殊一点,跟我说说话,跟我们大惊小怪一下。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很喜欢亲亲他的手,或者抱抱他。我觉得,父亲那个时候更了解我们,虽然那个时候我也渴望他表示一下爱,或者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
我的一生中,父亲只有两次跟我亲密无间地说过话。他问我:“儿子,遇到什么麻烦了?怎么回事?跟我说说你的困难吧。”听到他如此深情地说出“儿子”这两个字,我顿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重要的人了。他一般叫我的名字罗伯托,或者是“你”,骂我的时候则会用脏话。
我一直很反感儿子跟父亲高声说话。父亲无论什么时候批评我们,或者只是跟我们说说话,我们根本不敢看他,因为他的表情太过严肃。就算我想辩解,或者把事实讲清,他都不会让我开口。“你不要说了,”“你只会这个那个。”当他大声呵斥我们的时候,我从来不跟他顶嘴,相反我会责怪自己。我会对哥哥和妹妹们说,如果父亲对我们不好,那是因为我们有错。父亲是神圣的,我的父亲尤其如此。他是个好人,像他这样的人找不到第二个。
父亲不会无缘无故地揍我们。他总是用他现在都还拴着的那条宽皮带抽我们。那条皮带属于加厚型,他会用力抽打我们,对我更是如此。他老是狠揍我们,我们差不多都皮了,根本没感觉,即便他生气的时候对我们狠敲狠打。不幸得很,我还有个烂习惯,每当挨了打,我会用头撞击墙壁、衣橱或别的什么东西。我不停地用头去撞,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等我后来长到十来岁的时候,父亲用起了电线。那一根电线很粗,有两米多长,他折成四折,还打了个结。喔!这一下我们感受得到了。他每抽打一下,立马会冒出一道鞭痕。我父亲不是那种只教训犯事儿之徒的人,他会把我们两个都收拾一番。在这一点上,他是不偏不倚的。
父亲总是逼着我去学校。我竟然不听他的话,真是愚蠢至极!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不喜欢上学。当同班同学被抽到黑板上做题的时候,他们三下两下就做完了,而且把握十足。抽到我的时候,我总觉得有如芒刺在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在注视着我。我认为他们在议论我,我想比他们做得更好,可正因为如此,我没法集中注意力,需要的时间也就更长。
我母亲、姨妈或者外婆会领着我去上学,有时候她们甚至是拖着我去上学。她们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跟那些男生女生待在一起,心里觉得绝望极了。跟那么多人待在一起,我在心里感到自卑。
我上了四个一年级,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逃学。二年级我倒是只上了一次,可升到三年级之后,我只读了两三个月,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那帮朋友,或许也因为自己在家里感受到的自由太少,我以逃学为乐,经常去查普尔特佩克公园闲逛。只要我逃学,就会有人通知父亲,等我回家的时候,他早已为我准备好了皮鞭。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跟我哥哥很亲密。他一直在保护我,好几年的时间里,曼努埃尔充当着我的保护伞。我原来很胆小,很爱哭,用墨西哥人的话来说,我就是个“哭泣儿”,因为只要有人稍微说话声音大一点,我就会哭个不停。大孩子令我感到害怕,他们一吓我,我就会哭。如果有人碰我一下,我会大声尖叫,立马跑去哥哥那里。他也真够可怜,为了我跟别人打了不少的架。
我上到三年级的时候,曼努埃尔毕业了。没了他,我根本没胆量去面对那么多大孩子,于是我辍学了。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感受到别人对我的关注。别人总是瞧不起我……对我嗤之以鼻。我时常想的就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必听命于任何人。我想把自己变成一只风筝,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
我想过做一名运动员,做一个了不起的汽车司机或者摩托车手,去赛场上跟别人一比高下。我一直都想做飞行员。有一天,爸爸带着我去拉古尼拉市场买了一顶帽子,他问:“你想买哪一顶?”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顶带护目镜的,也就是飞行员使用的那一种。
当我跟朋友们一起玩耍的时候,所玩的游戏常常是飞行。为了更有真实感,我会跑到楼顶上,戴上护目镜,像一架大飞机那样在那里不停地跑。或者干脆在天井里奔跑。我会在水管上系上绳子,假装那就是机翼。我把它当成飞机,感觉到自己真的飞了起来。那是我的梦想。只要有飞机飞过,即便是在今天,我也会抬头看上一阵,好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开上一架大飞机。
就因为想飞,我撞破了头。我的表兄萨尔瓦多,也就是我姨妈瓜达卢佩的儿子——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吧——很贪玩,并且喜欢捉弄我们。有一次,我让他给我坐飞机,也就是提着我转圈子。我们一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于是他抓住我的手腕和脚踝开始转圈。突然,他一下子失了控,砰!我被甩到墙上,头部开了一个口子。等我醒过来的时候,爸爸和妈妈,还有其他人都给吓了一大跳。我浑身是血,但一点也没觉得害怕。实际上,我觉得流点血这事儿挺好的。我头上的这个部位还有个疤。
我身上到处都是伤疤,不撞这里就撞那里。我的头上还开过几道口子,要么是从屋顶上栽了下来,要么是拿石头跟朋友打架留下的。有一次,我差点弄瞎一只眼睛,流了很多血,以为自己就快死了。我当时手里拿着一把很小很尖的玩具铲子不停地奔跑,一下摔倒在地,铲子直接插进了左眼。其他人立刻把我送到了医生那里,所以这只眼睛至今用起来也没任何问题。伤得最厉害、最吓人那一次是我被一条狗咬了胳膊。
我学会游泳的时间在我哥哥前面,尽管他经常跟他那一帮朋友出去游泳。我经常缠着他们,巴不得他们把我也带上。我原来经常在逃学的时候去离家不远的一个泳池游泳,那里有一个服务员名叫霍苏埃令我憧憬不已,因为他不光游得好,为人也很不错。他很高大,很强壮,也很魁梧。不瞒你说,我觉得他的体格也很好。我很想像他一样,不光做好人,而且长得高高大大、壮壮实实的,让每个人都能记得我。他跟我们说过,他是怎么走遍全共和国的。
有一次,也就是我八岁的时候,我没钱买票进入游泳池。我和曼努埃尔,还有他的朋友阿尔维托,也就是蠢驴站在大门外的时候,突然来了个醉汉,于是我们想从他兜里弄点钱用。曼努埃尔和蠢驴要多少,这个家伙就给多少。于是,我也跟他说:“还有我呢?你难道不给我一点吗?”可他已经开步走了,我又说:“听着,先生,我只要一张票钱,难道你都不给我吗?”
“你是谁?”他问道。
“我是你刚刚给钱那两个人的弟弟。”我接着又告诉他,一张票需要多少钱。
“不给,你这小王八蛋!滚开。你长得太黑了。”
那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哥哥和阿尔维托进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感觉非常沮丧和渺小。
每当我逃学,或者是应父亲的要求去拉古尼拉市场帮着把他买的东西扛回家的时候,我习惯带上小妹妹玛塔。我对她的喜欢一向超过其他两兄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从来没见过我的母亲,或者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她的缘故。
我教会了她搭顺风车,怎样跳到电车的保险杠上,然后怎样抓牢等等。我原来还经常带着一只白色的小狗从卡萨—格兰德大街出发,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喜欢跟着我。我们像两只苍蝇一样,舒舒服服、高高兴兴地紧贴在电车的后面,小狗则在后面追着我们跑。每个人都会停下脚步盯着我们看,不管是公共汽车,还是小轿车里的人都会把脑袋伸出来打量这样的场景。我以为他们是在欣赏我们,因此感觉高兴极了。
我喜欢在电车高速行驶的时候跳上去。玛塔十分勇敢,也学会了这一手。我不止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也是在拿她的生命开玩笑,可她乐此不疲,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觉得,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她的喜欢胜过了康素爱萝和曼努埃尔。
我经常带她去查普尔特佩克公园,或者去神殿攀爬那些极陡峭的山坡。我把三根绳子拧成一股,一头套在我的腰间,另一头系在她的身上。我挑选最危险的悬崖先爬上去,然后再把她拉上去。她非常喜欢这项活动,从没说过什么。
我要说清楚,我一直视玛塔为妹妹。跟女性打交道自然会激起我的本能反应,知道吗?但跟我的两个妹妹完全是另一码事儿。令我苦恼的是,父亲发现我们一起出去玩耍之后,有时会表现得疑神疑鬼。他会这么问:“为什么要出去?去干什么了?”他还会问玛塔,看我们有没有干什么坏事。我曾经在军队医院的面包房做过一段时间,他们给我的报酬是面包卷随便吃。后来,我想到把玛塔也带上,兴许人家也会让她吃点面包卷。那家医院离得很远,父亲得知我带着她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