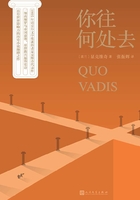
第十七章
对基隆来说,除掉格劳库斯的确是非常要紧的。格劳库斯虽然上了年纪,但是一点也不显得衰老。基隆对维尼茨尤斯说的话也大部分反映了实情,他以前认识格劳库斯,后来他把格劳库斯出卖给了强盗,还抢走了他的亲属和财物,甚至叫人杀他。但基隆对自己做的这些事并不感到后怕,因为他没有把那个将要死去的格劳库斯留在客店里,而是把他扔到明杜纳埃附近的野地里去了。只是有一件事他没有料到,就是格劳库斯不仅没有死,而且治好了刀伤,还到罗马来了。因此当他在做祈祷的那栋房子里见到他时,他真是吓得魂飞胆丧了。在最初的一瞬间,他确实不愿再去寻找莉吉亚了。可是他最害怕的还是维尼茨尤斯。他很明白,现在除了格劳库斯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权势的贵族在追逐他,要对他进行报复,而且这个有权势的贵族还能得到另外一个权势更大的贵族裴特罗纽斯的支持。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面对这种情况,他就不再犹豫了,与其招来大敌还不如去对付小敌。虽然他那怯弱的天性在采取血的手段时有些害怕,但他认为,假他人之手去杀死格劳库斯还是做得到的。
对他来说,现在最迫切的是人手的挑选,在这件事上,他想起了他对维尼茨尤斯提起过的那个办法。基隆因为夜里常常住在酒店里,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失去了尊严和信仰的地痞流氓混得很熟,在他们中不难找到那种什么事都敢干的人,而且有的人一嗅到钱的气味,就什么都愿意干。可是这种人有的可能真的替他去效力,有的拿到预付的定钱之后,也可能反过来以去报官来威胁他,把他所有的钱财都要了去。实际上,基隆对那些躲在苏布拉区或第伯河对岸的一些房子里的流氓无赖和可恶的盗匪已经产生了厌恶感。他惯于以自己的想法去度量别人,就以基督徒来说,他虽然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宗教,可是他断定在他们中间一定能找到听他使唤的人。在他看来,这是一些比别的人都更加忠实可靠的人,他一定要去找他们,要使他们懂得不是为了钱,而是要真心实意地替他效劳。
基隆决定就在当天晚上去找埃乌里茨尤斯。他知道埃乌里茨尤斯是忠于他的,会尽心尽力地支持他。但基隆是一个遇事谨慎的人,他知道,干这种事和那个老人对他的信任,和老人的高尚品德以及他对神的敬仰都不相容,因此他就不能把真实意图告诉他。他要找的是什么都能够干得出来的人,而且他还要对他们采取一个绝妙的办法,使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也非得替他干过的这件事永远保守秘密不可。
埃乌里茨尤斯老汉把儿子赎出来后,便在大竞技场附近那些多得不可胜数的小店铺中租了一间铺房。他在这里向前来看比赛的观众出售橄榄、豆子、无盐糕点和蜜糖水。基隆来到这里后,正遇上他在收拾铺面。基隆以基督的圣名向他问候,随后便开始谈起他来找他要办的事情。他说他过去帮助过他们,想必他们也该报答他了。他现在需要两三个身强力壮和胆大无畏的人去铲除一个危险,这个危险不仅对他是一个威胁,而且也威胁着所有的基督徒。他现在很穷,因为他把他的钱几乎一文不剩地全都给了埃乌里茨尤斯;但若有人能够替他效这个劳,他还是要给他们一笔酬金的。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相信他,老老实实替他把这件事办好。
埃乌里茨尤斯和他的儿子克瓦尔杜斯在这位恩人面前,几乎是跪着听完了他的这一番话。他们两人随即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他一声令下,就是让他们上刀山下火海也决不退缩。他们深信,像他这样一位圣人绝不会要他们去做违背基督教义的事情。
基隆也向他们保证,他要做的这桩事绝不会违背基督的教义。他这时还抬起眼睛朝天望去,好像要做祈祷,实际上他在想,既然他们已经提出了请求,是不是就把这件事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还可以省下一千个塞斯泰拉银币。但他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之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埃乌里茨尤斯已经老了,也许还不只是年龄而主要是忧愁和病魔已经把他摧残得衰颓不堪,他的儿子克瓦尔杜斯又只有十六岁。基隆需要精明能干的人,尤其需要身强力壮的汉子。至于那一千个塞斯泰拉银币,他觉得,只要他那绝妙的计策能够生效,省下大部分是不成问题的。
但埃乌里茨尤斯父子仍表示他们一定要亲自去办理这件大事,直到基隆坚决予以回绝之后,他们才退让了。克瓦尔杜斯这时便开口说道:
“我认识面包房老板德马斯,老爷!在他家的磨坊里干活的有奴隶也有他雇来的人,有个雇工力气很大,他一个人能干两个甚至四个人的活。我亲眼见过他举起一块四个人都搬不动的大石头。”
“如果他笃信上帝,又能为同教的兄弟做出牺牲的话,你就让他和我认识一下吧!”基隆说道。
“他是个基督徒,老爷!”克瓦尔杜斯回答说,“在德马斯家干活的,大部分是基督徒。他们有的白天干,有的干夜班,他是干夜班的。如果我们现在去,就正好碰上他们吃晚饭,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德马斯的家在中心市场附近。”
基隆很高兴地表示了同意,中心市场[1]就在阿芬丁山脚下,距离大圆戏场也不很远。他们不需要绕过山脚,只要沿着河边走去,穿过阿米里亚柱廊[2]就到了,这么走近得多。
他们走进柱廊后,基隆说:“我老了,好忘事,是的!我们的基督被他的一个门徒出卖过,可是这个叛徒叫什么名字,我这会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叫犹大,后来他也上吊自杀了,老爷!”克瓦尔杜斯回答说,他心里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连这个名字都忘了呢?
“啊,是的!叫犹大,谢谢你。”基隆说。
两个人默不作声地走了一会儿,便来到了中心市场,可是这里的大门已经关了,他们只好从它的旁边绕了过去。然后他们围着向民众发放粮食的仓库又转了一阵,就拐到左边去了。这里有许多房子,沿着奥斯天希斯大街[3]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一排,一直排到了泰斯塔丘斯山丘和彼斯托留姆市场上。他们在一栋木房子前停了下来,听见里面有轰隆隆的推磨声响,克瓦尔杜斯马上走了进去。但基隆却不愿在人多的地方露面,他总是害怕命运之神让他碰上那个格劳库斯医生,所以他宁愿一个人等在外面,抬头望着天上的月亮,自言自语道:
“这个当磨工的赫拉克勒斯倒挺有意思,如果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基督徒而又生性愚笨的话,那就不用为他花钱,他也会给我办事的。如果他是个流氓但很机灵的话,付给他一点酬金也很值得。”
他的这些胡思乱想在克瓦尔杜斯回来后被打断了。克瓦尔杜斯给他带来了一个体格健壮的汉子,他身上穿的那件爱克梭米斯汗衫总是把右肩和右胸露在外面,这样便于干活,工人们都很喜欢这种汗衫。基隆看见来人后,满意地松了口气,因为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粗壮的胸脯和臂膀。
“老爷,这就是你想见到的弟兄。”克瓦尔杜斯说。
“愿基督赐予你平安!克瓦尔杜斯!你先问问这位兄弟,我这个人可不可靠?值不值得信赖?然后,以上帝的名义,你就回去吧!别让你那年老的父亲孤单单地一个人待在家里!”基隆说。
“这是一位圣人,为了把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赎出来,他献出了他的全部财产。愿我们的——救世主给他准备一份天国的赏礼!”克瓦尔杜斯说。
这个膀阔腰圆的汉子听了他这些话,便躬身吻了一下基隆的手。
“你叫什么名字,兄弟?”希腊人问道。
“我在受神圣的洗礼时取的名字叫乌尔班,长老!”
“乌尔班,我的兄弟,你有空和我随便谈谈吗?”
“我们要到半夜才上班,现在在给我们做晚饭。”
“那么时间还早得很,我们就去河边走走吧!到那里我再把我的来意告诉你。”
他们来到了河边,在石头堤岸上坐下,远处传来的碾磨声和河水流向远方的哗啦声不时打破了这里的寂静。基隆仔细打量着这个工人,虽然他的脸色有点忧郁和可怕,就像罗马的野蛮人一样,但他觉得他是个善良和诚实的人。
“不错,这个人既和善又愚笨,叫他杀死格劳库斯是不用花钱的。”基隆暗自思忖道。
“乌尔班,你爱基督吗?”
“我衷心地热爱基督。”那个工人回答说。
“你也爱教里的兄弟姊妹,爱那些教给你基督的真理和信仰的人吗?”
“我也爱他们,长老!”
“祝你平安!”
“也祝你平安,长老!”
随后沉默了半晌,只听见远处的碾磨声和下面河水的哗啦声。
基隆凝望着亮堂堂的月光,以缓慢而又低沉的声调开始讲起了基督死时的故事。但他好像不是在对乌尔班说话,而是他自己想起了基督的死,他要把这个秘密告诉这座沉睡的城市。他讲得那么严肃动人,使得那个工人也哭起来了。基隆于是叹息起来,他很激动地说,在救世主遇难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来救他,即使不能把他从十字架上救下来,至少也应当制止士兵和犹太人去侮辱他嘛!那个野蛮人听后,由于悲伤和抑制不住的愤怒,紧捏着他的一双大拳头,听到基督的死他很激动,当他想起那群恶棍是怎么嘲弄钉在十字架上的羔羊时,他那纯洁的灵魂更是义愤无比。由于这种义愤,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要求复仇的强烈愿望。
基隆突然问道:
“乌尔班,你知道犹大是个什么人吗?”
“知道,知道!可是他已经上吊死了。”那工人大声说道。
在他的话中,仿佛表露出了一种遗憾的情绪。他遗憾的是,那个叛徒自己惩罚了自己,没有让他亲手去惩罚他。
基隆继续说:
“假如犹大没有吊死,他在陆地上或海上又遇到了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基督徒为了救世主的苦难、流亡和死去,应不应当对他报仇呢?”
“谁能不去为救世主报仇呢?长老!”
“愿平安与你同在,羔羊的忠实仆人!是的,我们自己受一点委屈倒也没什么,可是谁有权利宽容对上帝犯下的罪过呢?毒蛇只能生出毒蛇,罪恶只能生出罪恶,叛逆也只能生出叛逆,你看,从犹大的毒液中现在又生出了第二个叛徒。正像第一个叛徒把救世主出卖给了犹太人和罗马士兵那样,在我们中也出了一个叛徒,他要把救世主的羊群出卖给恶狼。如果谁都不加以防备,如果没有人及早斩断这条毒蛇的脑袋,那么我们大家就会遭到灭亡,基督的光荣也会和我们一起遭到灭亡。”
这个工人非常惊恐地望着基隆,好像不明白他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希腊人于是扯起他的外衣的一角,把它蒙在头上,然后用一种仿佛从地里发出来的声音不断地说:
“你们要大难临头了,真正上帝的仆人!你们就要大难临头了!基督教的善男信女们!”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只听得见碾磨的轰隆响声,碾磨工人低沉的歌声和河水的哗啦声。
“长老,那个叛徒到底是什么人?”工人终于问道。
基隆低下了头。那个叛徒是什么人?他是犹大的儿子,是犹大用他的毒汁喂养大的儿子。他伪装成基督徒,到做祷告的房子里去,要向皇帝控告我们的弟兄不承认皇帝是神,控告他们在泉水里放了毒,控告他们虐杀儿童,还说他们要消灭罗马这座城市,叫它连一块石头都不留下。再过几天,皇帝就会命令禁卫军把罗马城的男女老幼都监禁起来,然后把他们处死,就像他们过去处死佩达纽斯·塞昆德的奴隶那样。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那个叛徒干的。既然过去没有人惩罚第一个犹大,在基督受难的时候没有人救他,也没有人为基督去报这血海深仇,那么现在有没有人能够胆大无畏地去惩罚那个叛徒,去打死那条毒蛇呢?有没有人能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向皇帝控告之前,就把他消灭掉呢?在我们的弟兄和我们对基督的信仰就要大难临头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起来保卫我们呢?
乌尔班一直坐在石头井台上,这时他突然站了起来,说:
“我做得到,长老!”
基隆也马上站了起来。他冲乌尔班那张被月光照得很亮的面孔望了一阵,便伸出双手,把手掌慢慢放在他的头上,庄严地说:
“你到基督徒中间去,到做祷告的房子里去!找弟兄们问一个叫格劳库斯的医生。只要他们给你指了出来,你就以基督的名义把他杀了……”
“啊,格劳库斯?……”这个工人不断地重复着说,好像要把这个名字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你认识他?”
“不,不认识!罗马的基督徒有千千万,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的。可是明天晚上,我们的兄弟姐妹都会去奥斯特里亚努姆参加一个集会,因为来了一位基督的大使徒,他要在那里讲道。到那个时候,弟兄们会把格劳库斯指给我看的。”
“奥斯特里亚努姆?”基隆问道,“那里是城外,兄弟姐妹们都会去吗?集会在晚上举行?在城外的奥斯特里亚努姆?”
“是的,长老,那里是我们的墓地。就在维亚·萨拉里亚大道和诺门塔拉大道之间,您怎么不知道使徒要在那里讲道呢?”
“我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所以没有接到通知。再者,我从科林斯来到这里也没有多久,我不知道奥斯特里亚努姆在哪里。在科林斯我掌管一个基督教区……现在好了!既然基督这么启示了你,那你明天晚上就到奥斯特里亚努姆去吧,我的孩子!你在那里的听众中,一定会找到格劳库斯,你就在回城的路上,把他杀了吧!为了这件功德,你的全部罪过都会得到赦免的。祝你一路平安……”
“长老……”
“你还有什么事吗,羔羊的仆人?”
那个工人的脸上有难色,因为他不久前杀了一个人,也许是两个。但基督的教义是不允许杀人的,而且他杀死那两个人并不是出于自卫;即便为了自卫,也是不许杀人的。他杀人当然不是为了谋取钱财,这一点基督是明察的……主教当时还亲自派了弟兄去帮助他,就是不让他杀人,他自己其实也不愿意杀人,只因为上帝要惩罚他,给了他太大的力气……直到现在他还在痛苦地忏悔……别的人推磨时都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只有他这个不幸的人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罪愆,反省他对羔羊犯下的罪过……他为此不知祈祷过多少次,哭过多少次,也不知多少次地祈求过羔羊的饶恕,但他仍然觉得这一切都不足以赎他的罪孽……可是今天,他又答应去杀死一个叛徒……好吧!既然一个人要能够忍受别人对他的侮辱,那么明天,他就是在参加奥斯特里亚努姆集会的兄弟姐妹的众目睽睽下,也要杀掉那个叛徒,只是首先该让那个叛徒去接受长老会的审判,接受主教或者使徒的审判。杀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杀一个叛徒还是一件痛快的事,就像杀一只狼或者杀一头熊那样。但格劳库斯如果是无辜的呢?一次新的谋杀,新的犯罪和对羔羊的新的触犯不是又会给他的良心带来更大的痛苦吗?
“没有时间审判了,我的孩子!”基隆说,“因为这个叛徒会从奥斯特里亚努姆一直跑到安茨尤姆去晋见皇上,或者就在他当差的一个贵族家里躲藏起来。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凭证,你杀死格劳库斯后,就拿出来给别人看,不管是主教还是使徒,都会祝福你的善举的。”
说完他从身上掏出了一枚小钱币,又在腰带上找那把小刀。他用刀尖在钱币上刻了个字,把它交给了那个工人。
“这就是对格劳库斯的死刑判决,也是你的凭证。你杀了格劳库斯后,把它拿给主教看,主教会祝福你的功德,还会宽恕你以前那次非本意犯下的杀人罪。”
这个工人不由自主地伸手接过了那枚钱币,但他对他前次杀人的情景记忆犹新,所以马上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他带着一种几乎是哀求的声调问道:
“长老,你做这件事是凭良心的吗?你亲耳听到过格劳库斯要出卖我们的弟兄吗?”
基隆明白了,他非得拿出一些证据或者说出一些人的名字来不可,否则他在这个巨人的心中就会引起怀疑。他的脑子里马上产生了一个绝妙的想法,便说:
“你听着,乌尔班。我虽然住在科林斯,但我是科斯人。我在罗马给一个名叫尤妮丝的女奴讲过基督的教义,她是我的同胞,现在在一个叫裴特罗纽斯的人的家里当服装师。这个裴特罗纽斯是皇帝的朋友,我就是在他家里听到了格劳库斯要出卖所有的基督徒。他还答应给皇帝的另一个亲信维尼茨尤斯去基督徒中寻找一个姑娘……”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忽然惊奇地望着那个工人,因为他发现那个工人的一双眼睛像野兽一样突然冒出了火光,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狂野的愤怒和威逼恐吓的神态。
“你怎么啦?”基隆有些害怕地问道。
“没什么,长老,明天我就去杀了那个格劳库斯!……”
这个希腊人不再说话了。他拉着乌尔班的胳膊,让他转过身来,趁月光直接照射在他的脸上,又仔细地端详着他。显然他心里还拿不定主意,是再追问下去,把所有的一切都问个明白,还是暂且停留在目前已经打听到或者可以推测到的事情上,不再问下去了?
他那谨小慎微的天性终于取得了胜利,因此他深深地喘着气,又把手掌放在那个工人的头上,用一种庄严而又动听的声调问道:
“是在神圣的洗礼时给你取了这个乌尔班的名字吗?”
“是的,长老。”
“祝你平安,乌尔班!”
[1] 原文是拉丁文。
[2] 原文是拉丁文。
[3] 原文是拉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