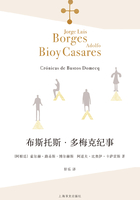
第4章 寻找绝对
无论我们有多心痛,都得鼓起勇气承认,拉普拉塔河的目光是投向了欧洲去的,它藐视和忽略了自身的真正价值。聂伦斯泰因·索乌撒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在《乌拉圭传记辞典》中省略掉了他的名字;蒙特伊罗·诺瓦托则只列出了他的创作年限(1897—1935)及其作品表,这些作品中流传度最广的为:《可怖的平原》(1897)、《黄晶午后》(1908)、《斯图尔特·梅理尔艺术作品及理论》(1912),后者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专著,赢得了不止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的称赞,此外还有《巴尔扎克〈对于绝对的探索〉中的象征手法》(1914),以及颇具野心的历史小说《哥门索罗封地》(1919),不过该作品被作家在临终之前舍弃了。在上世纪末的巴黎,聂伦斯泰因·索乌撒经常参加一些法国-比利时文艺聚会,不过,在诺瓦托简洁的记录中一再搜寻相关的蛛丝马迹纯属白费工夫,因为索乌撒甚至连一位安静的听众都算不上。同样地,那本记录也没有提及《小摆件》,那是他的混合题材的遗作,由他的一群将自己简称为H.B.D.的友人在一九四二年出版。此外,尽管存在大量的,但不总是忠实于原著的,出自卡图勒·孟戴斯、埃弗拉伊姆·米克尔、弗朗茨·韦尔弗以及亨伯特·沃尔夫的索乌撒作品译本,人们却发现,诺瓦托完全无意提起它们。
据观察,他的文化背景很多元。他的意第绪语家族为他打开了通向条顿语文学的大门;布兰内斯牧师向他轻松地传授了拉丁语;法语是在文化学习中自学的,英语则是从叔父那里继承来的,这位叔父曾是梅赛德斯市名为“扬”的大屠宰场的主管。他连蒙带猜可以听懂些荷兰语,还差不多能明白边境的通用语。
《哥门索罗封地》的第二版开印时,聂伦斯泰因在弗赖本托斯隐退了。在梅德伊罗家族出租的大宅里,他得以全身心地开始重编一部手稿已失传、书名也被人遗忘的巨著。就在那里,在一九三五年的炎炎夏日中,阿特洛波斯[7]的剪刀剪断了这位诗人执着的工作和修士般的生命。
六年后,对文学颇感兴趣的《最新时刻》的主编找到我,委派给我一个任务,请我秉持探索精神、心怀悲悯之情,在当地展开对那部巨著遗稿的调查。报社在理所当然地犹豫了一下之后,决定帮我负担那一趟闪着“珍珠的光泽”的乌拉圭水路旅行的路费。在弗赖本托斯,一位药师朋友——兹瓦格医生——则慷慨地替我解决了余下的花销。这一段短途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家外出,心中充满忐忑,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理解,说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尽管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地图的考验,但一位旅人笃定地告诉我,乌拉圭人和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这一点让我平静了许多。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在我们的兄弟国家下了船;三十日上午,由兹瓦格陪伴,在卡布罗酒店喝下了第一杯添了乌拉圭牛奶的咖啡。一位公证员加入了我们的对话,在谈笑间给我讲了一个旅途中的商人与羊的故事,同时还不忘调侃我们亲爱的科连特斯街上的有趣氛围。我们走上了烈日暴晒的街道,任何交通工具都显得很多余,过了半小时,在对当地的惊人发展赞叹了一番之后,我们走到了诗人的大宅。
房主唐·尼卡西奥·梅德伊罗用酸樱桃酒和加奶酪的面包招待了我们,并讲了那个永远新奇且诙谐有趣的老处女和鹦鹉的轶事。随后,他向我们表示,感谢上帝,大宅得以翻修,但已逝的聂伦斯泰因的书房却没有被动过,因为目前仍旧缺乏资金来改善它的状况。这的确是实话,我们瞥见了松木书架上的大量书籍,工作台上摆着一瓶墨汁,一座巴尔扎克的胸像正望着它沉思,墙上挂着一些乔治·穆尔的家庭肖像画和相片。我把眼镜架起来,开始公正地检视已覆满尘土的书卷。一本本黄色的《法兰西信使》如我们所预想地那样摆放在那里,这本杂志曾经办得非常成功;此外,还有本世纪后期最优秀的象征主义作品、几卷不完整的波顿所译的《一千零一夜》、玛戈皇后的《七日谈》,以及《十日谈》、《卢卡诺伯爵》、《卡里拉与迪姆那》以及格林的童话。聂伦斯泰因亲笔注释的《伊索寓言》也没有逃过我的双眼。
梅德伊罗同意我再去看看工作台的抽屉。我花了两个下午完成这项工作。关于自己誊写的那些手稿,我不会发表太多意见,因为普洛贝塔出版社已经把它们出版给公众了。虽然某位刻薄的评论家曾经抨击聂伦斯泰因风格上的浮夸以及过于频繁的离合体及离题手法的使用,但格洛萨和波利契内拉的乡村田园诗,莫斯卡尔达的兴衰变化,奥克斯博士在寻找贤者之石时的痛苦,已经永久地融入了拉普拉塔河流域文字最紧跟潮流的实体中,不可抹除。另一方面,尽管《行进》杂志最严苛的评论曾经对这些作品的优点赞赏有加,但由于它们过于简短,所以仍旧没能构成我们的好奇心所搜寻的那部万能杰作。
不知是在马拉美哪部作品的最后一页,我遇上了聂伦斯泰因·索乌撒的批注:
很奇怪,马拉美如此渴望绝对,但却在最不真实、最多变的东西——言语——中寻找它。没有人会忽略,言语的含义变幻不定,在未来,最有威信的词语应该是“轻浮的”或“不稳固的”。
我当时还得以将一行十四音节诗句相继出现的三个版本誊下来。在草稿上,聂伦斯泰因写道:
为记忆而活,却几乎遗忘一切。
在《弗赖本托斯的微风》——那是一部只比家庭内部出版物勉强正式一点的作品——中,他更倾向于这样表达:
为遗忘,记忆收集各样的材料。
最终版的文字出现在《拉丁美洲六诗人诗集》,是这样呈现的:
为遗忘,记忆升华此前的储备。
另一个有力的例子由这行十一音节诗句提供:
我们仅在失落之物中得以延续。
这句话被印刷出来之后则变成了:
坚持着,并被铭刻于流动之中。
哪怕是最粗心的读者都会发现,这两处出版后的文字都没有草稿上的庄重。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只是,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找到了事情的关键。
带着某种失望情绪,我启程返航。替我承担了旅费的《最新时刻》的主编会怎么说呢?NN和我分享了同一个寝舱,给我讲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故事,都很下流,有的甚至让人难以忍受,他的贴身陪伴让我完全无法振作精神。我想多思考一下聂伦斯泰因,但那健谈者一刻安宁都不愿给我。直到清晨,晕船的我打了几个迷迷糊糊的小盹儿,勉强把睡意和厌烦都掩在了里面。
现代潜意识的反动诽谤者拒绝相信南港码头海关的石阶给出了谜题的答案。我向NN表达了祝贺,恭喜他拥有超群的记忆力,随后又抛出了惹人厌烦的问题:
“您是从哪儿听的这些故事啊,朋友?”
回答印证了我粗暴的猜想。他说所有故事,或者说差不多所有故事都是聂伦斯泰因叙述给他的,剩下的则是尼卡西奥·梅德伊罗讲的,后者曾是逝者聚谈会上的座上宾。他还补充说,有趣的是,聂伦斯泰因讲得非常差,当地人还帮他改善了许多地方。突然间,一切都明了了:诗人对于达到绝对文学的热望、他对于言语转瞬即逝性的怀疑论调的观察、那些诗句在作品间的渐进性的耗损恶化,以及书房的双重特点——从象征主义的精美文字到叙事文类作品汇编。这故事并不让我们惊讶;聂伦斯泰因重拾了从荷马到杂工厨房乃至俱乐部的传统,他乐于编事件和听事件。他把自己编的故事讲得很差,因为他知道,如果值得的话,时间会像打磨《奥德赛》和《一千零一夜》那样打磨它们。就像回到了文学的初生时刻,聂伦斯泰因将表达限制在口头范围内,因为他知道,岁月会将一切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