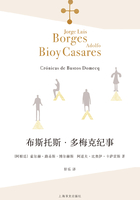
第2章 致敬塞萨尔·巴拉迪翁
毫无疑问,当代评论界已达成一种共识,众人都一致称颂塞萨尔·巴拉迪翁作品的繁复多样,赞美其永不枯竭的热情精神;然而,我们不该忘记,共识的形成总有它的道理。同样,我们也难免会提起歌德,不乏有人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联系,是因为这两位伟大作家具有相似的外貌,并且,相对偶然地,他们都曾写过一部《艾格蒙特》。歌德说,他的精神向所有方向的风敞开;巴拉迪翁则避开了这样的断言,的确,他的那一部《艾格蒙特》中没有类似的表态,然而,他所留下的变幻多样的十一卷巨著却证实了,他本人完全可以接受这样的开放态度。歌德与我们的巴拉迪翁都向众人展示了他们的健康和强壮,那是构筑天才作品最好的基础。艺术的俊美农夫,他们双手掌犁,坚定地分开菜畦。
铅笔、雕刀、纸擦笔以及照相机令巴拉迪翁的形象深入人心;对他广为传播的肖像,我们这些认识他本人的人似乎抱持着不公正的轻视态度,因为那形象并不总透着大师本人所散发的威严与男子气概,那仿佛持久、宁静,却不至于耀人眼的光辉的男子气概。
一九〇九年,塞萨尔·巴拉迪翁在日内瓦担任阿根廷共和国领事;在那里,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废弃的公园》。这一被当今的藏书家们竞相争夺的版本是由作者本人努力校对的;然而,毫无节制的印刷错误令其失色不少,因为当时那位加尔文派排版工是位彻彻底底的西班牙语白字先生。对小史大感兴趣的人应该感谢一段如今已无人记得并十分令人不悦的插曲,它唯一的好处就是清楚地阐明了巴拉迪翁文体学概念那几乎不道德的独创性。一九一〇年秋天,一位重要评论家将《废弃的公园》与胡里奥·埃雷拉·伊·雷西格[4]所著的同名作品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意图得出巴拉迪翁——还请诸位忍抑笑意——抄袭的结论。出自两本书的大量引文被放在平行的两栏文字框中出版,据评论家本人所讲,证实了他所提出的非同寻常的指控。然而,这一指控终究落得了一场空;读者们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巴拉迪翁本人也没有屈尊回应。我并不想记起那位小报作者的名字,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永远地保持了沉默。不过,显而易见,他的评论实在是盲目得惊人!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九年,巴拉迪翁的多产简直达到了非人的程度:他以迅猛之势接续出版了:《奇异之书》、教育小说《爱弥儿》、《艾格蒙特》、《德布希阿纳斯》(第二辑)、《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从亚平宁山脉到安第斯山脉》、《汤姆叔叔的小屋》、《共和国首都划分时期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法比奥拉》、《农事诗》(奥乔亚译本)、《论占卜》(拉丁语著作)。就在他全情工作时,死亡降临了;据他的挚友证实,在去世前,他的《路加福音》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那是一部《圣经》风格的作品,可惜没有留下草稿,想来如果能读到它,将会是有趣至极的。[5]
巴拉迪翁的方法论是如此多评论专著、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以至于任何新的总结都显得冗余。我们只需大致概括就已足够。它的关键思想已被法雷尔·杜·博斯克在其专著论文《巴拉迪翁—庞德—艾略特之共性》(Ch.布雷遗孀书局,巴黎,1937)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来,那便是“单位的延展”。通过引用米利亚姆·艾伦·德·福德的文字,法雷尔·杜·博斯克清楚地将这一点阐明出来。在我们的巴拉迪翁之前及之后,作家们从共享资源中挑选使用的文学单位都是词语,顶多是习语。仅拜占庭的或中世纪僧侣的诗文汇编将审美范畴放宽,收选了整段整段的诗句。在我们的时代,一个抄袭《奥德赛》的片段为庞德《诗章》中的一篇拉开了序幕,T. S.艾略特的诗作中则包含有戈德史密斯、波德莱尔及魏尔伦的诗句,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不过,一九〇九年时,巴拉迪翁就已经走得比这更远了。这么说吧,他吞下了一整部作品——胡里奥·埃雷拉·伊·雷西格所著的《废弃的公园》。莫里斯·阿布拉莫维奇私下吐露的话语向我们揭示了巴拉迪翁在面对诗歌创作的艰苦任务时所怀有的细致的顾虑和近乎无情的周密:比起《废弃的公园》,他更偏爱卢贡内斯的《花园的黄昏》,不过他并不认为应当把它模仿出来;相反地,他承认埃雷拉的书在他可能写出的作品之内,在自己的文字中,他已经把这层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巴拉迪翁为书冠上自己的名字,印了出来,没有删除或添加哪怕一个逗号,这是他一贯的原则。在我们面前的,是这个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事件:巴拉迪翁的《废弃的公园》。事实上,比埃雷拉所著的那本同名书更早的书,无论多古老,都会重复更早以前的某部作品。从那一刻起,巴拉迪翁就接受了此前没有人尝试过的任务,那便是潜入自己的灵魂深处,出版能表达那灵魂的书籍,但绝不为已经存在的沉重书库增加负担,也绝不会落入那种“写出了一行字”的廉价虚荣。在东西方的图书馆为他举杯致敬的盛宴上,这位先生怀着永不消减的谦逊,拒绝了《神曲》及《一千零一夜》,仅出于人道考虑,和蔼可亲地屈尊接受了《德布希阿纳斯》(第二辑)!
人们并不清楚地知晓巴拉迪翁思维演化的全部过程;比如,没有人可以解释那座从《德布希阿纳斯》等作品通往《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神秘的桥。我们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抛出我们的假设:这样的创作轨迹是正常的,是一位超然于浪漫情绪波动之外的伟大作家会走的道路,他终将在经典作品那超乎寻常的宁和中加冕为王。
让我们在此澄清一下,巴拉迪翁一直置身于学院遗风之外,完全无视已死去的语言。一九一八年,带着那如今令我们动容的羞涩,他参考奥乔亚所译的西班牙语版,出版了《农事诗》;一年之后,已经了解了自己精神广度的他又出版了拉丁语版的《论占卜》。是什么样的拉丁语呢?西塞罗的拉丁语!
对于一些评论家来说,在出版过西塞罗和维吉尔的文字之后再出一部福音书,包含着某种背叛经典的意味;而我们则更愿意在这巴拉迪翁没有走出的最后一步中,看到一种精神上的创新。总而言之,那便是由异教走向基督信仰的一条神秘却明晰的路。
没有人能忽视,巴拉迪翁不得不自己出钱来出版他的书籍,且印数少之又少,从未超过三四百本。事实上,他的所有书都一售而光,那些受到慷慨眷顾,有幸得到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读者纷纷被作品极其特别的个人风格所吸引,渴望着能一读《汤姆叔叔的小屋》为快,但这部作品可能已无处可觅了。正因如此,我们要鼓掌致意,赞美极端反对派的议员代表的壮举,他们在坚定地支持我们文豪中最具原创性、多样性的那一位的官方作品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