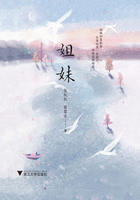
西湖宝石山
从小学到中学,在杭州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宝石山。
那时候的宝石山叫作“保俶山”。山下有一条保俶路,山上有一座保俶塔。相传保俶塔始建于一千多年前的吴越国王钱弘俶时期,是吴越国宰相吴延爽为佑国王钱弘俶应召去京(开封)平安归来而建。另一传说为五代的后周年间,信奉佛教的吴延爽,为了安放唐朝高僧东阳善导和尚的舍利,在湖边的山上建了九层高塔。至北宋咸平年间,一位被人尊称为“师叔”、双目患疾的和尚永保,募缘十年重修此塔,人们感其精神并以作纪念便称其为“保俶塔”,之后的宋、元、明朝一直都称之为“保俶塔”。明万历七年(1579年)重修为七层楼阁式,可登临远眺。民国十三年(1924年)塔倾斜,重修为八面七级实心砖塔。保俶山改名为宝石山,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
20世纪60年代,我家就住在延安路观桥一带,往西走经过狮虎桥,就到了少年宫(昭庆寺)广场。穿过广场(不要往白堤方向)拐入保俶路,路西百十米有一个斜坡小路口,是保俶山的后山入口。上小学的时候,我由父母带领去爬山,上中学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去爬山,多半都从后山上山。那条小道要比走葛岭那边的正门轻松近便,经年残损的石阶缓缓而上,渐而陡峭,经过一座小凉亭,再往上走几分钟,即可登上山顶。
山顶有一大片平缓的空地,空地中央立有一座砖塔。那座塔的形态很特别,像一把收拢的雨伞。塔尖上有一柄长长的锥子,直指云天,像极了雨伞的伞尖。那件黑色的铁器底端盘着一圈图案,像两个对拢的大钩子,听人说那是明代旧物。杭州多雨,每到下雨天,我在城区望着远处雾蒙蒙湿漉漉的保俶塔,就会有这种雨伞的联想,觉得它会突然撑开来,撑起一把巨伞,把整个湖面的雨水都罩住……
小时候上山,站在塔下,需要抬头仰视它。每次去我都会认真数一数它共有几层。下次去又数错了(其实是七级)。围着塔转一圈,可惜塔上一扇门也没有。那是一座实心砖塔,不能去里面一探究竟。
保俶塔的造型奇特,塔形细长。成年后我去各地见过很多塔,从未见过像保俶塔那么“苗条”的塔。有时候就觉得它像一个清高气傲的瘦姑娘,赌气离家站在这里看西湖,唤也不回。
保俶塔下的那块大空场,围着一圈石凳,朝后山方向走几步,就可以眺望后山的情形,就像如今从高楼上往下看立交桥的车流那样。
阳光或是雾气下,眼前突兀地冒出半座城池,许多许多黑黑白白的屋顶,高高低低的平房和楼房,在山下朝着远处一片片一幢幢摊开去,有一种千家万户的气象。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千家万户”的屋顶,就是在保俶山上,那是西湖背面的俗世景象。以后每次上山,都要站到那个位置,好奇地朝山下看一会儿。那些平房多半又旧又脏,楼房倒是很新,但也不高,记得女生们兴奋地辨认着山下的建筑物,指指点点说这是杭州城西北的文教新区呢,所以才有这么多新房子。忽然有人惊呼那片淡黄色的楼房和校园就是杭州大学,又有人尖叫看见了我们杭州一中赭红色屋顶的大礼堂,还有人认出了大运河边的卖鱼桥码头(我不太相信)……我们为此争吵辩论,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惊起树林里一群群小鸟。
杭州老城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大片黑屋顶。
从保俶山上看杭州老城,像一卷黑白的底片。
后来,那座山更名为宝石山,那座塔,也就称为宝石塔了。
我一直都很喜欢保俶山。因为它生动有趣,通达四方,亲近而亲切。
从“千家万户”那儿转过身,沿着山脊上的小路往西走,路边有石凿的水池,清泉从池壁上一滴滴渗出来。一路走过石壁、钻过石室、穿过石洞,头顶的巨石好像随时要掉下来。但下次去看,它们还在原来的位置上,稳稳当当卡在两山之间。石洞的石壁上有摩崖石刻,只剩风蚀雨淋的模糊字迹。继续往前,山路渐陡,两座笔陡的石壁之间,有一条几乎要“撞山”的嶙峋裂谷,我们瘦小的身子灵巧地从窄小的“一线天”里钻过去,那是每次上山屡试不爽的壮举。过了这道窄缝后,天空豁然开朗,眼前是更多的巨石,一块接一块,像巨人搭建的积木,石壁上嵌着斑斑点点的赭红色小石子儿。其中有一座浑圆的“馒头山”,石面光滑、石上无阶,没有栏杆或树杈可助力,全凭自己的双脚,弯下腰匍匐着手脚并用,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再爬,费力地攀爬,你拉我扯,差一点就会落在巨石间的夹缝里。那是最开心的时刻,惊险、刺激,尖叫、欢笑。终于爬上去了,山风骤然加大,身子差点被吹跑了,站稳脚,探头往山下望去,哇哦,就好像一个大舞台,忽然转换了布景。刚才保俶塔下那座黑白的杭州城,顿时变成了一个五颜六色的西湖——
从保俶山顶往下看西湖,淡绿色的湖面平静如镜,细长的白堤就像一条绿色的丝带,断桥上圆圆的桥洞,像只睁大的眼睛一亮一闪。孤山和苏堤在湖的一角连起来,好像在一个糖果盒子上打了一个蝴蝶结。小瀛洲像一个顺水漂流的花环,湖心亭好似一只翠绿的发夹,把湖面的波浪夹住了。一只只游船变得小小的,像一片片竹叶荡在水上。西湖那么乖那么安静,就像我们上课的样子。
离家的多年中,我一次次回想在山顶巨石上看到的西湖,那是我记忆中最完美最清晰的西湖,像一只精致的立体沙盘,固化在我记忆中。
很多年以后我读《西湖志》,知道了保俶山改名为“宝石山”并非空穴来风,宝石一说原有出典:保俶山的地质构成为火成岩,岩石上那些彩色的小石粒,在傍晚或清晨的阳光下,会发出流光溢彩的光泽,故誉为“宝石流霞”。
隐约记起来,就在当年我们攀爬“馒头山”的地方,有一块摩崖石刻,“宝石流霞”四个字清晰可见。但那时候我们并没有留意那些年代久远的古迹来历,我记住的是宝石山的生动有趣,它是一座可以“玩”的山。
喜欢宝石山,还因为它是一座四通八达的山。从山上可以到达西湖北岸的任何一个景点。
从“巨石阵”那里下来继续往前走,沿着石阶往上再往上,山路逐渐陡峭,需要“爬”上好一会儿,才能到达初阳台。初阳台建在一座山峰的制高点,一座两层高的楼台,面东,可望日出。西湖景点的地名都起得风雅,初阳台,意指清晨第一线阳光到达之地,可惜我从来没有下决心来此地看过日出。初阳台是一个必经之地,在这里山路呈三角形分岔,有好几块牌子指向不同的去处:“紫云洞”“黄龙洞”“岳庙”……还有一条路可直接下山。每次站在这些路标前,脚步就迟疑起来,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好了。后来一年一年、一次一次地走,过了好多年,才把每一个方向都尝试过了。
从初阳台翻山往岳庙方向走,有宽大的石阶,顺山势忽上忽下,两边是竹林还有松树林随行,忽高忽低。山顶上出现了一道延绵数里的山脊,平坦的黄泥小路顺着山势蜿蜒。路的一侧临湖,山下是波光粼粼的西湖;另一侧靠山,满山是苍翠的马尾松树林。贴着路边,一棵棵松树一溜排开延伸几里地长,很是壮观。山里人踪罕至,年复一年,松针在树下落了一层又一层,吹撒在小路上,小路变得松软且有弹性。
“文革”那几年,同学们闲来无事,在西湖周边四处游逛,把周围的山林都走遍了。有一回,燕君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地方,保俶山翻山往岳坟的那条路上,有很多松树,那里的松树会唱歌,就唱那个歌剧《江姐》里的一句“松涛阵阵哎,如海啸呦喂……”,不信下次我带你去。后来我真去了,走在那条山脊小路上,山风从松林里一阵阵穿过,满山的松涛抖动;风从一根根密密的松针缝隙里穿过,风变细了,发出窸窸窣窣的嘘声;风大了,松涛声也加大,变成了唰唰的下雨声。山风掀起我的衣服吹起我的头发,我身上也发出了窸窣的响声,好像在给松涛伴乐,整个人都淹没在松涛里了。
杭州人也不一定知道,宝石山山脊上,有一条奇妙的山路,松涛起伏,如诗如歌。宝石山就是这样一座会发出声音的山。
我十九岁去东北下乡后,有一年冬天在小兴安岭林场伐木,满山的红松樟子松,站在树下的雪地侧耳倾听,松涛阵阵,猛烈而强劲。松涛起伏的声响唤起了我对保俶山的记忆,一串串泪水冻在面颊上……
有一年,从初阳台翻山去黄龙洞,黄龙洞位于栖霞岭后的山麓上,左右二山夹峙,路旁漫山翠竹,景色清幽。石阶从郁郁竹林中穿过,阳光细碎斑驳地落在小径上。望见竹林深处白墙黑瓦隐隐的农舍,一株秀气的白梅、几株艳丽的红桃,从墙上好奇地探出头来。过剑门山、白沙泉,前面出现了一座厚重高大的黄墙,传来哗哗的水声,哦,“黄龙”真是先声夺人。还须再步行一段,进得山门,只见一股水帘般汹涌的瀑布,从“黄龙”的嘴里吐出来,水柱跌落池中,水花纷溅,有一条石板通往池中央。想必这“黄龙”吐出的水,就流到西湖里去了。
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有一次我从北大荒农场回杭州探亲,曾和妈妈一起去爬宝石山。那一次,我们执意想要去山里寻找“紫云洞”,紫云——多美的名字啊,妈妈赞叹。洞口飘着紫色的云霭,我们从云雾里钻出来,披一身紫色的云霞,想想都令人激动……我和妈妈两个人,在山路上走了很久,按着路标的指示牌,来回寻找“紫云洞”那个小小的岔口。发黄的松针落在我们肩上,枯萎的竹叶落在我们鞋上,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找到“紫云洞”,这个“紫云洞”好像消失在云里雾里了。我们走累了,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下来吃橘子。妈妈安慰我说:“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我们可以想象紫云洞啊,也许比看见了更好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紫云洞安在?妈妈已经离去,长眠于钱塘江边的山坳里,西湖的另一侧。我们可以想象紫云洞啊——宝石山有妈妈留下的声音,空谷悠长。
那几种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首宝石山奏鸣曲。
喜欢宝石山,因它有趣,因它通达,因它歌唱,因它友好。
说友好,是它就坐落在城边,如此随和,易于登临。山不高,缓缓地匍匐着,若是站在白堤的断桥上,面朝北里湖,隔空相望,只一眼,整座宝石山柔和起伏的山影尽收眼底。山影倒映在湖水里,伸手可及,湖与人是亲近的。目光越过郁郁葱葱的南坡,越过北山街宝石山“正面”隐约的葛岭黑瓦黄墙,山顶突起的巨石上,总是有几个小小的人影在朝山下挥手。曾经,我也是那几个小人影之一。
说宝石山的友好,与我别有一层含义。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它曾庇护过那个小小的人影。“文革”开始后的那年夏天,有一天,有人来找我问讯别人的事情,并说让我明天下午老老实实在家里等着,他们要带我去开批斗会。那一夜我很紧张,父亲正在交代“问题”,母亲也被贴了大字报,我可不想去开那个批斗会。我去找同班同学燕君商量,她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浙江话剧团宿舍。燕君说:那你就躲起来,他们找不到你,就没有办法了……可是我躲到哪里去呢?燕君的爸爸前不久自杀了,我不敢去她家。我到哪里去躲呢?想来想去,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保俶山,山那么大,他们肯定找不到我。
那天午饭后,我拿了一本书,慌慌张张地逃上了保俶山。天气很热,我满头大汗地在山上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一块平整的石头,隐蔽地藏在一片树荫下。我钻进去,坐在石头上看书。树荫像一顶蚊帐,把我罩起来,石头清凉凉很舒服,四周静悄悄很隐蔽,除了知了,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我低头看书,其实一行字也没看进去。前一晚没睡好,我的眼皮发沉,越来越困倦,身子不由自主地歪倒在石头上,在知了的催眠曲中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暗下去。我捡起掉在地上的书,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在山上睡觉呢?我挠着胳膊和小腿,小虫子咬的包好痒,但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没人发现我,也没人打扰我,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可惜我一直想不起来我在山上做了梦没有,唯有保俶山的石头和树荫,永远留在了我记忆中。傍晚我忐忑地回到家,才知道并没有人来过。那座山像一扇巨大的屏风,隔离了山下山外的一切苦烦。谢谢你,保俶山。
那个小人影后来长大了。若干年里,我在山上望西湖,见识过晴湖、雨湖、雾湖、月湖,还曾见过——夜湖。夜湖值得一记,俯瞰西湖的四季风光、日月阴晴,断不可错过宝石山上这一居高临下的观赏平台。
前些年在杭州,一日晚间友人聚会,餐毕,一群女友由杨芳菲带领,去宝石山爬“夜山”。后山的山路无灯,台阶却级级分明,好像整个城市的灯光都反射到这里来了。众人脚步轻快,一会儿工夫就上了山。从山上往下看西湖,白堤苏堤两条长长的灯带,嵌在黑沉沉的湖中,我觉得自己犹如在一架盘旋降落的飞机上,从天上鸟瞰机场停机坪闪光的跑道。三潭印月小岛,变成了一粒浮在水上的夜明珠。对面山上的雷峰塔,被灯光勾勒出一层层宝塔的轮廓,像是钱塘江上的一座航标灯。
保俶塔下那块空场上,有几位白衣飘飘的老者在灯下练拳,何处传来悠长的笛声。抬头仰视保俶塔,它被一圈蓝色的地灯环绕,衬出纤细修长的塔影。几十年过去,那个素裙的瘦姑娘,依然执拗地站在这里。据说塔顶的铁刹已经换过新的了,像是她高耸的发髻上的饰物。今夜她换上了一条蓝色的长裙,在灯光的映照下,露出了一丝羞涩的微笑。
下山后去湖畔居喝茶,无意中一抬头,竟被眼前的景色吃了一惊:宝石山竟然会发光发亮!那是一座荧光灿灿的宝石山,星星点点地洒满了银色、翠绿色的宝石。整座荧光灿灿的宝石山,浸没在蓝莹莹的北里湖中,湖水像缀满了星星的天空,熠熠生辉。我少年时没有见到的“宝石流霞”,终于在半个世纪后的西湖之夜悄然显现。
“宝石”是由悬挂于山坡树干上的串灯组成,灯光汇聚的夜宝石山,显得妖娆神秘。我却依然有些担忧:这无数的灯光炙烤,是否会影响树的生长和鸟的繁育?
遥望葛岭的南坡,我知道那儿有一家“纯真年代”书吧。原址是一家茶室,我小时候爬山常路过这里,偶尔可以吃上一碗加了桂花糖的甜藕粉。
2000年以后,杭州市政府把茶室旧址交给爱书的读书人朱锦绣夫妇,他们把茶室改造成了一家雅致而又有情调的书吧。如今这里常常举办各种读书活动,满屋书香与室外平台周围巨大的香樟树的气息难分彼此。书香熏陶着杭州城的爱书人和南来北往的游客,书吧的灯光融入了西湖的夜色和宝石山的灯海里。
有了这家书吧,书中自有开采不尽的宝藏,宝石山从此日夜“宝石流霞”。宝石山也因此成为一座真正令人亲近的山,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