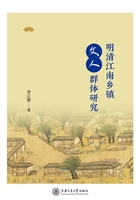
一、文人群体与地方文化传统
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社会生产技术得到较大提升,土地也得到了开发。正如学者张家驹所指出的那样,自东晋至北宋末年,“南方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中心,逐渐由南北平衡发展转而南方超出北方水平”,并且自南宋起“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了北方”。 至明清时期,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南方尤其江南地区已成为中国的大粮仓,掌握着经济命脉,是国家漕运必须依赖的根本。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人口也迅速增长。据学者吴建华研究,明代洪武年间,应天(今南京)、镇江、苏州、松江(今上海)、常州五府的土地面积32134平方千米,人口706.9万,而当时包含这五府的南直隶共有8府,面积总和92007平方千米,人口为895.4万,江南五府以占南直隶约34.93%的面积养活了占南直隶约78.95%的人口。
至明清时期,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南方尤其江南地区已成为中国的大粮仓,掌握着经济命脉,是国家漕运必须依赖的根本。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人口也迅速增长。据学者吴建华研究,明代洪武年间,应天(今南京)、镇江、苏州、松江(今上海)、常州五府的土地面积32134平方千米,人口706.9万,而当时包含这五府的南直隶共有8府,面积总和92007平方千米,人口为895.4万,江南五府以占南直隶约34.93%的面积养活了占南直隶约78.95%的人口。 在这一背景下,江南地区的乡镇社会也进入发达的市镇经济时代。
在这一背景下,江南地区的乡镇社会也进入发达的市镇经济时代。
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是江南乡镇社会的精英教育极为发达。这恰如清代成书的《震泽镇志》所概述的那样:
吴下风俗,古所谓轻心者,于今观之信然。震泽镇僻处县治西南隅,与湖州之乌程接壤,视郡邑为淳厚,范少伯之遗风、陆鲁望之高致,犹有存者。迨宋三贤设教于斯,而人习诗书、户闻弦诵,殆骎骎日上矣。宝祐间,山长沈义甫继之,建义塾、立明教堂,以淑后进,元初遂升为儒学,一时被薰育登仕版者几三十人。迄明季而士尚气节,故复社之兴,沈应瑞、吴允夏等实始其事,虽未免标榜之习,而异时之清风亮节,未必不自平日切磋也。至国朝,人才接踵,政事文章遂甲一邑。猗与盛哉。![[清]纪磊,沈眉寿纂:《震泽镇志》卷二“风俗”,见谭其骧,史念海,傅振伦等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369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从江南乡镇文人知识分子对明代复社的重要影响,和其人员构成的主要来源看,可知当时江南乡镇的精英教育是极有成就的。又如湖州的菱湖镇“人物之荟萃,舟航之环集,甲于湖郡”。![[清]孙志熊纂:《菱湖镇志》卷首“序”,见谭其骧,史念海,傅振伦等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766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另一方面,江南乡镇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教育水平也远超其他地方。据明代后期朝鲜人崔溥说:“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巷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
另一方面,江南乡镇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教育水平也远超其他地方。据明代后期朝鲜人崔溥说:“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巷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朝鲜]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中国行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从崔溥在中国的见闻描述可知,当时中国南北地区基础文化教育差别明显,江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普遍较好,以至于贩夫走卒皆能知书识字。
从崔溥在中国的见闻描述可知,当时中国南北地区基础文化教育差别明显,江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普遍较好,以至于贩夫走卒皆能知书识字。
较高的社会识字率说明江南地区的文化教育足够发达,人们的文化教育意识较自觉。学者刘梦芙指出:“士人读书讲学之风,遍及徽州六邑,书院与家塾星罗棋布,民间重视文化教育的程度远越他郡。”![[清]吴翟辑撰,刘梦芙点校:《茗洲吴氏家典》,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点校前言第18—20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而文化教育的自觉和经济的发达必然会给江南乡镇培养和造就出大量的文化知识群体。对此,早在清嘉庆十六年任宝苏局协理官同里巡检司职的钱江人陈锡华在《同里志序(陈序)》中就已明确指出过,他说:
而文化教育的自觉和经济的发达必然会给江南乡镇培养和造就出大量的文化知识群体。对此,早在清嘉庆十六年任宝苏局协理官同里巡检司职的钱江人陈锡华在《同里志序(陈序)》中就已明确指出过,他说:
嘉庆乙丑夏,余分巡斯土,见其地平奥衍沃,四面环抱叶泽、庞山、九里诸湖,镇独负土而起。此中鸡犬桑麻,民淳俗厚,自宋元以来,儒士大夫彬彬辈出。虽蕞尔地,无异通邑大都焉。……同里钟四湖之秀,五百年来贤人君子相继而起者,指不胜屈。![[清]周之桢纂,沈春荣,沈昌华,申乃刚点校:《同里志》“旧序”,见同里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编:《同里志(两种)》,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6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事实上,根据大量明清江南乡镇方志的记载,我们可以轻易地证实这一结论的可靠性。如《道光休宁县志》卷一“风俗”载引赵汸的《商山书院学田记》云:
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成德达材之士为当世用者,代有人焉。![《道光休宁县志》卷一“风俗”,转引自[清]吴翟辑撰,刘梦芙点校:《茗洲吴氏家典》,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点校前言第18—19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据学者赵华富《宋明清徽州六县进士统计表》的研究统计,宋以后,徽州许多世家大族科第蝉联,三代录取进士人数多达二千一百三十四人。 这些对于地方文化知识群体的概述正可以说明江南乡镇社会在明清两代的发达情况。
这些对于地方文化知识群体的概述正可以说明江南乡镇社会在明清两代的发达情况。
具体以某一市镇或村来看,其情形也大体如此。例如同里明清两代,以文学有名的人物,志载者有:石益、陈谟、徐彰、陈玠、陈琮(父丈德)、朱焕、陈序、周国新、陈理、李瓒、沈泰衡、顾曾贯、顾曾瑜、章名登、顾润先、陆府定、马士节、陈元龙、周爰谘(子纯如)、沈介立、朱镒、任士奇(父用)、王景望、王化源、许士焕(孙兆岩)、朱鹤龄、章梦易(子复)、章学易、朱、顾栋南、叶丹桂(子盛云)、袁之华、顾伟、周爰诏、朱穆(子寅旸)、殳讷、陈、袁潢、陈自振(子沂)、计朱培(弟濂)、周戬穀、陈自焕(子毓德、毓贤、毓秀)、马云襄(子贻良)、周杭、周俊济、王本、王文炳、范孙蕙(子汝桢、鸿业)、顾倬、袁宁邦(弟定海)、任德成、顾我锜、王前、王杯存、袁栋、王植、王廷锦、顾佑行(子畊)、顾时行(子桂林)、姚岱、任思谦(孙昌诰)、沈凤呜(弟凤翔)、俞希哲、张绅(弟汝济)、严璆、沈懿如、陈毓良、周眘(子南宫)、顾鸣扬、袁景辂、郑德勋、王曾垂(弟曾堉,子祖琪)、陈毓升、史乘长、周羲(父以恕)等,共有100人。![[清]周之桢纂,沈春荣,沈昌华,申乃刚点校:《同里志》卷十四“人物志五·文学”,见同里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编:《同里志(两种)》,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158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以一镇之规模而拥有如此之多以文学有名的人物,足以令人咂舌。如果说同里镇是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巨镇,文教发达,属于比较特殊的个例的话,那么清代苏州太湖中的一个面积仅0.8平方千米的孤立小岛上的甲山村的情况则更能说明问题。据清人孙尔嘉的《孟嘉公甲山志略》“文学”条记载,明代至清道光年间,甲山村共出了王之铖、孙士衡、孙士敬、吴棐、吴雷、孙尔嘉等25位以文学有名的人,其中的王之铖、孙士衡、孙士敬、吴棐、罗某组成的北山五逸在明成弘时名满苏州,而清代的吴淳、吴燮、吴雷父子三人在全国都有一定声名影响。
以一镇之规模而拥有如此之多以文学有名的人物,足以令人咂舌。如果说同里镇是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巨镇,文教发达,属于比较特殊的个例的话,那么清代苏州太湖中的一个面积仅0.8平方千米的孤立小岛上的甲山村的情况则更能说明问题。据清人孙尔嘉的《孟嘉公甲山志略》“文学”条记载,明代至清道光年间,甲山村共出了王之铖、孙士衡、孙士敬、吴棐、吴雷、孙尔嘉等25位以文学有名的人,其中的王之铖、孙士衡、孙士敬、吴棐、罗某组成的北山五逸在明成弘时名满苏州,而清代的吴淳、吴燮、吴雷父子三人在全国都有一定声名影响。![[清]孙尔嘉撰:《孟嘉公甲山志略》“文学”条,见[明]文震亨等撰,陈其弟点校,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吴中小志续编》,扬州: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265—267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再如《安亭镇志》记载,明至清嘉庆年间的文学人物有金濂、张汉辰、沈龄、陈可言、冯淮、冯迁、冯邃、陆郊、沈垹、谢大忠、沈果、张丑、杨湜、阚选、张昉、唐象钧、叶开五、张埕、徐宏化、德余、叶沄、徐杏辅、王晋阶等,共23人。
再如《安亭镇志》记载,明至清嘉庆年间的文学人物有金濂、张汉辰、沈龄、陈可言、冯淮、冯迁、冯邃、陆郊、沈垹、谢大忠、沈果、张丑、杨湜、阚选、张昉、唐象钧、叶开五、张埕、徐宏化、德余、叶沄、徐杏辅、王晋阶等,共23人。![[清]陈树德纂修,朱瑞熙点校:《安亭志》卷十七“人物二·文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304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从所举不同等级的两例可知,且仅及文学人物不及知识学人的例子来看,江南乡镇社会文人知识群体发达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故而,清人周之桢在纂辑《同里志》的人物志时云:“同里地虽一隅,君子之至于斯者多矣。”
从所举不同等级的两例可知,且仅及文学人物不及知识学人的例子来看,江南乡镇社会文人知识群体发达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故而,清人周之桢在纂辑《同里志》的人物志时云:“同里地虽一隅,君子之至于斯者多矣。”![[清]周之桢纂,沈春荣,沈昌华,申乃刚点校:《同里志》卷十九“人物志十·流寓”,见同里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编:《同里志(两种)》,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22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存在大量的文人知识群体,他们对于地方文化不是无干预的,而是发挥着积极的文化建设作用。如清初倪赐纂辑的《唐市志》指出:
唐市,在海虞之东南,地卑而多水,人柔而鲜争,为宋时周孝侯故里,德之所化远矣。自明迄今,文章道德之彦,掇巍科高第者,后先晖映,皆尚气节而重声闻。至于布衣、韦带之士,亦能操觚染翰,以著述相高。![[清]倪赐纂,[清]苏双翔补纂,曹培根标点:《唐市志》卷上“风俗”,见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19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证明常熟县属下的唐市镇在明清时期文化盛兴,文人群起,以至于普通村民也渐染文气。明末清初的松江府奉贤县青村镇更是远近闻名的文化发达镇,时人曾羽王在《乙酉笔记》中记述其家乡的这一事实时自豪溢于言表:
余生长青村,具知盛衰之由。自十余岁以至成立时,文风大盛。凡有子弟者,无不令其读书。每遇试期,应童子试者,五六十人。因具呈于青浦令朱锡元,另立青村一案,以比南邑之附于上海也。每府取十余人,至院试,则并青南两案,送入金山卫考。从此子衿日盛,而海滨称文墨之区,必以青村为首矣。![[清]曾羽王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标点:《乙酉笔记》,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又如清初的吴江同里镇,八十岁的章锡梦在《续同里(川)先哲志序》时也说:
同里环四湖之秀,语云水之方流者产玉,圆折者生珠,是固宜有贤人君子接踵而出焉。又镇治所辖村落不下百区,不特镇有学士大夫,而村落中亦有潜德弗耀、元文处幽者,是恶可以无志?先朝英庙,时里中吴蒙庵先生作《同里先哲志》,迄今世家大族犹有录而藏之者,后之人得以考其人物焉。![[清]周之桢纂,沈春荣,沈昌华,申乃刚点校:《同里志》“旧序”,见同里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编:《同里志(两种)》,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18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再如《南翔镇志》卷六“人物志”云:
古今来地以人传。槎里偏小,而尚论其人,如张司马、李给谏、李庶常兄弟,其勋业、谠论、文章,炳天壤而光史册,岂一乡一里之人哉!若夫处草莽,而行有足取,艺有可观,名流侨寓兹乡,女子守义自誓者不胜书,而不可不书也。至于佛老之徒,其志行高洁,足以传世者,附诸简末。![[清]张承先著,[清]程攸熙增订,朱瑞熙标点:《南翔镇志》卷六“人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42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清人张承先在这段人物志前的概述里,就特别强调了南翔镇文人知识群体的历史贡献和地位,以及其对于地方人文传统的历史影响和人们内心的文化自豪感。类似的文献记载不可胜数,关于文人群体在地方文化历史中的地位与影响的记述,在江南的每部乡镇志、村志里都不会缺席。
文人知识群体是江南乡镇、村社文化传统形成的行动主体,也是文化价值创造与传承的主体,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一直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明代台州府黄岩县林师言撰《林氏族谱》载王叔英序曰:
吾邑东南乡之故族林氏为盛。盖自五代石晋时有讳熙者仕吴越钱氏为黄岩丞,始居于邑之浦东里。熙四世孙有曰仪文者在宋某年间迁居于邑之莘塘,仪文之四世孙有曰某者仕为观察判官,以行继显于时。仪文之若干世孙某者又分居于甓山,若干世孙某者又分居于横溪。莘塘、横溪、甓山三地相去三四十里,而皆在邑之东南。三族者既各蕃盛,故凡居邑东南乡与凡往来者莫不知有林氏焉。在宋元之际登仕之途者难如升天,苟得一资半级之荣往往张声挟势、跨服闾里,自为长雄。或无仕宦之阶而富于资产者亦多自结于贵要之门,以求尊异于凡民。林氏之先当其时有官者既不挟贵以骄人,其无官而殷富者亦皆安居自守,优游田里间。又以诗书相尚而无有附权趋势之风。故其流波遗泽传至于今而其子孙犹有能循蹈规矩,笃学教行以不失先世之遗声者。呜呼!是可以称故族矣。余观世之所谓故族者莫不有籍先世之余光焉。然其先世有以仕宦功业称者矣,有以文学行义称者矣,有以道德闻望称者矣。若其徒仕宦而无功业,有文学而无德义,众人虽尊之,君子弗尊也。然而君子所尊者亦惟尊其身之有者而已。使为子孙而能继其先者,君子固益尊之;苟不能然者,君子不惟不尊之,固益贱之矣。何则为故族之子孙而能继其先者,不徒为其身之荣而尤足为其先人之荣,岂不益可尊乎?为故族之子孙而不能继其先者,不徒为其身之辱而尤足为其先人之辱,岂不益可贱乎?盖为凡民之子孙则人之责望者浅,为名人之子孙则人之责望者深,理固然也。世之妄人不知是理,至有生于名门右族而其行无一善,学无一长者,亦往往挟其先世余荣以高人;亦有其先人徒取仕宦、文学之名而其实无足称,或以多资末技贸取微官及得遥授虚职,至有冒祖他族之贵显者,亦每每号于人曰吾祖为某官,自谓故族子孙以自高而不知耻。其视林氏为子孙贤与不肖何如哉?林氏之子孙其存而最贤以文行著者咸与余友,故余知其先世为详。今为永康儒学训导曰师言者,乃余所谓最贤而以文行著者也。师言以其所修族谱一编征余为序其编首,余不得辞。故既为述其先世之盛而又为之盛道。夫!世俗所谓故族子孙之谬妄者以为其后嗣之戒云。![[民国]喻长霖等纂修:《台州府志》卷七十一“艺文略八·经籍考八·史部五”,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24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又如学者刘梦芙对徽州村落中文人的文化作用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
由于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朱熹生前曾三次回乡扫墓,讲学授徒,其学术思想通过诸多弟子代代传播,形成了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学派。士人读书讲学之风,遍及徽州六邑,书院与家塾星罗棋布,民间重视文化教育的程度远越他郡。更主要的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官学,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士人追求功名利禄,非藉此不可,这更能加深对朱熹的信仰。
……
在宗法伦理方面,徽州同样受朱熹影响极深,各宗族广建祠堂,大修宗谱,制订族规家法,行冠婚丧祭之礼,无不奉朱熹亲定的《家礼》一书为圭臬。《茗洲吴氏家典》李应乾《序》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朱熹思想为《家典》立法的指南,正是研究《家典》必须把握的要领。![[清]吴翟辑撰,刘梦芙点校:《茗洲吴氏家典》,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点校前言第19—20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4133-JQyEvD4cIN3PuKOITkXi1VyIW7emi2zP-0-1c70112c276bbc4dd2dcaddfcf95028d)
综上可知,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达和文化教育的繁荣,文化知识群体日渐兴起,形成较为庞大的社会力量,而这些人在知识教育和文化知识生产与创造上做出了显著的历史贡献,产生了较为深远的社会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