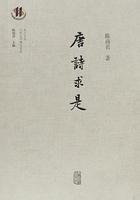
钱锺书先生对拙辑《全唐诗续拾》批评的启示
知道钱锺书先生曾阅读并批点过拙纂《全唐诗补编》,是十多年前的事,具体应在钱先生去世后一二年。中华书局徐俊先生(《全唐诗补编》责编,当时为文学编辑室主任,现任中华书局总编)为《管锥编》续约事到钱家与杨绛先生商谈,见到书橱间有这部书。他先前已经听闻钱批此书着墨很多,很想取出来翻一下,但总觉不太礼貌,没有提出。虽属传闻,但我相信应是真事,也希望此后能有机会领教钱先生的批评指点。
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册《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其中第十册居然收有读拙纂前书的札记,L兄知道后立即告诉我,并将有关几页复印给我,希望我谈些感受。
《全唐诗补编》是我在1982年到1987年间的著作,199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手稿集》来看,钱先生阅读批校的著作以古籍为主,今人著作仅有很少的几部,最晚的是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孝胥日记》,此后大约即因病住院了。拙著能经钱先生阅读且留下记录,确是很大的荣幸,也感莫大的惶恐。此书始纂于研究生毕业第二年,因为偶然发现几位前辈学者所辑《全唐诗外编》仍有未尽,遂不知天高地厚地欲以个人之力披检群籍,广事搜罗,虽自感能够依循目录以求广征存世图书,在唐人佚篇发掘方面也较前人更为丰富,出版后也得到一些中外学人的好评,但毕竟当时读书不多,又没有科学的检索手段来避免重收误收,加上以辑佚为学术目标,虽然当时也小心地规避误收重收,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侥幸多得的心理。出版二十年来,古籍检索手段发生革命性飞跃,自检发现和他人揭发误取者在两三百篇左右,大约占全书百分之四、五。正因为此,该书二十年来没有再版。而我现在对唐诗文献的认知程度,较先前有更清楚的理解,希望不久可以给读者以合适的交代。
钱先生关于拙辑的手稿,在笔记本中共五页,以抄录诗篇内容和出处为主,间附有若干按断。首题“陈尚君全唐诗续拾”。拙书199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册为原《全唐诗外编》的修订本,后两册为我新辑的部分,题作《全唐诗续拾》,取续诸前辈所补而有得之意。估计因《全唐诗外编》钱先生前已读过,修订本有减无增,故仅涉拙辑部分。可惜在《手稿集》中没有见到有关《外编》的部分。他对摘录的诗篇有考按者,一般在诗下加星号,在当页的书眉或页末写下按语,于此可以了解钱先生平日读书之认真规范,一丝不苟。所摘录作者及诗篇凡三十多则。有的仅录作者名,如宋之问、白居易,均加按语,是因按语而存名。有些录全诗,如孙思邈、卜天寿诸诗均录全诗,估计有录而备参的用意。如录孙思邈有关养生诗四则,其中有“美食须熟嚼,生食不粗吞”;“锦绣为五藏,身着粪扫袍”;“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神虚心易役,气弱病相侵”;“夜寝鸣雷鼓,晨兴漱玉津”;“侵晨一碗粥,夜食莫教足。撞动景阳钟,扣齿三十六”。当然不是着眼于诗学,而是看重其养生道理。几年前编本系刘季高先生文集,附收1972年12月《复钱锺书》信,是对钱告“婴喘疾”的回复,告以“除药物治疗、饮食节制外,尚宜有以培其本”,并自述练八段锦、以盐刷牙等办法。从上述摘录,可以看到钱先生晚年对身体状况的关心。至于其他录诗的去取原因,难以一一揣度,容以后再研究。在此仅就有关的按语,略述读后的体会。
先将钱先生的全部按语,按手稿顺序全录如下(编号、按语前括号中文字为我所加。原按仅有少数标点,也均由我增加。手稿识读较为困难,承王水照老师代为辨识,也表感谢):
一、(唐太宗《焚经台》)按此诗早见《全唐诗》无名氏卷,引此诗而断为后人妄托。日本刻小字全藏《四十二章经》宋真宗注,附唐太祖《焚经台》七律,有注甚详,荒诞可笑。《法苑珠林》卷二十六《敬德篇》引《汉法本内篇传》记焚经台事,却道及此诗。
二、(静泰、李荣互嘲诗)何以漏却《太平广记》所收李荣与僧互嘲语?
三、(卜天寿)侧字不解为音同之何字。
四、(宋之问)自《诗渊》辑补多首,无一篇佳者。
五、(惠能偈)观此乃流传本《坛经》改字之妙。
六、(沈佺期)此乃《木兰词》中摘句,编类书者草率误属主名,何以不注明?
七、(孟浩然)此乃府下俗书,窜易孟之《归终南山》起二句耳。浩然布衣,安得赴“北阙”而径辞天子哉!
八、(怀素)误甚,此乃戴叔伦诗,见怀素《自叙》所引,观《自叙帖》影印本即知。(戴御史叔伦……云:“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
九、(贾岛)贾岛《忆江上吴处士》诗:“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千古传诵(《全唐诗话》摘句“生”字作“吹”更佳)。俗类书窜改成此,不知秋风引起落叶、渭水,切近流走而对称,真目无珠而心无窍者。
十、(白居易)未辑《通典》卷四一赞摩尼教五律、《三国演义》104回吊孔明七律,皆伪作也。
十一、(杜牧)《老学庵笔记》载吕夷简《天花寺》诗,明本书袭之,牧翁不知,选入《列朝诗丙集》。此首亦吕诗作贼,徐氏为所欺耳。
以下就各则内容,分别略作申说。
第一则,唐太宗《焚经台》:“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谩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土来。确实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春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我据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七录出,并指出又见宋释子升、如佑辑《禅门诸祖师偈颂》卷下之下,题作太宗《题白马寺》。又加按:“《全唐诗》卷七八六以此诗归无名氏,云‘其声调不类,要是后人妄托’。然此诗征引甚早。《翻译名义集》亦非伪妄之书。同卷录义净三藏诗,亦初唐时人。恐馆臣之意不在声类,而在此诗有玷太宗之盛德耳。义净诗亦误录,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已斥其妄。初唐七律传世甚少,故重录之。”现在看来,当时的按语有失偏颇,没有考虑到初唐不可能出现这样粘对讲究的七律,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但如果要重新编定唐一代的诗歌,我仍建议作为附录备存于太宗名下,因为此诗与我同时据《金石续编》载陕西鄠县金正大石刻《赞姚秦三藏罗什法师诗》,以及据元祥迈撰《辨伪录》卷五所辑缺名赞(《佛祖统纪》卷四五作宋太宗《佛牙赞》),都是七律体的颂佛之作,虽然断然不可作为初唐七律之资料,却是宋元佛教史的重要文献。钱先生提供了有关此诗的两则重要线索,一是关于焚经台的本事,见于《法苑珠林》卷二六《敬法篇》引《汉法本内篇》,叙汉明帝尊佛后,“诸道士等以柴荻火,绕坛临经,涕泣曰:‘人主信邪,玄风失绪,敢延经义在坛,以火取验,用辩真伪。’便放火烧经,并成煨烬。道士等相顾失色。”未载诗,手稿中“却”字是“未”字之误,可知在高宗朝编《法苑珠林》时还没有所谓太宗之诗。另宋真宗注《四十二章经》,今习见者为日本《续藏经》三十七册所收本,附有署“唐太宗文皇帝制”的《题焚经台诗》,后附汉明帝夜梦金人,迎取此经的故事,当然为后世附会,“荒诞可笑”。此一出处为我所未知,只是还不能就此认为北宋前期已有此诗。
第二则,我据僧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录高宗初期内庭僧道互嘲的一些韵语,其中包括僧人静泰、义褒、灵辩和道士李荣的作品。道宣此书是弘佛之著,与《广弘明集》性质类似,但偏于叙事,其中道士颇被丑化。钱先生录了静泰、李荣、灵辩韵语,估计是看重其中一些攻击性的比喻很特别,他所指出《太平广记》所收李荣与僧互嘲语,见该书卷二四八引《启颜录》,《全唐诗》卷八七二已经收在僧法轨名下。我只收《全唐诗》不收的作品,不是疏漏。
第三则,吐鲁番所出《论语》郑玄注后的卜天寿杂写,经郭沫若的评述而广为所知,我也据郭说录二诗于卜天寿名下。现在更赞同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刊《文献》1994年第4期)的说法,卜天寿如同许多敦煌、吐鲁番的学童一样,只是据当时民间流传的诗歌,抄写于文本之末,绝不是诗的作者。钱先生所录的这首是:“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所缺二字据郭沫若、龙晦说补。郭沫若认为侧书就是侧身书写,钱先生似乎不太赞同,但究为何字,看来他一时也无合适解释,因而有所存疑。
第四则,是对新辑宋之问诗歌评赏的看法。宋之问去世后,友人武平一辑其诗文为《宋之问集》十卷。这个本子可能到明代前期还存世,因此在《永乐大典》和《诗渊》中存佚诗约二十首。今存嘉靖后所刻宋之问集则为明人重辑,已非原集。从存录作品的立场,当然应该求备,以适应各方研究之需求,但就唐诗欣赏的立场来看,则补录之诗艺术性是要差一些,毕竟前此已有许多选家和学者做过抉择。附带说到,《诗渊》是明前期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历代诗集,仅有一抄本流传,归北京图书馆后,又长期未编目,到20世纪80年代方为世人所知。我曾试图证明编录者为浙江临海一位水平不高但抄书勤奋的士人,可惜未及成文,根据也不记得了。
第五则,六祖惠能受法偈,传世的契嵩本以下《坛经》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从吴越僧延寿《宗镜录》卷三一所引作“菩提亦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用拂尘埃”来看,此一文本至少在唐末已经出现。而敦煌所出法海本《坛经》,则作二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当然敦煌本更接近惠能思想的原貌,且只要稍通禅理,即可以看到两种受法偈思想的巨大差异。但从文学立场来看,则改本显然更具感染力和号召力。钱先生肯定流传本“改字之妙”,正是从这一立场所作之评判。
第六则,我据宋佚名编《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一四载著名的《木兰诗》中四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收在沈佺期名下,特为录出,并加按云:“此四句即《木兰诗》中后人以为极似唐人所作之句。《万花谷》收佺期《塞北二首》摘句后,又收此四句,署‘前人’,未详编者另有所据抑疏忽致误。今人或主《木兰诗》为唐初人所作。今姑录出附存佺期名下,以供研究者采择。”此四句,今人认为最似唐人诗,有宋人书标述作者,虽然我也不认为据此就可以认为是沈诗,但觉得将其举出还不是毫无意义。钱先生断定此为“编类书者草率误属主名”,批评我“何以不注明”,即认为我所加按语态度还不够明确,我尊重他的意见。
第七则,我据《吟窗杂录》卷一四收正字王玄《诗中旨格》引孟浩然《归旧隐》二句“北阙辞天子,南山隐薜萝”,加按语云:“此二句疑为浩然《归故园作》‘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之异文。”《吟窗杂录》所署南宋状元陈应行撰乃出依托,其初本应为北宋末蔡传所编,今人已有共识(参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所附《吟窗杂录考》)。正字王玄《诗中旨格》大致为五代末至宋初的诗格。唐人诗格内容都较浅俗,录诗也多错误,钱先生讥为“俗书”,不算酷评。《归终南山》即《归故园作》,为本集与《河岳英灵集》诗题不同。至于责问“安得赴‘北阙’而径辞天子哉”,我则有所保留,盖诗人作诗,本非实录,且唐人诗歌常经数度改写,流传中更多变化,故录此以备文献。
第八则,我据明汪珂玉《汪氏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二录“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二句为怀素诗,确属误录戴叔伦诗。
第九则,与前第七则类似。我据《吟窗杂录》卷一三僧虚中《流类手鉴》录阆仙诗“离人隔楚水,落叶满长安”。因为前句不见贾集而补出,后句见于一般文学史称引,当然知道,但交稿时忘加按语说明。当时因为看宋人轶事述晏殊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入词也写入诗,认为贾岛也有这种可能,即予录出。钱先生对诗意解读甚好,所言甚是。稍可补充的是,《全唐诗话》有署名尤袤或廖莹中等数说,其内容肯定全部抄自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只是计书的一个节录本,虽老辈颇重此书,今人则认为一般可以不用。作“秋风吹渭水”的摘句,见《唐诗纪事》卷四〇注明“张为取作《主客图》”,即唐末通行文本就是如此。
第十则,因白居易而提及未辑的两则伪诗,是提示线索,指为后世依托。所云“《通典》卷四一赞摩尼教五律”,可能记忆有出入。杜佑《通典》成书略早于白居易之成名,今所见无论《十通》本,还是中华书局所出王文锦点校本,以及影印日本宫内厅存北宋本,卷四一仅有一则关于摩尼教的敕令,未有录诗,未知钱先生所据为何本。《三国演义》一〇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述诸葛亮死后,“杜工部有诗叹曰:‘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虎帐不闻施号令,麟台惟显著勋名。空馀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好看绿阴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白乐天亦有诗曰:‘先生晦迹卧山林,三顾那逢圣主寻。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托孤既尽殷勤礼,报国还倾忠义心。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杜、白二集皆有宋本流传,均无此诗,可知为明清间人依托,诗还不错,个别诗句可以找到来源,如“辜负胸中十万兵”为南宋华岳《翠微南征录》载《冬日述怀》末句。但绝非唐诗,盖好事者所作,托名家以求其流传。
第十一则,我据民国十三年刊徐乃昌纂《南陵县志》卷四二录杜牧《安贤寺》:“谢家池上安贤寺,面面松窗对水开。莫道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钱先生数言,指出此诗托伪的曲折事实。我据他的指示检索文献,得到以下线索和结论。
吕夷简是宋仁宗时宰执,诗名常为其官名所掩。《天花寺》诗:“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现知北宋时至少被四次称引,分别见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九、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江休复《江邻几杂志》(《诗话总龟》卷一五引)和蔡宽夫《诗史》(前书卷二九引),其中吕希哲为吕夷简之孙,吕公著子,最可凭信。南宋较有影响的引录则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和吕祖谦《宋文鉴》卷二七。吕祖谦也是吕夷简后人,颇存家族文献。
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一六收明初人木青(号松鹤)《太素轩》诗:“盘陀石畔看云屋,一一轩窗面水开。不是避门妨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除首句不同,后三句显然抄袭吕诗,就是不知道是木青本人抄袭还是后来传误,只是钱谦益没有察觉,仍予收入。清初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五指出此“即宋人‘贺家湖上天花寺’诗,近某亦载之明朝诗,何也?”虽未指名,即指牧斋。
此外,《六朝事迹编类》卷下收杨修《横塘》诗:“早潮才过晚潮来,一一轩窗照水开。鉴面无尘风不动,分明倒影见楼台。”此杨修为杨备之误,所引诗为其作《姑苏百咏》之一。杨备与吕夷简同时而年辈稍晚,此诗从吕诗中搬用了一句。
传为杜牧诗,也不始于徐乃昌。今知《嘉靖宁国府志》卷四因前两句作古诗,《万历宁国府志》卷五录全诗而不题作者,《嘉庆宁国府志》卷一四、《嘉庆南陵县志》卷四已作杜牧诗。徐乃昌修志时,沿袭了前志的错误,有所失察,但非有心作贼。
钱先生关于拙辑的读书札记虽然篇幅不多,所涉内容则极其丰富,或指示辑佚线索,或指出作品误收,或说明歧本各有可取,或提示依托在所多有,都足启发思路,指点迷津。当然我因为一直做唐诗文本的研究,在个别问题上的看法容有不同。二十年前古籍无法检索,现在可以随意地检索数千种典籍中的每一个人名和词语,当然在文本处理方面也可以更精密。但我始终相信,仅靠检索猎取文献的做法无法代替第一手的广泛阅读典籍,只有在融会贯通地阅读群籍基础上才能对学术有透彻的认知。钱先生的读书笔记为我们树立了一代学人勤勉读书、独立研究的典范,值得我们长久地学习和体悟。
2012年3月18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