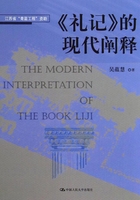
二、何为“乐”
乐就是音乐。作为同是发音载体的声、音、乐是有所区别的,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和境界。人心有感于外界事物的活动表现为声;声相互应和产生变化就形成音;排比音节用乐器加以演奏,用盾牌、斧钺、雉尾、旄牛尾进行舞蹈,就形成乐,“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记》)。音产生于人心,乐通于人情事理,“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记》)。禽兽“知声而不知音”(《乐记》),民众“知音而不知乐”(《乐记》),只有君子“为能知乐”(《乐记》)。审察一般的声能借以了解有节奏文理的音,审察有节奏文理的音能借以了解反映人情事理的乐,审察反映人情事理的乐能借以了解国政民风,从而也就具备了治国的途径。相反,不懂得声就不可以与之研讨音,不懂得音就不可以与之研讨乐,理解乐的功效才能近于理解礼的真谛,“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知礼矣”(《乐记》)。声音之道又是与政治相通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乐记》),音律中的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对应君、臣、民、事、物:“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乐记》),五音协调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五音紊乱、交互侵陵则会产生极端放肆而没有规矩的慢音,慢音也是国家即将面临灭亡的征兆。
“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乐记》)乐是天地和合之道的表现,是中和之气的纲纪,是人情不可或缺的,聆听《雅》《颂》之乐声,会使心胸志向宽广;手执盾、斧之舞具,演习俯仰屈伸之姿势,能使仪容面貌端庄;踏着节拍走在队列的舞位上,可以使人们在行列里能够端正,进退行动能够整齐,“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是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记》)。正乐能使人伦之道为之大清,耳目为之聪明,血气为之和平,能移风易俗,使普天之下都得到安宁,“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凡是乱世之音,悲哀而不庄重,欢乐而不安详,缓慢平易而凌犯节奏,放纵沉迷而忘了本性,动摇通畅之正气,泯灭平和之品德,“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如之德”(《乐记》)。
此外,“乐者,乐也”(《乐记》),音乐就是娱乐。君子之娱在于提高道德,小人之乐在于满足情欲。用道德制约情欲,就能享受娱乐而不至于淫乱;为满足情欲而忘记道德,则会被声色迷惑而得不到真正的娱乐。因此,君子抑止情欲而调和自己的心志,推广正乐借以完成其教育作用。乐教推行,从而人民归向正道,德教的成效由此显现无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乐记》)。古代圣君贤王很重视引起人们感触的外界事物,先王作乐用以效法政治,成效卓越的则能使人民的行为体现高尚的道德,“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乐记》)。
先王作乐是基于“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乐礼》)而成的,集性情、音律、礼义、生气、五行于一体,阴阳刚柔各安于其位,使气质属阳的不至于散慢,气质属阴的不至于闭塞,气质属刚的不至于暴怒,气质属柔的不至于怯懦,在此基础上,圣人“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乐记》),通过制定个体差异的教习等级以增广节奏练习、审查表现色彩以衡量品德高低、规范音律礼记的匀称性以及排比乐章的先后次序以模拟行事作为,使得疏亲、贵贱、长幼、男女的伦理都能体现在乐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