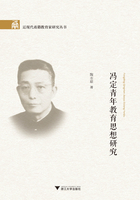
第二节 教科书风波:在北大首次遭受批评
一、任北大本主编,突击编写哲学教科书
1959年冬天,按照中宣部的部署,中央、北大、人大、上海、吉林、湖北都要编出一部哲学教科书。北大本由冯定担任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人很多,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的绝大部分教师之外,还从哲学系的学生中抽了一批人参加。冯定作为主编,就以他向新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路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打破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为“两大块”的方案。一开始讲总论,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统一起来,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渗透在里面;然后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展开论述;最后讲作为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及其范畴。写出的教材初稿分为九章,冯定亲自执笔撰写绪论部分。后面的各部分由师生们分头编写,因为时间太紧,大家各自为战,集体研究讨论并不充分,主编也没有时间统稿审改。编写组内部的思想认识也没有统一起来,各章初稿的水平参差不齐,不尽符合冯定提出的体系方案。中间讲辩证唯物历史观那一章,从劳动生产、人民群众、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战争与和平,讲到教育、文艺、道德、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内容包罗万象,篇幅很长,鼓出了一个大肚子。在很多问题的表述上,又尽量为当时的政策、方针做解释和辩护,因而难免带上“左”的时代烙印。讨论会议要求各本书继续修改,不要搞成“陆定一”(六本定为一本)。
二、教科书“原则性的缺点”引发的冯定专题检讨会
可惜,思虑严谨、学风独特的冯定似乎并不为北京的哲学圈所容纳。
1960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开展以后,冯定色彩浓厚的人生观哲学很容易招致异议。1960年3月,在中央高级党校召开了讨论六本书稿的哲学教科书讨论会,在当时“左”的氛围下,会上的某些意见有些偏激,包括对北大本绪论的意见,有人说它有“原则性的缺点”,这种评断其实是缺乏客观公正性的。听到“原则性的缺点”这样几个字,到会的北大哲学系的人员大惊失色,而这部分正是冯定所撰写的内容,哲学系党总支部书记王庆淑紧张得急忙递纸条给助教高宝钧,让他发言时说事前没看过冯定写的那一章。哲学系党总支部在中央高级党校揭发冯定主编的教科书有问题后,在教学检查活动中抢先布置对冯定的专题检查。可笑的是,就在这之前不久,哲学系还高调总结了冯定的教学经验,并在校刊上醒目刊出。当然,在那个把一切都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年代里,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为了赶快划清界限来自保,知识分子群体里有如此可悲可叹的自相矛盾的举动一点也不奇怪。哲学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冯定的专题检查讨论会,让冯定无法冷静面对。
讨论会后,冯定虽然因为受到批评而颇受打击,但并不气馁,他在1960年5月29日提出了修改的设想。冯定肯定了这次编书的收获:
打破了旧的传统,在理解和体现毛泽东思想上作了努力。他说,就好像演戏新出场的人,打扮得虽然不够好,但红脸总还是红脸。冯定认为初稿有三个问题修改时需要注意,一是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不要单独讲人生观,如果把个人提出的种种人生问题,帮他一个个解释,那样比较被动。二是讲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了很多独立的新的范畴。讲哲学要以今天为中心,立足于当代现实、当代的阶级关系,在这个基础上继承以往对它有用的东西。全书的结构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原来只作为一章还不行,各章之间太不平衡。
从中他归纳出三条原则:一是讲任何问题都要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贯穿社会实践;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讲自然科学问题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此书要与专门的自然辩证法教材有区别;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要分章专门讲。他这次设计的书稿结构共24章,其中有11章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居于全书中心地位。
但是就在冯定提出修改的设想之后没有多久,除他本人之外,参加北大编书的骨干都奉命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同人大和市委党校的同志一起另编一个“北京本”,北大本的修改就被搁置了下来。后来“批判”浪潮接踵而至,也使编哲学教材之事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