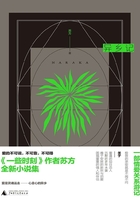
第2章 爸爸
一
陈年曾经恨过王麦的,陈年后来忘了。当时大家都是十二岁,王麦总是梳一个高高的辫子,皮筋扎得相当紧,牢牢揪住头皮。她的眼角因此总是向上吊着,太阳穴拔出青筋来,整天像要去寻仇。
有一个下午,王麦认为自己的辫子不够紧了,需要重新扎辫子。撸掉皮筋的时候,她的同桌陈年看见,那散开来的头发仍然是个辫子形状,没有因为失去束缚而重获自由。陈年猛然意识到,电影里那些一松开发辫就能够魅惑地甩出一头瀑布的场面都是假的,女生的头发是硬的。他心里一惊,又想到女生也会拉屎、淌鼻涕、脚底汗臭、指甲藏泥……他第一次想到这些,像走在路上一屁股掉进井底,好多天眼睛里黯淡无光。从此陈年再看女生,就和从前不一样了。都怪王麦的钢丝头发!他后来就怪里怪气地喊王麦“妇女”,一直喊到几个月后他们永别。同学们不明白其中意思,但也跟着叫了。女老师们听见了很愕然,但并不管,回到办公室里叫陈年“小流氓”。王麦自己最不懂:妇女是骂人话吗?她因为不懂陈年骂的是什么,便不知道如何反驳,只好不理睬,倒像是坦然接受。陈年于是更加恨她。
陈年就是从那时候读起书来——之前也读书,但那是作为男孩子似的读父亲的“大人书”,或是读大人们不许他读、且连大人自己也并不该读的书。七字头的最后一年,陈年看透了女生的真相,开始像个读书人一样读书。几个月以后,他们一家从长江边搬进了北京。他敏锐地发现,对父亲来说,这一次迁徙并不是“赴京”,是“回京”。他们住进崭新的楼房,不过家具杂物是旧的——床柜桌椅,棉被茶缸,一件件打了包从老房里运来,恨不能位置摆放也如前。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仍然是小心的,而陈年与他们的儿子们是初羽的鸟,要放声了。他认定北京就是他的家,对妇女王麦的恨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他越来越乐在其中地读书。他发现世上的书变多了。
如今陈年也到了父亲当时的年纪,身份亦和父亲一样,是个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这词不大被人用了。从前不用是因为风险,如今不用是因为过时。陈年写过书,也教过书,写过剧本,拍成电影,还三不五时参加活动,制成节目,教人读书。过不了几年,他便可以着手撰写回忆录,虽然眼睛花掉了,但他的妻子还年轻,很可以助他完成。如果没有另一个王麦,他的回忆录会是多么洁净统一,翔实忠诚。他想起王麦轻蔑地说他“做都做得,说却说不得”,仿佛这是不对的。
可那正是他的信啊:可做不可说。他的大半生都是这样信过来。他不和她辩,就在深夜里写大字,“不可说”。他曾经害怕王麦,像杯水怕活鱼那样地怕。
二
陈年第一次见到王麦是在南方的海边,他受邀去参加一本杂志的年终颁奖礼。当时的北京是冬天,而南方不是。落地已经晚上了,天仍然不黑,陈年坐在去酒店的车里,大开着窗——两旁是南方的树,大叶片在暖风里招展,像大佛的柔掌。慷慨的天光像海水一般,是荧荧的透明的蓝绿色,披在一样样东西上,仿佛东西自己闪着光。风携着露水摸进了陈年的眼睛里,陈年的眼眶就软了,又摸进他的鼻子,他的心腔就润了,最后摸进了骨头里,他的人就轻了。北京远远地在身后了。那干燥的,牢固的,混凝着灰土的响亮的,都一并在身后了。他开始觉得衣服穿多了,胸口沁出一层薄汗。
陈年下了车,三两步就进了酒店大堂,惊讶于两腿的轻盈。一个穿短裙的姑娘小跑迎上来:“陈老师?”
“哎。”陈年干脆地应着,知道是杂志社的接待。
“这您的房卡,日程,还有三天的餐券,”姑娘在肩上的大包里翻出写着陈年名字的信封,左胳膊伸出去高高一指,“电梯在这头,您是十四层,早餐七点到十点。”
“好嘞。”陈年接过信封没有打开看,知道里头有钱。
房间很敞阔,陈年进了屋走到尽头,拉开窗帘和玻璃门——露台也很敞阔。天终于黑了,风却还一样温润。他听到一句句懒懒的浪声,循声看出去,酒店里圈着一片海。
“陈老师?”
陈年回到屋内,才听见门铃和人声,开门看,是大堂里的短裙姑娘。
“进来坐。”陈年招呼着,猜测是社里有事情嘱咐——明天有一场他和几个作家的对谈。
“没事儿,我来给您送个火机,”她亮出手心里攥着的打火机,放在茶几上,“他们房间里没火柴。”
“哟。”陈年自中午上飞机,的确有大半天没抽上烟,“谢谢谢谢,”他为了表达感谢,立刻点起一支来,“你知道我抽烟?”
“啊,”她眼睛圆圆的,和那夜晚的天光一样清凉,“之前您来社里,就进我们主编办公室抽烟。别人主编可都不让。”
“嗨。”陈年听来觉得惭愧,嘴里猛吸两口,掐灭了,又把打火机拿在手里,“谢谢你,真没人对我这么好过。”
这话似乎重了,令她有点窘,轻轻扯着包向他解释:“我备了好些呢,不是单给你一个人的。”
陈年笑了,这时才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麦。”
“王麦,”陈年想起了故乡的女同学,这巧合有点令他兴奋,“我从前也认识一个王麦。”
“真的?”她开玩笑的心情太急切,嘴巴脱了缰:“不会是我妈吧。”
话出了口王麦自己又听见,才知道没道理。陈年这时倒不笑了,眼光对着她的眼光,像在琢磨什么。王麦跟着也琢磨,心里细究下去,曲曲折折拐到了小路上,脸就红了。
她脸一红,陈年的脸便也可以红了。
“这会儿还有饭吗?”陈年先回过神,岔开去问。
“酒店里没有了,”王麦为难地这样说着。陈年明白她没权给房间挂账,“不过,有几位老师约了十点钟出去吃夜宵,这会儿,”她看看手机,“九点四十六了。”
陈年问都有谁,王麦说了几个名字,陈年一听都还成,就决定也一起去:“咱们就在这儿等一等。”
王麦点着头,忽然不能像刚才自在:“那……我能也抽烟吗?”
“能啊!”陈年把手里热乎乎的打火机递过去,短促地想了想,“我媳妇也抽烟。”
“嗯。”王麦又看看手机,“九点四十八了。”
四男三女,挤进了一辆车。司机一听说“夜宵”,便嚷着“我懂我懂”,逃命一样地奔起来,半小时才赶到一家稀稀落落的排档,脚底下是土路,房后似乎就是村了。老板迎上来,一张口是北方人。几个女的有点怕,男的一挥手:“既来之,则吃之。”
总归是那几样海鲜,清蒸辣炒,煮汤煲粥,搭着冰啤酒。王麦明白她是结账的,可是老板偏不给菜单。
“你们吃什么,就说,我后头一做,就完了。”北方男人敞着眼睛笑着,满不在乎地挥着大手,“完了一块儿算!”倒像是王麦在跟他客气。
“可是……我们要先看菜单呀。”王麦不甘心。
陈年在桌底下伸出手,压在她胳膊上,小声地:“你别管,我来结。”
“不用不用,”王麦几乎从凳子上弹起来,声音也是同样的小,“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陈年的眼神和声音都严厉起来,“听我的。”
王麦低下头,嘴里咕哝着。
“坐好。”陈年命令她。
王麦坐直了一点,眉毛还皱着。
“裙子拉一拉。”
王麦就忍不住笑了。
一桌子七个人,除了王麦都是“老师”,都是弄字的人,都不那么爱啤酒。起先的兴致是为了相互知名但不熟,等聊开来熟一些,兴致就淡了。酒不诱人,海鲜味道也欠鲜,烟就很快抽光。王麦主动去买,问哪里有店,老板朝黑处一指:“那下头,有个小铺,关门了你就敲。”
王麦一路提着心,图快买了整条中南海,不敢讲价钱,买了就走。走回到一堵半米多高的砖垛底下,看见旁边站了人——几个本地的青年,瘦瘦小小的,见王麦过来,嘴里叽里呱啦地热闹起来。
她便不敢走了——穿着短裙,怎么敢在这些眼睛里抬腿上去呢。青年们见她不动,觉得有趣了,更加说说笑笑,渐渐要走近。王麦望着垛上远处的光,心一横,大声喊:“陈年!”
后来的日子里,陈年老提起这件事来笑她,学她的样子,苦着脸:“哎哟,吓得呀,‘陈年!’‘陈年!’”
王麦反驳:“我没喊那么多声儿!我就喊了一声儿!”
她一喊陈年就听见了——她刚走他就站到了路口去,等着迎她。一听她喊,陈年立刻急了,几步跑过去,边跑边也喊:“怎么了怎么了!”
青年见有人来,就散了。危险没发生,王麦不好意思起来:“没事儿。裙子有点短……不好抬腿。”
陈年还警惕着,等那几个人都走远,两下脱了衬衫,围到王麦腰上去。王麦顺从地抬着胳膊,像是交给裁缝量。陈年先把两只袖子在腰里绑了个死结,再前后看看,又蹲下把衬衫扣子一颗颗扣好——就真成了条裙子。
他仍然蹲着,脑袋就伏在她的小腹前。王麦把手背在身后,不然就要伸出手去摸他的头顶、耳朵……好像风一下子停了,四下里忽然静了,南方的夜里王麦的脸烧起来了。陈年吸着气闭上眼,喉咙里像是吞了一团热沙,压住心口。他感到一浪一浪的快乐,想唱歌。
“好了!”陈年站起来,拍拍她的肩,“大方了。”
“嗯。”王麦从鼻子里挤出瓮瓮的一声。
他们同时侧过身去,躲开对方的眼睛,因为脸上的笑再也藏不住了。
三
“你怎么了?”老七问陈年,“是不是谈恋爱了?”
“怎么了我?”陈年一惊。
“老发呆。”老七眯着眼睛,磕一磕烟灰,“手机老在手里捏着。”
“最近事儿多。”陈年应付着。
“到时候啦。”老七拖着长音,没头没脑地说。
陈年猜不准老七认为到了的是什么时候。大学时候他们住同一间宿舍,老七就是八个人里排第七。陈年最小,办事讲话却最显老成,便没人喊他老八。陈年和老七从小就认识——两人的父亲也是朋友,同一批从干校回北京。于是两个儿子一同上学,一同逃学,一同骑车划船,喝酒抽烟——分数不算太要紧,陈年读书多,父亲的朋友也多,给他考个文科足够了。
两人的不同是从大学毕业开始的。分配的单位陈年都觉得不配,想进高校讲课,请父亲去打招呼,父亲不打。陈年也不急,你不打有人打,就去找和父亲一批的叔叔。叔叔一听乐了:“你爸不管你?我管。”
陈年自己连系都选好了,书记是哪个,一说,叔叔心里有底:“一个电话的事儿。”
“您现在就打吧。”陈年把电话推过去。
老七却决定做生意。先倒了几批书,试过水,就多筹了钱,倒衣服鞋帽,一趟趟地跑到广州去。陈年的第一本随笔集出版的时候,老七挣到第一笔一万块,张罗着请客,让都来,认识不认识都来,问大伙老莫还是玉华台,陈年说玉华台。
陈年一向吃饱了才喝酒,所以总剩他一个不醉。老七第一个大了,两根黑瘦的胳膊在陈年脖子上吊着:“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没意见。”陈年摇头。
“你这个态度就是有意见。”
老七缠着不放,陈年索性认真:“老七你理想是什么?就是钱吗?”
“钱怎么了?”老七反问他。
“总归是……”陈年措不好说辞,“还有更高贵的事儿吧。”
“‘高贵’,”老七啧啧回味,“工人阶级最高贵!现在都在哪儿呢?”
陈年没说话,挑衅地盯着他。
“陈老师,”老七提起肩膀,又顺着椅背出溜下去,“钱,不高贵,但是!钱干净。”
现在老七就有许多许多钱,一手做餐饮,一手做艺术品收藏,顺带养着几家小书店,还即将进山修座庙,邀请陈年也参加。陈年看着老七平摊在腿上的肚子心想他和这时代配合得真好,他和他自己配合得真好。他数数看自己,三十二岁时提了副教授,三十三岁就辞了公职做闲人——当时很算是新闻的,如今闲人多起来,自由似乎不稀奇了。
还没轮到他的时候,时代是三五年一变的——有时两个半年劈开,也是天上地下。可是一轮到陈年,时代仿佛懒得管了,不给他父辈那般的起伏考验。陈年离开体制,以为是开始,没想到真就闲淡了下去。他早早摆好的反叛姿态,如今成了顺应——当他发现这一点却已经迟了,他的心脏和骨头开始老了,只好仍然那样僵硬地摆着。他觉得他是被欺骗了。他们的父亲都去世了。
没过几天,老七给陈年置了间工作室,方便他见人谈事,又因为置在郊区,远,所以“万一晚上回不去,睡这儿也正常”。老七说。
陈年就大体明白他说的“到时候”了。
四
原来恋爱是这样。陈年日日夜夜持续地激动着,惊讶于他的恋爱竟是这样迟来,又这样崭新。
“我是第一次谈恋爱。”他拉着王麦的手告诉她,心里充满对自己的怜惜。而她从经验出发,只当是一种喜新忘旧的表白。
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陈年主持着给王麦搬了家。他看中那房子里沉重结实的木头家具;白墙已经不白,映着曾被长年遮挡的灰黑形状;地板是实心实意的木头,踩上去咯吱作响,闪着哑暗的红光,像干透的血迹。
王麦觉得这些家具太大了,整个房子都太大了,仿佛不留神就会压在她身上。她想换几样新东西,让眼前轻便一点点。陈年不许。
“就这样,”他笃定地说,“像个家的样子。”
他的生活开始紧张起来,每天一睁眼就跑到那房子里,踮着脚溜到床上去,看王麦睡觉,看她觉察响动睁开眼且一睁眼就能够露出笑来。他如果轻轻说:“还早,继续睡。”她便真能继续睡,有时要睡上一两个小时。陈年的一条胳膊给她做枕头,另一条不疾不徐做一些温柔的探索。他的工作就等在这房子外面——许多人要见,许多会要开,可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在这些早晨里他什么都不做,只看着她。他真羡慕她能够这样地享受睡眠,不觉惊扰。大概没人害过她,陈年想。
等王麦真正醒过来,他们才正式开始这一天。有时吃早饭,有时没时间。床也那么大,像一张四方形的海。陈年沉迷于亲吻,相较于激烈的明确他甚至更爱亲吻,令他忘情。而王麦更愿意要明确——第一次就发现了,他们完成得那样好,谁都不必委屈,竟会那么好。
“简直可以参加比赛。”王麦神情认真地说。
老天爷啊,陈年在心里喊。
他把她整个地监护起来,在他选定的房子里给她做饭,给她洗澡,给她穿衣服。短裤和短裙不能再穿了,低胸和丝袜“比短裤还恶劣”。他带她买许多布料充足的长裤、T恤和衬衫,盯着她穿:“多好,明星都这么穿。”
王麦对着镜子皱眉头:“像下岗女工。”
“胡说,”陈年批评她,“下岗女工哪舍得穿这么好的衣服。”
“走吧。”王麦一甩胳膊,准备出门上班。
“等会儿。”陈年把她扭回来,抬手扣那衬衫领子上最高一颗扣子。
王麦使劲儿挣:“这个扣是不扣的!”
“谁告诉你不扣的?”陈年立着眼睛,“不扣为什么要做个扣子?”
“为了美观,真的!”
“美什么观,你这叫益街坊你知道吗。”
“什么?”王麦扑哧笑出来。
“益街坊。就是傻,便宜别人。过来,扣上!”
和每天一样,陈年把王麦送到杂志社旁边的路口,剩下的一小段要她自己走。下车时四下如果没人,可以迅速吻一下,如果有人,就在底下捏捏手。这一次王麦下了车,走出几步远,发现陈年也下车追过来。
“怎么了?”她紧张起来。
“这个扣子,”陈年严肃地指一指她,“不许我一走就解开。”
王麦忍着笑:“那你亲我一下,我就不解。”
陈年迅速亲了,眨着眼问她:“服不服?”
王麦服了。
五
头一年总是慢的,实打实的,一天是一天。第二年就快起来。他们还是一样的相聚,一样的分别,可是相聚前的等不及更甚,分别时的不舍得也越诉越沉重。他们的默契更丰满了,游戏更曲折,情意更加清楚,速度就更紧迫。
“那你是不是爱我?”王麦总是问他,次次都像从来没问过。
“是。”陈年踏踏实实地点头。
“是吗,”王麦想一想,“那我更爱你。”
这是甜蜜的斗争,可是令陈年恐惧。爱与更爱,孝与更孝,忠诚与更大的忠诚——她懂什么?陈年高高地看着王麦。她可不知道这样的斗争里有生死。
他第一次感到戒备,是王麦终于问他:“她什么样子?”
陈年尽力表现得不把这话题当一桩事:“就是那样,你知道的。”
这样的敷衍,反而使她能够接着问:“我怎么知道?”
“就是老夫老妻那样的,没什么。”他太太并不是老妻,比王麦大一些,小他十几岁。
“老夫老妻什么样?”
“总之不像我和你这样……就像你爸妈那样。”
“我爸妈感情好的,天天吵架。”王麦的眼睛已经睁得很大。
“我们不吵架。我们有事才说话,没事不说话。”他神色很坦荡。
“什么样的事算有事?”
“……比如,有我的快递寄到家,她就告诉我一声。”
“那,”王麦问题储备不足,顿一顿,“都有什么快递?”
陈年松了气,笑出来,把王麦脑袋扳进怀里:“你担心什么,我只有你。”
王麦不出声。
“我只有你,”陈年捧着她的脸:“我说这话,你明白吗?”
“什么?”王麦大声喊,“你捂上我耳朵了,听不见!”
陈年叹气:“不说了!”
在房子里的时候,他们做什么都在床上。陈年添来一张黄花梨小方桌,吃饭时搭上床,倚躺着吃。吃饱了,就感到适意的昏沉。陈年拿一把宽木梳,缓缓地梳王麦的头发,像摸小猫的毛,不经意地:“要是还让娶两个……”
王麦闭着眼睛,身上一僵。她那么信陈年,以为他是最文明的一批——他凭什么以为她愿意?她没说话,为了留恋当下的适意。如果她能把面对陈年时一句句咽下的话全部说出来,噢天知道,她也知道,这一切会比一支舞曲还短暂。
这支舞跳了两年,舞步终于乱起来。陈年的管束越来越紧,而王麦的期待越来越大。有一回吵起架来,王麦把那温存时的话扔回他头上——“娶两个!”带着愤怒和眼泪。陈年不吭声,心里坚决不认——人们总是曲解他的意思,只为了给他定罪——他所描绘的不是倒退,是进步,是融洽的集体的自由。她如果不同意,可以退出集体去,可她竟掉过头来来批判他,这怎么行?
于是他要先批判。一次王麦读新书,被他抓住,作者正是他不齿之流——青年新秀,面孔俊朗,文辞狂大,还梳个辫子——他称之为“假狠”。
“看这种烂书,”陈年夺去翻两页,愤愤地一摔,“烂书最害人,比烂人还害人。”
“你又不讲理,”王麦眨眨眼睛,“烂书不就是烂人写的,怎么会比烂人更害人。”
陈年一怔,生硬地往回掰:“不是这回事——有彻头彻尾的烂书,但是没有彻头彻尾的烂人……人,人都是有原因的。”
王麦便不说了。她知道陈年往下无论说什么,总是在说他自己了。而如果你要他真正地说说他自己,他便又“不可说”起来。
“过几天,我爸妈要来。”
陈年已经站在门口要走了,穿着一只鞋,回头看王麦:“来看看你?那过几天我先不来。”
王麦坐在沙发上望他:“也看看你。”
“你跟他们说了我了?”他走不出去了,鞋又换回来。
“说了,他们老问。”王麦的脸一半委屈,一半理直气壮。
“他们知道我是谁吗?”陈年沉默了半天问。
他知道事情不一样了。王麦的父母和他是一辈,他们懂得另一种对话。他没有单位,可是整个社会都是他的单位。
“‘你是谁’?”王麦惊讶又好笑,“你是谁啊?”
他是谁?陈年在心里一片片地剖开。他是那些担不起丑闻的人,他是要写回忆录的人,他是指望名字活着的人——而他看得对,没人害过王麦,她所以是指望爱的。
陈年换了好声气,求王麦不要爸妈来,她不肯。她乖巧的时候是女儿,站起来与他争论就成了女人了,和他太太没什么不同——都要他负责任。他要两个责任做什么?
“不行,”王麦气喘吁吁地冒眼泪,像个丰沛的泉眼,“要么你跟我爸妈说,要么你回家告诉她……你不告诉我去告诉。”
陈年浑身发抖:“告诉她,告诉以后我怎么办?你根本不知道后果。”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我完蛋,彻底完蛋。后果就是痛苦,后半生的痛苦。”他颓然。
王麦惊奇地:“现在就不痛苦吗?我不痛苦吗?”
“就因为你痛苦,就得让我也痛苦,”陈年眼睛血红,“你怎么这么自私!受过教育吗!没学过孔融让梨吗!”
“让也是孔融自己让!可没人逼着他让!”
王麦一声比一声高,她的眼睛不再疼惜他,话也不留情。这个小小的人啊,曾经像他口袋里的一朵花,如今像一支孔武有力的队伍。陈年认得这个队伍,他一出生就被这队伍摘出去,过些年又招回来。陈年那时就懂得:这队伍永不会消失,谁的屁股也别想坐稳。这个夜晚,他在王麦身上认出了他们,也认出他迟来的考验——王麦就是他的考验。
“找个牙刷给我。”他轻声说。
“不走了?”王麦愣住一下,仍然冷冷的。“别哭了,”陈年说,“我心疼。”
六
飞机落了北京,老七问陈年回哪儿,司机一道送。陈年说工作室吧,欠了几幅字要写。老七想了想说那我车送你,我另找个车回家——兜到郊区再回城太远了。陈年也不谦让,点头同意。这一趟把他累着了。
他答应了老七一同修庙,老七负责弄钱,而他是设计师。一年间他们跑下了国内国外十几座大大小小的庙,都不只是过路过眼,都要同住共修,时时还要苦劳动。据他所知,王麦离开北京也有一年了,而他仍不大敢回来,每次回来也不大有心回家去住——老七早有一双儿女,所以回京必要回家,而他没有这样的必要。他从不想养孩子。他没有,可他的姐姐有,就足够了,一个家有一个孩子就够了——他和他的父母、姐妹、伴侣,整个地加在一起,才算一个家。他和太太两人是少数,称不上一个家。他们是合用一间宿舍的情谊,如同室友的关系,而当他不在家时太太的心情——他猜测,大概就像室友外出过夜的心情吧。
“北京不好待。回家吧。”
这是陈年给王麦最后的话。他在那房子里住过那一夜,第二天便请王麦杂志社的主编到工作室去喝茶。他们是同一代,有共同的光荣要捍卫。
“你那有个小员工,好像是叫王麦?我听说,”喝到了第四款茶,陈年才不经意讲起,摇着头,“办事不行,不靠谱。”
主编起先不懂:“小孩儿吧?都是老编辑带着,我没太见过。”
陈年咬咬牙:“心术不正。这样的年轻人,能不用就不用吧。”
主编端起茶杯占住嘴,不说答不答应,也不问原委,另起了头聊别的。
临走了,陈年送人到门口,才忽然想起似的问:“老周,你们杂志也做新媒体吧,集团支持吗?”
主编叹气:“精神支持,财务不支持。”
陈年慢慢悠悠地又想起:“我有个朋友,正想投点钱做媒体,你这儿要是行的话,我约上他,改天再喝茶。”
主编自然是行,不迭道谢,陈年摆摆手:“你等我消息。”
主编便明白了,陈年说的是“我等你消息”。
王麦立刻没了工作,另一边陈年退掉了房子,三天之内搬出去。
“回家吧,”他知道王麦没有存款,远远地坐在她对面,“北京不好待。”
王麦哭了两天,第三天走掉了。爱不是爱了,她便没了指望,也不剩一丝斗志。陈年并不担心她垮掉——二十几岁的人,哪里不能站起来?如今他再想起她,更有由衷的羡慕——要是没有遇上他,她也许一辈子都是完完整整的自己,哪会有机会去反叛和重建?他就没有过。
陈年放下行李,洗了手,汲了墨,决定抓紧时间,完成两幅字两张扇面就睡觉。抽纸出来时,架上掉下一本旧书,扉页露出两道字——
左边是他的:“陈年购于一九九〇”。
右边是一阵呼啸的风:“王麦生于一九九〇”。
陈年不知道王麦什么时候写上去的。这行字令他恍然又看见当时的颜色,听见她清亮的喊声——可他的确早已经忘了。
他又记起了那张床,记起自己把最好和最后的都给了她,记起有一次当他们贴伏在一起,山峦与沟壑都贴伏在一起,她发出那个使他堕落的声音——
“爸爸。”像梦里的呢喃。
他记起当时的耳朵里那一声轰响,记起肌肉颤栗,骨骼融化。他仍然闭着眼睛起伏着,可眼前出现了所有光。他在那光里看见一切秘密敞开,看见了快乐的真正形状,看见他同时抓住了最为宽广的自由,和最深最深的埋葬。
烟烧到头了,落在扇面上。陈年吹掉那雪白的灰段,久久地盯着,下不成笔。他想他的人生就是这扇面的形状,越去越敞,越去越敞,险些收握不住——然而他是韧的,他活下来了。他为之自豪,又遗憾给他的考验太少。
他就像旷野中的芦苇,在任何一场风暴里都不会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