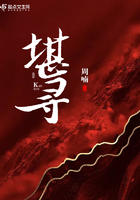
第11章 忆忧烟波之“有灯光也照不亮的黑”
“我觉得昨晚你们明明可以在护城河边布网,即便不抓他也可以查清楚盗尸的人是不是常集,可你为什么偏不?”叶轻飘头顶一片菜叶遮阳,啃着一截萝卜,盯着挖萝卜的三人。
“我们的目的不是找到七姊妹就可以么?”寸言挖了半天又努力拔,那萝卜都快被拔细了,但土里的部分依然纹丝不动。
“那为什么我们不乘着他们都不在,夜闯常家去查个清楚?”
“你上次不是已经试过了吗,那里有常集最大的秘密。”寸言又用锄头刨了半天,那萝卜露在外面的已经是很长的一段了,没想到这个泥土那么紧实,拔个萝卜居然拔到满头大汗,可越拔不起来就越不甘心,现下的寸言脱了靴袜,把衣衫卷起别在腰间,高高卷起库管跟那个萝卜杠上了。更云和卷堆也对这只倔强的萝卜来了兴趣,都停了手里的活过来看热闹。
“可是常集家的秘密咱们最终是绕不过的,因为目前我们只有这一个线索可以用……!”
“咔嚓!”赌气似的脆响,那萝卜断成两半,更云和卷堆看着贴近地面那个白生生水汪汪的断裂口,扫兴的摇头叹气。
一阵轻而节奏缓慢的敲门声。
“开门去。”更云盘腿坐下,使唤卷堆。
“你怎么不去。”
“你站着的呀,方便。”
卷堆撇嘴,嘟嘟囔囔一路踢踏到大门边,然后便没了动静。
“卷堆。”更云试着大喊,没有应答。
“不会被妖怪给吃了吧,哈哈哈……”更云啃着从地里刚刨出来还带着些泥土的水萝卜,贼笑着。
“估计不会,妖怪会被他吓死的。”叶轻飘站起来够着脖子朝大门方向望去。
“你俩去看看。”寸言还在跟埋在土里的那半截萝卜死磕。
于是,第二拨去的两人又没了音讯。
寸言心下也觉奇怪,十分不甘心地放弃了那截快被刨到底的萝卜,拍拍手上的泥,光脚警觉地走向大门。一路还苦于没有东西可以打打掩护时,却看到背对着的三人互相搭着肩形成一道人墙堵在大门口。
寸言蹑手蹑脚,做好随时接招的准备。他从卷堆和叶轻飘之间拨开一道缝,用凌厉的目光一眼锁出去,却是一惊,眼底略微失望,不过很快恢复正常。危险可以暂时先放一放,寸言慢慢松开已于无意识中握紧的拳头。
门外阶下俏然玉立的是一位妆容精致、衣着简约的女子,面如带珠梨花、瘦削苍白,眉梢向外,眼尾上翘,倦意极浓的眼眶里花色潋滟,然而眼底还是有掩不住的恹恹之气,唇间玫色轻点。一袭白裙迎风柔软的贴在婀娜有致的身段上,裙袖随风飘摇,如同天降使者,扶风于晨光薄雾里。
终于来了一个还能转动眼珠理智思考的,那女子目光有意无意带过寸言的高低裤腿以及同样高高卷起的袖子,微微抱拳颔首:“我是常集家中的织织。”
女子稍稍停顿,继续道:“请问四位可是曾经到过我家中?”
“不错。”寸言正色道。
“织织姑娘,我们到屋里聊呗!”不知几时从陶醉中清醒的叶轻飘使劲绷开两只胳膊撑走两边的卷堆和更云让出一条道。
“不了”织织在目光转向叶轻飘时变得亲切很多:“我是来送请柬的,邀请各位到家中做客!”织织说完双手奉上一张请柬。
“我和常集诚挚地邀请各位,今日日落之后,任何时辰你们都可以来,想必你们都会来的,对吗?”织织略微歪头,目光款款。也不知她这话是挑衅多些还是邀请多些。
“定当造访。”寸言拱手。
织织在原有的浅笑上笑意更深了些,似乎很满意于眼下的情形,朝着三位男子微微作揖后转向叶轻飘挑了一下眉头,身姿后旋,一道白影一晃已不见踪影。
叶轻飘还沉浸在织织对她的友善上,寸言目光变得更为深邃,而另外两个自始至终都不曾言语过的人如大梦初醒般吐出了衔在喉咙间的一口赞叹。
“注意到她腰间那块环玉中间的绣品没?”卷堆横着挪到寸言身旁。
“那是她身上唯一的饰品。”寸言收回远行的目光:“原来你没有丢魂。”
卷堆扭头平常地盯着寸言的脸看了一小会,没有任何特别的表示继而转回织织离开的方向:“我记得飘飘说过他们家的家丁叫她襄母,叫常集襄子,她腰间的那块绣品是榆树叶形的布料上有一个豺狗头像。我想起来书中记载这是乞桑城王室必须佩戴的饰品,而且也只有王室才以襄子襄母称。”
寸言一顿,神色间有被卷堆点醒之态,稍作总结,他眼色一亮说道:“《族经》中记载,桑榆城和乞桑城的祖先原是同气连枝的兄弟,后各在毗邻的地方建自己的安身隅所,由于一边种桑树一边种榆树,故种桑树的一边称桑城,榆树的一边称榆城,合称桑榆城。可往后延续数十代,又与他族通婚后,血脉之情日渐淡薄,为扩充人员和土地,桑城先祖合城攻打了榆城,并险些使其灭族。榆城的先祖为保族中血脉不断,带着剩下的几个妇孺投降跪拜乞求放他们一条生路,并承诺世世代代不再跨入桑榆地界,他日不管族中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见到桑城的人都会百里之外俯首绕道而行。可是桑城的先祖恐后世有根患之忧,令斩尽杀绝,当时血染残阳、泥化赤色,天地间一片鬼哭狼嚎的凄阴戾气。桑城城主为警示后代子孙弱肉强食的道理,将尸体曝露荒野,任凭尸体自然风干和腐烂,任凭飞禽前来啄食、走兽前来撕扯储粮。直至这些尸体全部变成残肢散架,臭气随风雨沉寂,桑城的先祖才挖掉这个城里所有的榆树,种上桑树,烧毁所有村庄,翻下覆表,建立新的桑榆城,也就是现在这个桑榆方城。”
更云和叶轻飘听得入神,如同一段历史自己就身在其中。
“不错,我也在《垦泥》中看到过这样的记载。”卷堆接上话题:“桑城的祖先认为已斩草除根,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不料有一具女尸在被野狗撕扯的时候,却从腹中撕出一个活着的婴孩,由于那个孩子在出生见到周遭尸殍遍野的世界时并没有啼哭,所以没有人发现。那只野狗把这个小婴儿一直藏在自己的肚皮底下,直到晚上一个外嫁还未到夫家就闻讯赶回的姑娘找到这个孩子,并偷偷把他抱走养大,于是有了后来慢慢建立起来的乞桑城。为纪念当时先祖为保全族血脉跪求桑城城主的情形,新城叫做乞桑,而为圆先祖的遗愿,乞桑城处处种满榆树无一棵桑树。因为当时回来救孩子的姑娘为培养孩子一生未嫁,所以女子在乞桑城有着很高的地位,而豺狗也因此成为他们的图腾,且只有王室才能佩戴相关饰物。不过在任何书籍里都找不到有关乞桑城所在位置的记录,据说乞桑城现在和桑榆城一样的富庶。”卷堆在整个叙述的过程中神色由灰转亮,像铺上春晖。
“我读过很多书,却没听说过你说的《垦泥》,但记载的是一样的。”寸言看向卷堆。
“那也就是说织织和常集都是来自于乞桑城,那么常集又懂墓地的机关,说明他是桑榆城曾经很有地位的人,光凭这一点就很矛盾啊,还别说盗尸那些奇怪的举动了。”叶轻飘一副头疼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今晚去了就知道。”寸言一脸漠然看向远方。
“你是说他们叫我们去是想摊牌?”卷堆问得很是淡定。
“或者说是想和我们分清关系。”
叶轻飘和更云也捻着下巴有同样的感悟。
一个似乎连星星都躲回去了的夜晚。
“织织说只要天黑以后都可以来,为什么我们还要等到这么黑的时候?”
一行四人行至常家门前止步,大门口两盏新换的红灯笼比往天更大更亮。
卷堆正色意味深长地看了叶轻飘一眼,道:“因为现在邻居们都睡了。”收回目光时,抡眼看到寸言赞许的目光。
“我们是光明正大被邀请的,干嘛要等邻居们睡着偷偷摸摸地来。”叶轻飘似乎对这种造访方式不大乐意。
“飘飘,我们来是要听人家秘密的,更严重些可以说是来揭人家底的,你以为人家随随便便就会跟你说啦!”更云说完连贯地一眼横扫卷堆和寸言一模一样的表情,对自己偶尔地动脑居然完全言中而有些激动。
叶轻飘拧眉深深思考,忽觉真的是这么个理儿,有些怪自己没脑子,遂把腰间的绦带结实地再次打了个结,跟着三人走上台阶。
照礼,卷堆上前敲门。意料之中,并没有人前来开门。但是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眼望去里面一如既往地拾级而下可到达第一个院子,院子后呈上走的趋势可以到达后院的房子。
一眼就能感觉出这个院子比别的晚上新添了不少灯笼,一丝风都没有,温暖的灯火下还有些惬意。
叶轻飘和更云知道此行必定要大干一场,于是都卷起袖子,四处防备,可寸言和卷堆两人却大摇大摆慢慢踱着,如同饭后散步。
见叶轻飘一根神经绷到快断,更云的一双眼睛到处滴溜溜地打转,卷堆不得不开口劝道:“莫着急,他们不是在这里迎接咱们。”
叶轻飘注意到更云一直在盯着前方,所以才敢倒着走看向后面的寸言,寸言给了她一个赞同卷堆的眼神。
“那是在哪里?”
叶轻飘继续望着寸言,卷堆刚欲回答,寸言就抢了先机:“依你自己的判断呢?”
叶轻飘再次垂下眉眼,闷头一悟:“是后院那个黑洞!”
“依据。”寸言背过手去,一副老师傅的模样。
“我上次在那里被袭,不是我到了那里才被发现,因为那里是不愿被他人踏入的地方。”叶轻飘很是笃定,可看向寸言时,他依然表情淡漠,一时间有些怀疑自己。
“我说的不对吗?”叶轻飘再三思索,不得不一副询问的样子看向寸言。
“这也需要你自己判断。”
寸言说完就看向别处,叶轻飘认真考量过他这句话,转正身体昂首朝前走去。
穿过两个院子,没有遇见一个人,直至到最里面那排屋子前面。
“就是这道门,穿过去,后面就是一个黑洞。”叶轻飘想起上次遇见的黑衣人,胃里有些翻滚。
寸言走到最前面,伸手推开门,一股浓烈的香味扑鼻而来,其间夹杂着另一股味道,像是腐尸又像是焦尸,总之是一种发自肺腑抗拒的味道,另外还有若隐若现的潮湿气。
屋子里一片漆黑,可是却可以看到屋子另外一边外面灯笼里闪烁的烛光,和叶轻飘描述的毫无二致。
自从到达这排屋子的门前,四人就开始小心谨慎了起来。在这间屋子里唯一的声响就是此起彼伏毫不同步也豪无间断的呼吸声,叶轻飘多怕有什么异动被这些嘈杂的声音混盖住。
寸言一回头,三人都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可是更云和卷堆却跟随他的目光到了叶轻飘身上,叶轻飘也跟随他的目光到了自己身上。正一阵吃惊,寸言却已回头伸手推开了那扇叶轻飘上次也推开过的门……一阵寒气逼来,那股参杂了几种气味的味道被深深地灌进肺里,真是防不胜防!
这次没有人来袭击和阻挠。
几人调整呼吸,探出半截身子朝那黑幕里看去,除了黑和不断冲击着鼻子的臭味及晕人的浓香,啥都没有,或者说啥都看不见。
更云伸手取下离自己最近的一盏灯照到面前,不过他还是只看到前方的一团黑,有灯光也照不亮的黑,这到底是什么啊?更云正纳闷,却听得身边叶轻飘一声“哇”及和他并排的身体倒退一步的感觉。
更云看向她才发现,他看前面,可大伙儿都看的是脚下,而且几人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也不由得低头望去。
“哇!”
更云也不禁往后退了一步,原来黑洞不在前面,黑洞在脚下!眼下自己的脚尖和洞口边沿对得一丝不差,真难想象刚刚要是多走半步,现在自己是在洞底还是在往洞底掉的途中。
看清状况,叶轻飘和更云都走回洞口边,四人各提一盏灯往下探照:这是个垂直向下的洞,像是水井那样,在灯光有限的射程里,看不到洞壁更看不见洞底,洞口四周也没有绳索之类的东西,更谈不上楼梯。
自从上次在常集家门前跟踪,更云就习惯了带着石块以便探路,现在他不知从哪摸出一把,一块块分别扔向洞的四壁,没有声音。向下扔,也没有任何声响。趴在洞口边往里大吼一声,也没有回音。寸言转身回到屋子里开始寻找机关、销楔之类的东西,叶轻飘则怀疑是不是走错了路,更云则举着灯盏朝四周查看。
“是这样。”一直在原地就快站化的卷堆突然说。
“心中有道,脚下自然有路。闭上眼睛,心中默念三声后开始自然走路。”卷堆神情严肃而又满眼放光。
“怎么走啊,这脚下没底嘛,怎么落脚?”叶轻飘有些小着急。
“就像平常那样迈腿就行,在心里默念的那三声里把自己集中在自我的意识里,不要去猜想你的处境,最重要的是不可以停下不可以睁开眼睛也不可以说话,直到我说可以了。”卷堆说着,站到最前面,示意三人站到他身后。
更云排第二,叶轻飘在站到寸言前面之前望向寸言。寸言也看向她:“听他的,在我们几个里,幻术他最懂。”
叶轻飘这才放下心来,闭眼,虔心默数三声,凝聚意识,然后抬脚试探着迈出去……本以为会“哐啷”一下身体就无抓无挠地向下坠,不想脚下真有路。
尝到了甜头,于是放大了胆子迈出第二步,当完全确定脚下安全的时候,叶轻飘侧耳聆听,却不见身边同伴的动静,她甚至极度放缓了自己的脚步还是听不见自己以外的任何声音。
不知自己是不是和他们在一起,不知是不是他们也出发了,不知他们是不是也走的同一个方向……叶轻飘的疑问很多。按捺不住地想去弄明白,但篱酿说过一时的忍不住是会坏大事的,只能赌一把,因为这些总是会得到印证的。
“这路平坦得像镜面!”这是更云用心去感觉后总结出来的,“真是难以想象黑暗里隐藏的是一条这么好走的路。”更云暗自佩服修这路的人,更好奇这路会通向哪里,第一次觉得不用看路行走,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原来瞎子的世界也没有那么困难嘛,全新的体验使得身心顿觉舒畅,如身处柔软的草垛晒着干净的太阳。
可是这种平坦和干净爽朗也没有维持多久,没有过渡,仿佛一切只是因为多迈一步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闷热潮湿,耳朵里充斥着“咕咚咚”煮沸的声音和铲子大力搅拌东西的声音,还有“噼里啪啦”柴火燃烧的声音,期间还夹杂有不知道是哪些种类工具发出的声响。
往里走着,一种酒糟的味道越来越浓。渐渐地,酒糟的味道成了全部的味道,闷得人头晕,似是醉酒。不爱动脑子的更云不得不启动那快生锈的大脑去判断:现在在哪里,这么热闹的地方该是快到目的地了吧?
在酒气的热浪里穿行,一会儿功夫便开始大汗淋漓,更云感觉到从头至脚汗水已经变成了河水,衣服湿答答地裹在身上,裤腿也束缚着双腿,迈都迈不开,而且脚下的路质感已经是凹凸不平的泥地皮,踩上去还有些粘黏,没走一段路就完全的精疲力竭。
“也不知道叶轻飘他们怎么样了”,更云这样想着慢慢地脚下开始磕绊起来,两只脚也开始互相使绊,现在不要说不能睁眼了,即便能睁也没力气睁。也不知是哪只脚绊了哪只脚,一个趔趄,更云一把向旁边扶去。
“哦哦哦哦……”更云从心底一路打颤到了手臂上,他能感觉到那一瞬自己全部的鸡皮疙瘩都亢奋起来,这样的热浪也温暖不了这一刻的寒。
在达到清醒的颠值那一刻更云回味了一下,自己刚刚抓到的似乎是一只壮且糙的手,而且正在劳作。这次更云主动张开两手臂,每走几步他就能摸到一个人,或是背或是手,或是他们手里的工具,总之心里缓和了许多,看来是快到了。
正当这么想着时,热浪忽然没了,也没了那种潮湿黏稠感,四处滴滴嗒嗒的落水声音,一种陈酿的味道起初刺激着更云的鼻腔,渐渐地觉得这种味道很是特别且越来越喜欢甚至沉醉。
这是羌泥没有的,但更云知道这叫酒,因为六四那里有过这种类似的味道,不过与这个比,差远了。六四很宝贝,只跟主上分享,她说那是她珍藏了很多年的,喝一点少一点,如果羌泥一直像这几年一样风调雨顺的话,再过几年他们就有多余的粮食来酿酒。
原来,刚刚路过的那叫酿酒啊!更云恍然大悟。
“尝一口?”
“好啊!”更云答应得甚是爽快,但收不住的后悔,因为卷堆说过不可以说话,何况这是哪里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