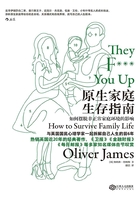
简介
女演员米亚·法罗(Mia Farrow)在家里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5。19岁时,她曾对此表示遗憾,她对一位报社记者说:“一个孩子需要更多的爱和感情,而在一个大家庭中,孩子所能得到的关爱则要少得多。”25岁时,她初次产子,生了一对双胞胎,不久之后,她又生了一个儿子。那时她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家庭,她可以给孩子们更多关爱——比她自己在童年时所得到的关爱更多。但在一年之内,她收养了2名越南婴儿。在接下来的12年里,她又生了1个孩子,并收养了6个孩子。最终,总共有12个孩子叫她妈妈。如今,她说:“大家庭的好处是极大的。我想重现我的童年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她忘掉了身处一群兄弟姐妹中的迷失感,但是科学证据表明,米亚在19岁时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一个很大的家庭中,满足孩子的需求有多困难。在子女数量不少于5个的大家庭中,孩子们长大以后更有可能违反法律和患上精神疾病。米亚收养的几个孩子当中,有2个孩子曾因在店铺盗窃被抓。米亚·法罗曾自豪地说,她亲自照顾孩子们,并不借助保姆的任何帮助。可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满足12个孩子的需求是很难的,更可能培养出缺乏个性、渴望爱和关注的孩子。
米亚还离过几次婚,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女孩,到了适婚年龄时,更愿意接近年长(与自己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性,以获得专一的爱和安全感……米亚的养女宋宜(Soon-Yi)是伍迪·艾伦的现任妻子,而米亚是伍迪·艾伦的前女友……20岁时的米亚显得特别稚气,她的第1任丈夫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与她结婚时已经50岁了;她的第2任丈夫音乐家安德烈·普列文(André Previn)年龄比她大16岁。米亚·法罗亲身体会过在大家庭里成长是什么感觉,那她到底是怎么了?至少在19岁时她曾说过,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是缺爱的,她为什么想重现那样的童年环境?也许,她从父母那里遗传了一个基因,这使她想要一个大家庭。但也有可能,她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发现自己在重复过去的,不仅是米亚·法罗——我们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我们重复童年经历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事实上,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如何应对自己的朋友、选择爱人,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能力和兴趣等几乎一切心理状态,仍在通过我们每时每刻的经历,不断地反映着我们的童年经历。
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遇到陌生人时,我们会基于自己的童年关系,对他们产生偏见。不知不觉中,我们把他们与我们原生家庭中的人物混淆起来。陌生人的名字、说话方式、模样等每一个细节都可能会唤起我们的记忆(来自我们最初的家庭剧本),然后我们就把这些记忆强加给了那个陌生人。
我们与密友的相处方式受到童年故事和角色的影响,不仅如此,研究表明,我们甚至会使这些朋友以我们童年时习惯的方式行事。童年时,我们在家庭中无论是被视为甜美可爱的孩子,或是害群之马,都会出去结交以同样方式看待我们的人。如果他们不那样行事,我们要么会操纵他们,使他们以那种方式对待我们,要么会假设他们是那样看待我们的,不管真相如何。难怪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恋人和密友。我们首先要求他们适应我们的童年剧本,然后为了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我们也必须适应他们无意识的童年剧本。伍迪·艾伦的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结尾处有一个笑话,而这一证据证明了那个笑话背后的真实性。一个男人去看心理医生,他说,他的妻子以为她自己是一只鸡。心理医生问那个男人为什么不离开自己的妻子,男人回答说:“因为我需要鸡蛋呀。”这几乎概括了我所知道的所有婚姻:每个人都需要对方的疯狂。
还有一个科学证据表明,米亚·法罗的行为是受她的成长环境影响,而不是她的基因所致。脑的电——化学模式使每个人大脑中的思想和感情变得独特,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童年经历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孩子的母亲患有抑郁症,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就会影响孩子,使其大脑右侧额叶形成可测量出的特殊的电——化学模式。心理学家们知道,这些模式不是遗传的,因为它们在孩子出生时是不存在的。只有当孩子的妈妈以抑郁的行为方式对待孩子时,这些模式才会在孩子的大脑中形成。虽然这些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形成得越早,就越难改变。它们会存续多年,除非在此期间孩子的成长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另外,现在已有研究表明,右脑的功能障碍与多种精神疾病有关联。
除了脑电波,大脑的化学物质也会受到童年经历的巨大影响。例如,皮质醇(cortisol)这种激素的分泌就是为了应对来自环境的威胁或其他行动要求。在正常人体内,皮质醇水平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停上升或下降,但如果我们在6岁之前生活在气氛紧张的家庭环境中,我们的大脑中就会像被放置了一个失灵的调控器(它负责设置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使皮质醇水平异常。如果一个成年人在童年时受到了持续的威胁,被父母虐待或忽视,那么这个人的应激系统要么会关闭(皮质醇水平过低),要么会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皮质醇水平过高)。也就是说,这个人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可能总是很低,因为他对会引起“战斗或逃跑”反应的外界刺激已经麻木,这些刺激已经不能使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上升了;或者,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可能一直都很高,随时准备对危险做出迅速反应。一个人若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那么在成年后,他体内就会有特定的皮质醇模式,这能反映他所受虐待的类型。一个人若在童年时遭受过性虐待,那么到了成年后,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很高;一个人若在童年时生活在冷漠和缺爱的环境中,那么到了成年后,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很低。
早期抚育对心理的作用是如此深远,甚至会影响我们大脑的不同部位的大小。海马(hippocampus)在我们的情绪功能中起关键作用,它位于大脑下部的一个区域中。对于海马体积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童年遭受过性虐待的女性,成年后会拥有一个比正常体积小5%的海马,遭受性虐待时的年龄越小,她的海马的体积缩小就越显著。性虐待以及其他童年经历都可能导致成人患上抑郁症,患抑郁症的成年人的海马体积也是会缩小的。因此,在我们的婴幼儿期,父母对我们的抚养状况,以及我们在成年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等因素都会影响大脑的体积和形状。
与此相一致,在童年遭受虐待时的年龄越小、遭受的虐待越严重,其影响就越深。一项研究对800名9岁儿童进行了调查,其中一组儿童在3岁之前遭受过严重虐待,另一组儿童在3~5岁遭受过严重虐待(在3岁前没有遭受过虐待),前一组儿童的精神状况比后一组儿童更异常。而后一组儿童的精神状况又比第3组儿童(仅在5~9岁遭受过虐待)更异常。儿童遭受虐待的具体类型,也预示了以后出现的情绪障碍的类型,例如,遭受忽视的儿童在以后出现的问题就不同于遭受身体虐待的儿童。此外,这些儿童如果曾遭受过几种不同类型的虐待,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比较高,从而长期处于“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模式中;如果只是偶尔遭受身体虐待,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比较低。若是对这些9岁儿童的大脑进行检测,就会发现,遭受虐待时的年龄越小,其脑的电——化学模式以及大脑结构的异常就越严重。0~6岁这个阶段很重要,会从身心两方面影响孩子成长。
无论是否有心理问题,我们大脑的模式和结构都会影响我们对朋友、恋人和职业的选择。我们选择的人或活动总是与我们的期望(由脑的电——化学模式产生)相匹配的。例如,我们如果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成年后就更有可能遭受更严重的伤害(虽然大多数强奸受害者在童年时并没有遭受过虐待,但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这种经历就会使我们更容易陷入可能遭受伤害的环境中)。当然,青少年期及以后的经历(例如找到合适的爱人,接受心理治疗,或服用抗抑郁药物)可能改变我们大脑的电——化学模式。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己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0~6岁这个阶段的经历影响的。
对以上证据的一个最常见的反驳是:“我和兄弟姐妹在性格等方面的差别都很大,你要做何解释?我们有相同的父母,在同一个家里长大,有同样的成长环境,但我们的大脑里为什么没有相似的模式呢?这种差别一定是由于基因的不同。”答案在于,就算是亲生的兄弟姐妹也不具有“一模一样”的父母。因为每个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都是非常不同的,这些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在不完全相同的家庭里成长的。无论你相信与否,兄弟姐妹长大后的差别与这种成长环境的不同有很大关系,基因的影响相对来说是很小的。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的一项研究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多图书、报刊文章和电视纪录片都对此进行了专门介绍,他的研究对象是被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他的研究结论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我们应该对这项研究的结果持谨慎态度,更应该抵制媒体对这项研究的过度吹捧。因为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
对这一点的认识,不仅可以让我们摆脱“基因决定论”的束缚,也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我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个人或社会的改变就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穷人会贫穷、疯子会发疯、坏人会使坏,都是基因造成的,那么针对穷人的教育支出、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谈话治疗、针对罪犯的开明监狱制度就都没有意义了。这些方法都是徒劳的,就和尝试用这些方法来改变一个人的眼睛颜色一样徒劳。但是,科学证据表明(见下文),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个性不是由基因决定的,兄弟姐妹在性格等方面的差别也不是由基因决定的。
认识到这一点,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我们自身,就有助于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应用于整个社会,就可以使社会进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监狱里90%的犯人患有精神疾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他们的成长环境造成的:等你读到本书的结论时你就清楚了,如果对儿童的照顾得到改善,那么日后,罪犯的数量就会大幅度减少。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200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一个政府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幼儿期的早期抚育方面进行投入。但不幸的是,对孩子和国家来说,幼儿期是最不受关注的阶段。”
这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是,许多人都不愿意去思考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真实原因,更不愿意去思考犯罪的童年起因。在许多发达国家,虽然人们生活在所谓的“抱怨文化”之中,特别容易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但大多数人仍然很维护他们的父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童年的一个相对真实的叙述,正如辩论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指出的:“不把自己的痛苦当回事,轻视它,甚至嘲笑它,这种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中是被鼓励的……许多人(曾经也包括我自己)都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对自己的童年缺乏敏感性,并为此感到自豪。”然而,了解一下父母是怎样抚育我们的,直面真相的后果并不会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具有破坏性。如果我们发现父母对我们的抚育方式既有破坏性也有建设性,那就不需要徒劳地对他们进行指责,也不需要选择伍迪·艾伦式的反省和毫无意义的刻薄。了解真相与自我怜悯是不一样的。
我并不是说,当你意识到你的问题(倾向于惹恼你的老板,或者总是爱上不该爱的性伴侣)的童年起因,就应该痛责你的父母,指出他们的可怕行为。大多数父母都会尽自己所能,为孩子做到最好。我们应该做的是,接受并重塑他们在我们童年时对我们采用的抚育方式,使之符合我们自己的人生目的,重写我们的人生剧本。
当然,这并不容易。T. S.艾略特(T. S. Eliot)曾精辟地写道:“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现实”。我们与现实之间隔着正向错觉(positive illusions)的玫瑰色泡沫,所以我们倾向于高估朋友们对我们的喜爱程度,低估坏事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粉饰过去,以适应现在。例如,当大学生被要求回忆大学预科的成绩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稍稍夸大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几乎没有人会说一个比实际取得的成绩更低的分数。此外,父母会把子女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开明培育,把子女身上不讨父母喜欢的特征归咎于基因。我们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未来抱有积极的幻想。在一项研究中,与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男性相比,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男性更认为自己的病情不太可能发展为典型的艾滋病。现实的融洽版本 使我们保持理智。
使我们保持理智。
请相信我,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本书在你和你的家人之间挑起了麻烦,打破了你对自己童年的幻想泡沫,或者加重了父母的焦虑感。当你读这本书时,请尝试从孩子,而不是从父母或准父母的立场来看。在我看来,我的读者是一个家庭的产物,而不是负责养大一个孩子的人。如此一来,当读到有证据表明父母的抚育方式可能是导致某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时,你就不太可能采取防御的态度,感觉需要为自己辩护。本书的目的是,让你更好地了解你的童年经历如何影响着你现在的生活,以及这种知识可以如何帮助你。
事实上,这其中隐含的一条信息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伤害是正常的,每个人在童年期都会遇到问题,若能改变我们对“正常”的界定,我们所有人都将会因此获益。例如,人们对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群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有1/5的人一直受到精神疾患困扰,多达1/3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段可能受其困扰。还有研究表明,有20%~40%的人虽然表现出了严重的症状,却并没有患上精神疾病。我们现在应该改变“只有‘我’一个人有问题”的信念,进而意识到,生而为人就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神经症是惯例,而不是特例”,这可以使我们发现,我们并不孤单。这也是一个起点,我们能够借以了解哪里出了问题,认识到自己有选择的余地——可以简单地重演过去,或者重写剧本。
这本书有助于我们审视情绪。就像会计师需要辛辛苦苦地对企业的交易进行年度审查,看看它的财务状况如何,你可以用这本书来审视你的童年期发生过什么,查明它是如何对现在的你造成影响的。每一章的结尾都有一个简短的练习,通过这一练习,你可以运用这一章刚刚讨论过的内容,对自己的某些方面进行审视。你可以在读到每章结束时,趁热打铁做练习,或者等到读完这本书之后,再回过头来做每一章结尾的练习。读这本书时,请随身带一支钢笔或铅笔,读到有共鸣的地方,你可以顺手在边上做个记号,当你以后再读时,它就会在那里提醒你。这个审视将有助于定义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会这样,当你读到第6章时,你将能运用我提出的一些建议改变自己了。
你可以继续像个演员一样,在你的家庭中无休止地重复扮演同一个角色,有人在很早以前就写好了这个剧本了。或者你可以成为自己剧本的作者。但是在你开始这项工作之前,你需要多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你的命运没有被编码到你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