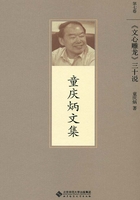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二、《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现实针对性和文化内涵
以现实的、历史的和逻辑的、综合的方法(我自称为“文化诗学”)来解决一切文学理论问题,是我理解问题的基本方法。对于《文心雕龙》的文体观念,我坚持我的一贯的研究方法。
首先,关于《文心雕龙》的现实针对性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理论家写一部著作,提出一种观点,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总是针对某个现实发生的,或历史遗留的问题而发。一部《文心雕龙》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或它的针对性何在?这是我们理解刘勰《文心雕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刘勰在《序志》篇说:
……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8]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指出刘勰生活的时代,诗人、辞人爱好人为地玩弄词句技巧,浮滥而爱奇,而不重作品的内容,不贵乎“体要”,其结果是“文体解散”,这是在当时写作中存在的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怎么办?这就要从端正文体入手,特别要重视“体要”。
但是作家要在写作中防止“文体解散”,并非易事,更不是了解一下文章体制的要求即可,这么单一的问题,而是寻找规范的文体从何来的问题,这就涉及“文之枢纽”中文原与文变的问题;又涉及各种文体的具体来源、正确要求和典范树立的问题,这就要“论文叙笔”(这其中就包括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当问题弄清楚时,文体的规范问题就解决了吗?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还必须了解创作论、作品论等各种具体问题,其中重要的有“神思”、“定势”、“风骨”、“体性”、“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附会”等问题。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刘勰的思考,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的著作具体论述了文章的起源、创作、结构、欣赏等问题;另一方面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也力图要联系文体,解决“文体解散”的弊端,或者说全书都又涉及文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认为“《文心雕龙》一书,实际便是一部文体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许徐复观的思想从《齐春秋》的“彦和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的说法中得到启发,也未可知。徐复观的这一意见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毫无根据的。
其次,关于文体的来源及其文化内涵。
文体起源于“五经”,这是刘勰在著作中明确指出来的。这里可以引用他三段话,他在《征圣》篇说:
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9]
这意思是说,论文一定要用圣人的标准来检验,并探寻如何以圣人的经书来作为根据。《易经》里面说,辨明各种事物,给予正确的说明,使语言有决断,而辞意完全。《尚书》里面说,文辞注重体现体要,不要喜欢奇异。所以知道使言辞正确用以建立论点,体要所以使文辞成。这样写成的文辞不会有猎奇的毛病 ,建立论点有措辞决断的作用。纵然精妙的意义写得曲折深隐,也并不会妨碍论述的正确。虽然文辞含蓄婉转,也不会使体要模糊。体要与文辞是相通的。这些都可以在圣人的文章里看到。这段话中,基本的意思是无论文辞怎样,是含蓄婉转,还是曲折深隐,只要抓住了“体要”,文章也就成功了。一段话中两次提到“体要”这一文体的核心概念,说明了“五经”文体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善于掌握“体要”。由此可见,“体要”
的源头在“五经”中。进一步说,文体的源头要从“五经”那里去找。
更重要的是《宗经》中的“体有六义”说: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10]
这段文章的意思是:如果能效法五经来写文章,那么学习文体就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中“体要”和“体貌”又特别重要。“五经”文体中的体要、体貌有哪些呢?有六个含义:第一是要情感真实而不虚假;第二是风趣纯正而不杂乱;第三是事实可信而不荒诞;第四是义理正确而不歪曲;第五是体例精约而不繁杂;第六是文辞表现而不过分。扬雄用雕琢玉器作比喻,说明“五经”虽文章含有文采,但又要依靠德行来确立,而德行则又依靠文章来流传。孔子用“文、行、忠、信”来教育学生,而把文放在第一位,正像德行与文采相互衬托,前后两者互相促进。后世的人学习德行,树立名声,没有不以圣人为师的,但在利用文辞写作,就很少学习“五经”的写法了。后来汉代的辞赋家离开了“五经”的源头,“文体”就差不多要“解散”了。这段话中的“体”,不是某些研究家所说的一般文章,明显是指文体。这一点我在《〈文心雕龙〉“体有六义”说》中已做了说明。要论述的是“情深而不诡”等六句话的内涵。“情”是文体的一个基本要素,其他“风”、“事”、“义”、“体”(体要或体貌)、“文”(文辞)也是文体要素,那么“六义”即是文体的六个要素。这些要素都有优劣之分或程度之别,如“情深而不诡”,即“情感”有深厚与诡异之别,“风清而不杂”,即格调(风)有清新与杂乱之别,“事信而不诞”,即事实有真实与虚假之别,“体约而不芜”,即体要有简约与芜杂之别,“文丽而不淫”,即文辞有丽雅与浮靡之别。如果六点皆优,那文体必定是真文体、好文体;如果六点皆劣,则“文体解散”,没有文体可言;如果优中有劣或劣中有优,则视情况和程度而论。劣多而严重者,即可视为“文体解散”。
第三段话,也是《宗经》中的一段话: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11]
这段话具有总结性。一言以蔽之,所有的文章文体都来源“五经”。“统其首”、“发其源”、“立其本”、“为其根”都在说文体来源于“五经”。这里不单是一般所说的文体中的体裁问题,根据刘勰自己所说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以及与文体相关的问题,如《体性》篇的“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因内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等观点,都是基于文体观念,刘勰是在“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包含了先秦以来文体观念的诸多丰富的内容。
刘勰的文体观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但人们只是笼统地说“原道”、“征圣”和“宗经”,并没有具体地指出来。把刘勰已经指出的东西略去了。其实,这是问题本质,是不能略去的。在我看来,刘勰的文体观念背后还有具体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上面所引刘勰这段话,表面是指“五经”,实际上道出了中华文化中的五大特点。
如中华文化讲《易经》,《易经》讲“易”,那么“易”是什么?最初可以解作“简易”。原来“易”是讲卜卦的、讲阴阳的。卦开始时是“易解”的,“卦”是一定的,“—”代表”是天代,两个“-”是代表地,有“天地,不能没有万物,所以三个“”,就是天地物结合,构成一卦。后来卦加爻,仅卦就有六十四卦,爻就更多,卦爻都要进行复杂的推演,于是“简易”就成为不“简易”了,它逐渐成为了儒家的一种“数目的哲学”(朱自清语)。它利用奇数、偶数对于天地、阴阳、万事万物、子嗣、人寿等一系列天地万物与人的变化问题,做神秘的、复杂的计算和推演,于是“易”的含义多在“变化”的意义上使用。刘勰这里说,“《易》惟谈天”,神妙之极,但可以实用。所以《系辞上》说它含义深远,文辞又十分精美,只是事理难懂。孔子读《易经》,读得那么认真,以致竹简的皮带断了三次。原来“易”已偏重于论,它是圣人探索学问的奥秘的宝库啊!正因为中华文化一开始就讲“易”,这在文体上就有了论、说、辞、序的区别啊!这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一种文化。
刘勰又认为“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这也是说中国的文体与中华文化在根源上的联系。《书》即《尚书》,《尚书》“是中国古代记言的历史”,记载了古代时期一些资料,“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12]这以后,这种文体就发展起来,诏、策、章、奏,就是其中常见的几种。
另外,刘勰又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这里所说的“诗”是指古代的,以赋比兴为特点的《诗经》。《诗经》最早是古代的歌谣,后来用文字记录下来,先秦时多称“诗”。“诗言志,歌永言”,诗是言说人的情志的,两汉后才尊称为“经”。《诗经》本身就有文体,风、雅、颂是三种体裁,赋、比、兴就是文体中文辞构成的方法。对于《诗经》,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此不多言。要指出的是在刘勰看来,《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文体的来源之一。其中“赋、颂、歌、赞”是其中流行的体式。
又,刘勰认为“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重“礼”是中华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礼”是什么?刘勰的文体观念如何折射出中华民族多“礼”?我们似乎可以从孟子的“四心”说,看出一点端倪。孟子主张“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3]“礼”既然是“辞让之心”的根本,那么人与人之间讲究“辞让”,就必然折射出“礼”来,礼不仅仅是人之心之理,还必须从实践中表现出来,从口语交往和文章撰写中表现出来,这样“铭、诔、箴、祝”等文体,就是“礼”的实践的产物。铭、诔、箴、祝等文体也就具有浓浓的文化内涵。
最后,刘勰认为“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编著的一部编年简史,写得很简明。后来有《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后人总结“春秋笔法”,“以一字为褒贬”(杜预语),又说其“微言大义”(《汉书·艺文志》语),还有司马迁所说的“笔则笔,削则削”,都接近于从文体的角度来评《春秋》。刘勰认为以《春秋》为根本,才生发出纪、传、铭、檄这些体制。这些体制背后就含有《春秋》的文化意义。
讲中华文化,不能不讲“五经”或“六经”。现代国学家马一浮曾指出,“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凡诸子、史部、文学研究皆以诸经统之”。[14]这是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言论。讲中国古代文体不能不讲“五经”,刘勰理解这一点,所以他讲文体,是从《原道》《征圣》《宗经》篇开始讲的,他设置“文之枢纽”这一部分,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讲清楚文体来源“五经”和它的古典文化内涵,但只能先简略地讲,后面各篇再展开详细地解释文体所关涉的各种问题。徐复观认为《文心雕龙》“下篇才是文体论的基础,也是文体论的重心”的说法是不妥的,必须把文体论的基础按照刘勰自己的意见移到“上篇”,先讲清楚文体的来源与文化内涵,讲清楚“体有六义”,然后再涉及文体观念的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