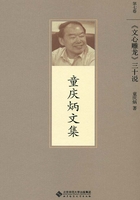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三、“原道”说总结了中华古代的创作和理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提出文原自然的思想,把古老的自然作为文章和文学的本体的来源,这绝不是偶然的。刘勰的“原道”说充分地总结了此前产生的创作和理论。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先秦时期提出的“兴”说。产生于《诗经》中的“兴”,历朝历代对其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都有道理,这里不重复,我只提出如下对“兴”的两点看法。
第一,“兴”作为心与物交融的产物,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早期,这不是偶然的。“林奈分类法”的做法把看起来极不相同的东西归并为一类,这往往是属于儿童和原始人类的行为。“兴”起源于西周早期,那时我们的古人常常用儿童眼光或原始人的眼光去观看周围的事物,于是《诗经·关雎》里写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思是,关关叫着的大水鸟,河里小洲来停留,苗条善良的小姑娘,是人家的好配偶。在这里,关关叫着的大水鸟,与一个小伙子向一个姑娘求爱,有什么关系呢?《诗经·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意思是,南方有棵高树,底下不好停留,汉水有位仙女,真不容易追求。树下不好停留与仙女不好追求有什么关系呢?《诗经·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温和的东风,带来了好雨。和睦过日子,不该发脾气。东风带来的好雨与家庭和睦有何关系呢?《诗经·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意思是,风凄凄,雨凄凄,还有打鸣不止的鸡,盼着的人儿来到了,我心上的烦躁才平下去。[15]风雨凄凄、打鸣的鸡与盼望的人回来了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时候,科学的认识比较少,科学分类也还没有开始,于是人们常常会把属于物与属于心的不同质的事物“混淆”“混同”在一起,以表达心中对事物的表现性的理解。又如《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春天的桃花开得很红火与女子出嫁的欣喜吉庆的场面本来没有联系,这不是一类的,是不同质的,但早期的人类并不懂什么科学分类的道理,而把它们归并为一类,以表现他们快乐温暖的心情,后人把这种写法称为“兴”。朱熹《诗集传》解释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没有说明“他物”与“所咏之词”是什么关系,从上面所举的例子看,实际上两者是“异质”的,但又是“同构”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上升的结构,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也是上升的结构。《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是下降的结构,但“盼着的人儿来到了”是上升的结构,所以这首诗的结构是下降而后上升。
第二,“兴”一般都是自然事物的描写,古人把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自然整体中可以寻找到共同的特征,如上升与下降,沉落与浮起,延伸与收缩,前进与后退,向阴与向阳,躁动与宁静,等等。自然事物中这些特征,实际上是一种力的结构,自然中这种力的结构,与人的情感活动的力的结构,常常是一致的。物的变化可以与人的情感变化相对应。人有喜怒哀乐,婚丧嫁娶;景有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于是诗人就借描写自然事物的特征及其变化,以表现与人的情感中相对应的情感及其变化,描写自然景物成为中国古人诗歌,特别是唐诗宋词里最重要的现象。刘勰专门研究过“兴”,他从“兴”的这种意义中体会到,写文章、写文学作品,都要以自然为本,还要有相应的情感的表现性,两者缺一不可。刘勰一定理解,人在观看物的那一刹那间,物已经不是原物,已经带有人的心理印痕。刘勰的确是有这种体会的,他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批评了汉代初年许多赋家,说他们只是“品物毕图”,只知道细致地、全面地、铺排地描写“物”,而没有通过物的描写表现出“情”来。所以在《诠赋》篇,刘勰要求赋家既要“情以物兴”,又要“物以情观”,在物与情之间互生互动,并找到均衡点或结构点。刘勰似乎是深入地思考并总结了这些问题,他觉得有心智的人看见了“物”,不会仅仅把自己的观感停留于物理性和生物性的“物”上面,一定会把观感延伸到非物质的“情”上面,这就是《物色》篇所说的“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文原于道”就从这些体会中提炼出来。我不同意某些学者把刘勰的《原道》篇孤立起来看,更不同意把《原道》某几个句子孤立起来看,而要把《文心雕龙》全书打通了看。这样,他的《原道》篇的说法与《诠赋》《神思》《时序》《物色》等各篇的说法是一致的,一方面要以“自然”为本,重视“天文”、“地文”;另一方面又要升华到“人文”,这就是文源于“道”。
“异质同构”的理论在中国古人那里,似乎也有初步的思考。《易·系辞下》提出“观”、“取”、“通”、“类”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观象”、“观法”和“观鸟兽”都是对着天地和鸟兽来观看,是人的知觉活动。那么这种以客观的周围世界为对象的知觉活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这就是要观看到“天象”、“地法”、“鸟兽文”,“天象”、“地法”、“鸟兽文”这三者显然是不同的,但又有相近、相似之处,那就是无论“天象”、“地法”,还是“鸟兽文”,都有复杂的“纹路”,构成错落有致的图文。这种图文看起来像用笔画出来的美丽的图画,或者像我们最早的甲骨文的构形。进一步,这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图画或构形,用来制造“八卦”的意象,可以起到通神明的作用,可以类似万物之情状。这段话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客观存在的物,天、地、鸟兽等;第二层面是人的知觉活动,即“观天”、“观法”和“观鸟兽”;第三个层面是通过“八卦”意象来类比“万物之情”。第一层面是物质的,第二层面是非物质的,它们是异质的;但物质的层面不会停留在此,一定会通过人的知觉活动,延伸到第三层的人的主观的情,这样延伸出来的“万物之情”就可能是与物同构了。
更为明显的理论是“君子比德”说。“比德”理论是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共同的思想,但各有思路和特点。这里无法展开来论述,仅就儒家的“君子比德”说与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论做一个简要的比较。中国古代的“比德”说,主要是说自然物对象常常可以作为人的道德、精神的象征,于是文学创作中可以通过描写自然物对象的特征,来表现人的道德美与精神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最早提出“君子比德”说。“比德”一词最早出现于《荀子·法行》:“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所以贵玉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这里的“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意思就是,玉,可以用来比喻君子的道德。为什么玉可以用来比喻君子之德呢?难道是因为玉少而珉(一种似玉的石头)多,即“物以稀为贵”吗?孔子说不是。孔子认为玉虽然是一种物质,但它身上有非物质的道德意识,所谓“仁”、“理”、“义”、“行”、“勇”、“情”、“辞”,这些都是道德意识。孔子认为这些道德意识与物质性的玉可以归并在一起来理解,换言之,这就是“异质”(一个是物质,一个是意识)而“同构”(都具有广义的道德意识)。看来,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在对物体的物质属性加以肯定的同时,更看重物体所象征的精神意识。
在《论语》中,孔子对“水”特别有感情。《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按照孔子的本意,是讲时间就像流水,不会再流回来,劝告人们要爱惜时间。但进一步也可以让人理解为—催人上进,修养美好的道德,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水本是物质,但在这里转化为精神的象征。
《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孟子解释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孔子的三句话要联系起来理解。但孔子突出的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为何乐水呢?因为水流动多变,无所不至,这和知者的见识广博、心思灵活有相似之处,这就使知者欣赏水。仁者为何乐山呢?因为山稳重崇高,巍峨而立,这与仁者的崇尚道德、坚定不移有相似之处,所以仁者乐山。水和山都是物质,但在这里成为了智与仁的象征。
《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据《庄子·让王》等多种资料,孔子这句话是他困厄在陈蔡时对子路说的,意在以松柏有耐寒之品格,来比喻他自己临危难而不失仁义之心。
玉、水、山、松柏等都是无意识的事物,但孔子通过自己的知觉活动(主要是视觉活动),就能延伸出非物质的意识、精神来,这是什么原因?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解,不要过分区分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实际上,“感性世界中处处有宇宙中各种力的相互作用的侵入。这种宇宙之力既支配着星球和季节的变化,也支配着尘世间各种细小的事物和事件。与之相悖的行为固然会导致混乱和冲突,但人的感官并不是生来与之相悖的。例如,刚生下来的婴儿就最接近于‘道’”。[16]阿恩海姆这样说是否有些夸大其词呢?实际上并不夸大其词。正如阿恩海姆发现的那样,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不是决然分开的,它们都受宇宙的“力”所支配,换言之整个宇宙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统一性。过分的逻辑与理智反而会违背这种“力”的结构,从而也就违背了规律,违背了“道”。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面对一种困境:一方面,要把感官的模糊的认识与理智的明晰区分开来;但另一方面他又让感官对理智说出了轻蔑的话:“可怜的理智,你从我们这儿得到证据,而后就想抛弃我们,要知道,我们被抛弃之时就是你垮台之日。”[17]
好了,我觉得应该把话拉回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当刘勰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的时候;说文“与天地并生”的时候,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他所说的“原道”是天文、地文和人文的内在的统一。是的,太极是天地,是自然,是物理世界,但在人的知觉活动中(“惟人参之”),它已经被提升为人文。人文是意识、文化和精神,是心理世界,但它和“太极”异质而同构,这就是“神与物游”,这就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啊!这可能就是鲁迅所说的“汗漫”处吧,祖保泉先生所质疑的“混为一谈”吧!看来,我们只有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同时又在西方理论的“照亮”中,才能理解刘勰的“原道”说。
(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
[1]鲁迅:《鲁迅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手迹原文无题,编者加《“诗论”题记》。首载《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鲁迅研究年刊》, 1974年创刊号。
[2]蒋祖怡、韩泉欣:《略说鲁迅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批判继承》,载《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12月,第11卷第4期,第66~67页。
[3]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4]祖保泉先生的书中在谈到普列汉诺夫的“文学起源于劳动”后,曾说“这只说明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理论家所能完全肯定的,我们更不能责怪包括刘勰在内的古代文学理论家们不知道这一科学观点”。可祖先生刚刚说完不要“责怪”,立刻就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责怪”刘勰不晓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了。见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第12页。
[5]《〈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6]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538页。
[7]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8]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9~610页。
[9]转引,同上书,第614页。
[10]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9页。
[1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4~615页。
[1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619页。
[13]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14]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
[15]以上各篇译文均引自李长之:《诗经试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6]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17]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