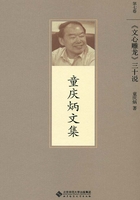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一、刘勰的“原道”说是唯心主义的论调吗?
1999年,我在《遵义师范学院学报》杂志上发表了《〈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一文。时间过去了十多年。十多年后,我又一次给学生讲《文心雕龙》,发现了老一辈的有些学者对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没有完全理解。我自己十年前的理解也缺乏深度。此文我想尝试用西方现代的心理学观念来解释刘勰的“原道”思想,看看西方的思想是如何“照亮”刘勰的思想的,以补前文之不足。也想就鲁迅先生对“原道”的看法,当代古文论学者、“龙学专家”祖保泉先生的一些看法,提出来讨论,就正于方家。
鲁迅是认真读过《文心雕龙》的,他的著作中有许多思想来自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里不拟一一论列。鲁迅的著作中直接明确提到刘勰的有五处。他早年的《摩罗诗力说》一文,在议论屈原时,曾引用刘勰《辨骚》篇的话,说:“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这是借刘勰的话说明屈原的《离骚》影响有限。鲁迅的《吃教》一文,也谈到刘勰,说:“达一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做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刘勰作为晋以来的名流,也是都要在儒家、道家和佛家之间吸收思想营养。鲁迅这个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刘勰文论思想的综合性是很有帮助的。此文接着“吃”的主旨,还谈到刘勰由“不撤姜食”一变为“吃斋”,于肠胃里的分量原无区别。鲁迅谈论刘勰最重要的地方,还有以下两处。一处鲁迅在《“诗论”题记》中提到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地位,说:“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苞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这是把刘勰的《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做出了肯定性的高度评价。另一处是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道:“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其说汗漫,不可审理。”这一段显然是对刘勰把文章与天地自然相等同提出质疑。所谓“汗漫”,即空泛,不着边际,“不可审理”,即不可详细考察。鲁迅对于刘勰文章源于自然之道的评论,很自然就引起人们的研究。
早在1980年,就有学者发表文章说:“从今天看来,刘勰的这些说法,的确有许多糊涂观念在里面。首先,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并不是‘自然之道’的直接表现。文学确实反映了自然的道理或规律,但这种反映必须经由人类的头脑,必须通过艺术的形象,也就是说,它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现实在人类头脑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映的产物,是意识形态,属于社会的精神现象。因此,像刘勰那样,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自然现象混同起来论述,就难免不流于荒诞不经……充满神秘色彩的唯心主义的说教。”[2]前辈学者祖保泉教授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和教学,贡献甚多。仅就他1993年出版的70万字的宏著《文心雕龙解说》而言,其注释、其解说,全面细致,功力深厚,多有创见,给后辈学人很大的启发。但对我们的父辈学者来说,他们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唯心主义批判,“唯物”就是“进步”,“唯心”就是“反动”,这种思想深入骨髓。这样,就把唯物认识论(其实那是对唯物认识论带有许多偏颇)看成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对所研究的对象,处处都要把它们放到“唯心”、“唯物”那个天平上去衡量,从而把复杂的学术问题公式化和简单化,丧失掉学术研究应有的品格。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祖保泉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有时(我仅说“有时”)不免也陷入那种“唯物”和“唯心”,“进步”与“反动”的旧套子中去。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有时就用旧套子套新事物。这些似乎是多余的话,但我认为不多余,所以不得不先说,并把这段有关历史语境的话,摆在这里,意在说明我与前辈学者商讨问题时,也在检查和审视自己。我这里要商兑的,就是鲁迅的关于刘勰的“道”、“汗漫”而“不可审理”的批评和祖先生对刘勰“原道”的理解。祖先生在《文心雕龙解说》一书中,在引用了鲁迅的上述质疑后,也给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
概括起来,祖先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给刘勰扣了两顶帽子——“历史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刘勰在《原道》篇中是怎样犯了“历史唯心主义”错误的呢?祖先生引了刘勰的《原道》头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然后质疑道:“《原道》篇开头就这么引人注目地提出问题,照刘勰看,有天地时便有人类,也便有文章。天、地、人、文四者都是同时出现在宇宙间的。也就是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文章、文字)与物质的天地(包孕万物)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存在决定意识,或意识决定存在的关系。显然,刘勰是丢掉了人的社会性、脱离了人的社会历史发展来谈‘文’的起源的,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论调。”[3]祖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来批判刘勰,认为刘勰没有认识到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观念形态是第二性的;更进一步,又用人的历史社会性来评论刘勰写于6世纪的文章,这是否“责怪”[4]过分了呢?当然,祖先生似乎也不是要求刘勰的“原道”思想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他书中对古代学者常常满口称赞他们朴素的唯物思想。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地体会刘勰《原道》篇全文和刘勰《文心雕龙》全书,刘勰朴素的唯物思想不是贯穿《原道》全篇和《文心雕龙》全书吗?仅就《原道》篇看,黄侃先生在北大的讲稿就指出《文心雕龙·原道》篇,“……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章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显然,黄侃先生的理解是有道理的,刘勰《原道》篇强调的就是“自然”的演绎功能,自然→人心→语言→文章(包括文学),文章是以自然为源头的,这难道不是朴素唯物主义吗?又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也曾说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又说:“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刘勰在叙述了文章发展脉络之后,还说:“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这些话语论述到了文章与人的关系,文章与世情的关系,文章与时代的关系,就不仅仅是朴素唯物主义了,就是拿到今天来立论,也是很精彩的,怎么能说刘勰“是丢掉了人的社会性,脱离了人的社会历史发展来谈‘文’的起源”呢?
看来,祖先生硬要给刘勰戴上“历史唯心主义”的帽子,关键就在于他认为刘勰把“天、地、人、文四者”并举,“同时出现在宇宙间”,没有说明物在先心在后,没有说明物决定心的问题,这就把物与心哪个是第一性,哪个是第二性;是物决定心,还是心决定物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交给刘勰,并要他回答。生活于5~6世纪的刘勰的确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回答马克思19世纪才提出的问题。
况且,我们既然是谈论刘勰的思想,最好要放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考察,而不宜以西方现代的问题来为难他、“责怪”他。在心与物问题上,西方文化讲“唯心”与“唯物”,那么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心与物谁先谁后的问题?谁决定谁的问题?根据回答的不同,这就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一正一反的对立。东方的中国则不同,中国文化很早就形成了“中道”观念,《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中道”思维,把天下一切事物都分为“两端”,如乾与坤、心与物、阴与阳、动与静、高与下、内与外、方与圆、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等。对于“执其两端”而取其“中”,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走极端,不绝对化,不惊世骇俗,不标新立异,其真正的意义是说:两端之间在一条线上,有一个中间过程,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包容的。比如心与物是相通的,著名国学家钱穆在《中华文化十二讲》中曾说过,“中国人观念,主张心与物相通,动与静相通,内与外相通。相通可以合一,合一仍可两分。既不能有了心没有物,也不能有了物没有心。心与物看来相反,实际是相成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和《文心雕龙·物色》篇直接讲心与物的相互关系,就是按照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中的观念来理解的。《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一方面是“睹物兴情”,另一方面是“情以物观”,两者相反相成,相互促进,不存在对立关系。《物色》篇则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一方面是心随物以宛转,另一方面是物与心而徘徊,也是心物相反相成,相互促进。祖保泉先生所引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句话,所关注的也是心物关系问题,即文章与作为自然的天地是相互生成的,讲的是自然与文章的并生关系,而不是讲自然与文章谁先谁后的问题,谁决定谁的问题,刘勰所关注的是自然与文章“两端”一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就后文看,刘勰讲了自然中“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的美丽,又讲“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这里的“性灵所钟”,强调了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凝聚、集中和汇合的功能,这就更突显人的性灵的作用,并没有“脱离人的社会发展来谈文的起源”的弊病。这段话最后的结语是:“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里的“有心之器”是指具有心智的人。有了人,就有人的发展历史,这是当然之理。这结语把物与人分开,但更强调的是有心智的人在文章产生中的能动作用,说明人是多么可贵,这是重视历史传统的中国古人一贯的人文主义的体现。所以,我认为祖先生给刘勰扣“历史唯心主义”的帽子是不妥的。这种不妥,既表现在不可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要求中国古人,又表现在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语境进行解读的误解。
祖保泉先生给刘勰扣的第二顶帽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这实在是太“高抬”了刘勰,因为一般人都认为黑格尔提出“理念”为万物的精神本源,这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的理论是“先验”说的;刘勰生活于5~6世纪,理论的性质是经验性的,怎么能独出心裁或标新立异而提出“精神本源”问题呢?祖先生在其书中三次说到,刘勰是“客观唯心主义”,归结起来是对“神理”、“太极”、“圣文”等词语的训诂问题。对这些词语的训诂,同样要进入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语境,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解释,这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是没有对应关系的。
例如,对于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的“神理”一词,我在十几年前所写的那篇《〈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一文中谈到,“刘勰说:‘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龙献图’、‘龟献书’在刘勰看来是真实的自然。这里有人可能要问,篇中所提的‘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这也是自然吗?回答说:是。在我们先人的自然观念看来,这也是自然。古代的人们对自然并没有今天人们科学的认识,常常把一些传说的东西,想象成真实的,当成自然存在。因为先人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对自身的能力是缺少信心的,所以把语言文字的最早创造归功于龙献图、龟献书,是不足怪的,这是先人的古老天道自然崇拜论在起作用。自然崇拜论的实质,就是把世界上一切神秘的、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为自然的本然存在。把平淡的还给自然,把神奇的也还给自然,把一切荒诞的都还给自然,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王充《论衡·自然》中说:‘河出图,洛出书……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笔墨为图书乎?天道自然,故图书自成。’我认为用王充讲的‘天道自然’,来理解刘勰的‘道’最为合理。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刘勰并不是从认识论的视野来看待天道自然的,而是从古代的朴素的存在论来看天道自然的。人进入自然,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自然不仅仅是认识的对象,而且也是体验的、感悟的和想象的对象。自然是神奇而神秘的,不可预测的,所以刘勰给他的‘自然之道’加上一个‘神理’的规定的”。[5]我至今仍觉得我的理解是对的,对于远古人类而言,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感、不可知感,于是用后人所用的“互渗律”来认识、想象周围的事物。远古人类与周围现实所形成的关系本身就是客观存在,我们不能用我们今天的科学认识,来替代古人实际存在的状况,并指责他们是“唯心主义”。
又如对“太极”一词的解释,也关系到对《原道》篇的理解。刘勰在《原道》篇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祖保泉先生认为,“太极”
一词在刘勰之前,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也许祖先生的说法是对的,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祖先生偏偏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理解,以便作为批评刘勰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根据。就刘勰的《原道》篇的语境看,“太极”来源于《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郑玄注《易·乾凿度》称“太极”为:“气象未分之时,天地之所始也。”这个解释可能最为准确。当代著名学者高亨则说:“太极者,宇宙之本体也。宇宙之本体,《老子》名之曰‘一’,《吕氏春秋·大乐篇》名之曰:‘太一’,《系辞》名之曰‘太极’。”[6]据此,我们可以把“太极”理解为宇宙原始混沌之本体。刘勰的“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即可理解为人类的文化、文学和文章,最早来源于古老的自然。为什么我们要把“太极”理解为万物的“精神本源”呢?
以上所述,说明把刘勰的《原道》篇的“道心神理”批评为“历史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把属于刘勰的东西还给刘勰,把历史还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