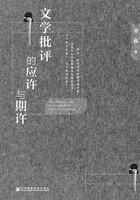
一 作家 读者 批评
对一部文艺作品的批评,大致有这样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欣赏性的,也就是纯感性的、直觉的、先验的。我们看了或听了一部作品,喜欢它或者不喜欢它,喜欢它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方面,比如情节、人物、台词、旋律等,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它恰好在那个时间点触动了我们的某根神经。这种批评是只言片语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但显然,它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托,也不见得经得起推敲。我们看了王家卫的电影,会喜欢他“有味道、无意义”的台词;看了东野圭吾的小说,会折服于他缜密的推理;看了胡风的诗歌,会为他的激情所打动……这几乎是所有人对其文艺作品的评价,不管他有没有进行过文学与艺术评价的相关训练与学术积累。但如果上升一个档次,我们也许会关注到与王家卫相关的法国“新浪潮”“作者电影”;会关注到胡风的“七月派”,关注到他的文艺思想、人生经历等。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层面,知识性的、经验的、发散性的文学批评,这里已有了一些历史的、文化的、思想性的成分。我们欣赏了某部文艺作品,试图去了解它背后的内涵,将眼光放宽放远,去研讨艺术家的风格特色、品性喜好,艺术品产生的年代、思潮,归属于什么流派、引起了哪些社会反响,等等。这样的文学批评,有了些学院派的味道。从某种角度来说,研究就是选择一个恰到好处的点去切入作品,独辟蹊径也好,高屋建瓴也罢,然后立论驳论,诉诸文字,论据论证——就成为我们现阶段的大部分“文学批评”。这样的文学批评更多的是在表现作品而不是评价作品。它适合作为文学史或艺术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但对比真正的文学批评,还有相当的距离。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层面——审美性的批评,是最高也是最难实现的,它给作品以生命和诗意。之所以说它难以企及,是因为这一境界的实现需要批评家经年累月的知识积累和心性磨炼,还需要灵性的感悟和智慧的启迪,才能将优雅的审美观内化为自己的语言评判,而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和第二种发散性批评的区别,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宗教和迷信的区别一样。前者追求的是永生永世的超越,而后者看重的则是现世现报的功利。1827年10月,雨果才华横溢的批评文章《〈克伦威尔〉序言》发表,文采飞扬又不容辩驳地挑战了在欧洲主导两百余年的古典主义权威:
我们把上面所讨论的这些事实加以简要的概括,可见诗有三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相应地和一个社会时期有联系,这三个时期就是抒情短歌、史诗和戏剧。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而近代则是戏剧性的。抒情短歌歌唱永恒,史诗传颂历史,戏剧描绘人生。第一种诗的特征是纯朴,第二种是单纯,第三种是真实。行吟诗人是抒情诗人向史诗诗人的过渡,就好像小说家是史诗诗人向戏剧诗人的过渡。历史学家与第二个时期一道来临,编年史家、批评家则和第三个时期同时产生。抒情短歌的人物是伟人:亚当、该隐、挪亚;史诗的人物是巨人:阿喀琉斯、阿特鲁斯、奥里斯特斯;戏剧的人物则是凡人: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奥赛罗。抒情短歌靠理想而生活,史诗借雄伟而存在,戏剧以真实来维持。总之,这三种诗是来自三个伟大的泉源即《圣经》、荷马和莎士比亚。[1]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美文”。不论是对欣赏者还是对艺术家,文学批评对文艺作品的审美启迪都类似于阿拉丁的神灯、芝麻开门的秘诀。有了它,就敲开了美学宫殿的大门,如临仙境,使人恍然大悟;少了它,则无法真正体会品读作品,如盲人摸象,事倍功半。
作家写作的坚持与读者阅读的不认可,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面对几个古老的问题:作家到底是为了什么写作?文学作品是写给谁看的?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生存样式繁复的时代,文学担当了什么?批评改变了什么?
作家为什么写作呢?大致看来,一是生存之需要。写作是安身立命之本,就好像工人为什么做工,农民为什么种地,教师为什么教课。既然选择了“卖文为生”,那么姑且就这样做下去,作品是写给工农兵、写给人民大众的。我写,故我在。二是心灵之需要。写作是为了敞开生命,倾听语言。司马迁“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著《史记》藏名山、传大都,他这一生所受的屈辱与斥责都可释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史铁生说,我寂寞,所以我写作。他们把写作视为献给自己的情诗,是要把人生磨砺记录下来给别人看。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作家写作是因为心理郁积无处安放。三是人性之需要。人性是极为丰富复杂的,面对爱、面对罪与罚、面对彼岸,作家穷其文字也难以将人性写得圆满。巴金说,创作总根源于爱;萧红说,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为着人类的愚昧;徐志摩说,诗歌的性灵全在对爱、自由、美的追寻。这样的写作,写给了文学的历史。当然这几种分类未免简单而武断,因为作家的写作是流动的、不均衡的。有的作家本是为生存而写作,却逐渐使自己的文字上升到人性之美的真纯,比如沈从文;有的作家本是为“玩票”而写作,却使作品成为一座城、一段历史的宝贵记录,比如老舍。按常规思维,为生存而写作的作品应该是最接地气的,否则便不会有销路,作家也就不会有收入。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或许由于题材、主题太切近现实了,读者反而质疑这类写作的真实性,也就谈不上更深的感动与升华。
对此,作家可否自问:我的写作表达了什么,读者又能从中读出什么?我的文字以怎样的方式书写了生活,会给未来留下些什么?写作的根基问题如果不搞清楚,作家便没有理由苛责读者的不解风情。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被毁掉了——烧了,炸了,只剩下一本或几本这几年的小说,小说能否真实地反映或代表今天的人或事?一部分的真实也好,“一声叹息”的真实也好。是不是写青春就要在校园里风花雪月,喝咖啡、穿名牌、开豪车?是不是写农村就要让底层被苦难碾压得喘不过气来?是不是写贫困就可以让人为三百块钱杀人,写家暴只能让媳妇烧了房子来报复?是不是写职场、写官场就要让白领、公务员尔虞我诈、心力交瘁地踩着别人向上爬?是不是写历史就要让历史顺应当下的伦理价值观?当然不是的,说到底,还是作家为什么写作和如何写作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个生存多元、信息多元、审美多元的时代,读者为什么仍然阅读呢?有一派是人生经验派,读作品是为了追随经验。他们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学习成长,在《简·爱》中学习恋爱,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学习生存。对这一类读者,文学不过是手段,是通向目的的途径。况且对经验来说,文学并不是“特供”的,去“百度”“360”远比文学来得快捷、全面。这类读者跟文学的关系只能若隐若现。另一派是人生幻想派,读文学是为了获得镜像式的意淫。他们极易将自己移植到作品中去,东施效颦地误读人生,幻想自己是灰姑娘、白雪公主,期待白马王子、霸道总裁的降临。而这类读者近年来常常被文学的图像化——也就是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网络游戏等分流走,他们也并不是文学的忠实爱好者。最后留下来的一派就是接受美学所谓的“真正的读者”了,他们是为阅读而阅读的读者,是能够投入地、欢娱地、悲伤地欣赏文字之美、辞藻之丽,用心地去和文学作品共振共融的读者。正因为有他们,一代代文学经典才能历久弥新、长盛不衰。
读者的阅读期待虽然有分歧,但他们对作品的要求则不谋而合——作家的描写总要受控于当时的规约,要真实而不拧巴、不造作地写心灵、写人生、写历史。对于经验派,如果他在“市长秘书”“驻京办主任”里得到的官场经验还没有《厂长秘书的日记》或《乔厂长上任记》真实,那他就会宁肯放弃今天的小说转向别处;幻想派也要求“写今天”,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在世界上170多个国家流传了几百年,每个地区的版本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动。当年在日本,小说中的水晶鞋就被改掉了,因为其时的日本是不穿鞋的,若硬让灰姑娘穿上鞋,童话在当地的民间基础就会大打折扣。文学的阅读一派是今天的作家最应该对得起也最需要挽留的读者。他们为《红楼梦》的青春而感叹,为海子的“麦地”而吟唱,他们以自己的心灵去触碰另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世界,他们在文学中读出的是人类内心深处隐秘的声音,静默、聆听、感悟。只是,让他们感念的鲜有当下的创作,他们常常要穿越历史的隧道执手于“百日王朝”时期的马赛或1805年的彼得堡,去接续彼时彼地的地气,而不顾今天的排行榜或畅销书。对此,生活在今天的作家又做何感想呢?
回到批评的原初。
当下的文学批评备受争议,文学批评成了这个时代迷路的孩子,向着交叉小径花园的各个方向探寻却难以找到正途。批评者已经很努力了,但作者、读者都不怎么买账,批评越来越成为批评者无人喝彩的表演——从对古典文论的继承,到对西方文论的借鉴,不可谓不全矣;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理论文章,不可谓不深矣;社科院、文联、高校的专家、教授、研究生,学术人员不可谓不众矣;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项目、奖金等的投入不可谓不丰矣。结果是,我们不断地开研讨会,不断地提出新的艺术命名,不断地给文艺作品评奖,可结果呢?真正的大师在哪里?不朽的经典在哪里?在当下吗?在我们周围吗?我们为什么没有王国维?为什么没有“脂砚斋”?我们在越来越发达的文学批评中反而看不到生命的纹理,听不到诗意的欢畅,触摸不到前行的路标。艺术是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但艺术更应是对生命的理想和诗意的追求,所以更应在繁荣的表面、丰富的痛苦中保持文学批评的审美品位和精神愉悦。也许一个时期(比如某次全国性会议或某个人物、事件的周年庆典)会有几个核心议题,各方观点林立,但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极难有个权威性的、令人信服的、接地气的结论。即便在网络里,众网友热热闹闹地对某一作品、某一话题发表评论,也是各有各的心腹事,各观点像平行线一样无法交汇,更遑论擦出“火花”。
或许文学批评的魅力便在“批评”本身,结论的信度与效度本就是徒劳。宽慰地说,对文学批评的质疑、失望与拥戴同时存在是可以接受的,这至少说明这一领域有关注度和生发点,有发展延伸的可能。但我们却不得不认真思考“批评之批评”的问题。与文学本身的变化相适应,文学批评逐渐彰显自由、提倡创新,出现了言说渠道媒体化、言说方式时尚化等新质,特别是博客、微博、论坛、跟帖、微信公众号等移动通信媒体方式盛行以来,批评也较以往发生了改变。当下的文学批评可以被视为这样几种方式:学院式的文学理论批评、追踪创作的知识性批评、以新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混搭”式随性点评,几种批评方式各有所重又各有所短,尚存有待提升的空间。如果我们无法细致入微地对当下文学批评各病灶逐一化验、分析、报告,只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当前批评的病症:理论批评有失“温度”、知识批评有失“力度”、新媒体点评有失“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