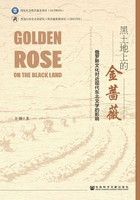
一 俄罗斯文化的东西方性
探讨东北地区接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问题,首先要对俄罗斯文化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它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这是一个以其挑衅性而激起西方其他民族不安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个体,正如人的个体一样,都是该民族的一个微粒,因此也像这个民族一样在自身包含着矛盾,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都包含着矛盾。”[1]俄罗斯民族精神中这种复杂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包含了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源流。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之地处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在这里东西方各民族之间征服兼并的战争连绵不断,曾几何时称霸一方的民族也难免饱受异族的入侵之灾,征战者的金戈铁马往往带来的是民族迁移的浪潮,而民族大迁徙导致各民族汇集交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激烈碰撞和融合,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影响,为这里最终生存下来的文化深深地打上了文明接合部的烙印。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文化还在襁褓中就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叉影响。
俄罗斯文化这种东西方性的特征,首先与其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特定的具体文化来说,自然地理、气候、生物圈等自然因素一方面是外部因素,表现每一种具体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超文化语境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是文化发展有机的语境。它被人意识,被人所适应,显示特有的语义,成为文化的内在结构,被人反映在语言和民间文学中。不同的自然条件相应地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和经济生活的类型,产生不同方式的崇拜(如宗教和习俗、仪式和神话等),产生互相区别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形式和国家制度的形式。总之,最终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2]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俄罗斯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基础。广袤的平原和浩瀚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这一切决定了俄罗斯主要经济活动的类型,决定了耕种的特点和国家组织的类型,形成了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形成了民间文学幻想的形象和民间哲学最初的观点。俄罗斯土地的辽阔无比,俄罗斯平原的无边无际,这些强大的自然因素,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灵中保留下来。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俄罗斯精神的景观与俄罗斯土地是一致的。大自然在俄罗斯人那里是一种比在西方人尤其是在拉丁文化圈的人那里更加强大的自发力量。”[3]
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是在一块巨大的没有任何屏障保护的领土之上。无边无际的平原给了俄罗斯人特别重要的影响。在平原上,一切东西都显得那么柔弱而渺小,轮廓不可捉摸,变动也感觉不到。平原有着辽阔的空间,人烟稀少,四周一片沉寂,观察者能感受到一种心平气和的宁静,一种让人沉迷不醒的梦幻和孤独的荒凉。而巨大国土上漫长的寒冬又让俄罗斯人感受到生活的冷酷。对游牧生活方式的向往与定居文明的自我意识的二重对立是俄罗斯文化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内核,害怕失去自由的忧愁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常常困扰着俄罗斯人,导致了这种二重性的无法解决。四周没有自然屏障,又使俄罗斯民族必须面对来自东方游牧民族的抢掠和来自西方文明的侵略的双重威胁,由此也导致了俄罗斯人不断的征战,不断的扩张。千百年来,东西方各民族之间征服兼并的战争也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其次,原始多神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是俄罗斯文化东西方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用宗教可以把俄罗斯文化大致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多神教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三千年;第二阶段是罗斯受洗后的一千年。在基辅罗斯基督教化之前,古罗斯人信奉东斯拉夫多神教,依靠多神教信仰和神话来积累、传承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丰富和发展民间口头创作。俄罗斯20世纪的国学大师利哈乔夫指出:“多神教在现代的理解中不是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不同。这是各种信仰、崇拜的相当混杂的综合体,而且也不是一种学说。这是各种宗教仪式和一整套宗教崇拜对象的集合体。”“古罗斯人对东斯拉夫多神教的神灵顶礼膜拜,但他们没有神庙,没有特别的祭司阶级,只有一些术士和巫师,这些人被认为是神的服务者和神的意志的解释者。古罗斯的这种多神教模式与我国东北地区的原始萨满教异曲同工,表现出了原始人群对自然神的崇敬。东斯拉夫多神教,特别是多神教神话作为一种丰富的文化遗产对古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4]
公元10世纪罗斯受洗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选择,古罗斯社会上层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弗拉基米尔大公首先进行了对多神教崇拜的改革,虽然改革成果甚微,但从客观上为罗斯受洗做了铺垫。古罗斯选择基督教的原因有许多美丽的传说,从编年史传说中所记载的罗斯拒绝其他宗教而选择基督教的理由来看,这一选择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其理由在今天看来很多是表面化和幼稚的,不过,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和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角度看,问题就复杂得多。一方面,罗斯受洗在客观上建立了基辅国家这一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宗教形式;另一方面,罗斯受洗把罗斯纳入了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文化和世界观范畴。这种选择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间决定了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俄罗斯文化的几个历史范式共有的,不但在文字、宗教仪式、建筑、造型艺术、世界观等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并且还给予俄罗斯文明化进程、社会政治经济进程强大的影响。不过,应该看到,古罗斯社会选择东方基督教作为国教,这一文化历史选择本身不仅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及其代表的上层政治团体操纵的结果,更是东斯拉夫人古代多神教文化本身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取向导致的结果。东斯拉夫人多神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取向迫使罗斯统治者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其他选择,具体的政治形势和当时的政治打算只是加大和限制了这些文化前提条件的作用。古代多神教文化的精神内核存在于古罗斯神话、文化传统、居民的大众心理、经济形式和生活方式等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预先决定了社会实践的目标和指向,预先决定了人民和国家对宗教文化传统的选择。随着基督教化在罗斯社会的深入发展,基督教精神与古代罗斯的传统道德相融合,沉淀在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彻底改变了俄罗斯人的生活,使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古代多神教文化因素仍以隐晦的形式存在于俄罗斯社会之中,美国学者汤普逊曾论述过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现象,认为:“圣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把基督教合法性强加给萨满教行为的做法,而且,这是俄国双重信仰的最完整、最重要的表现。圣愚的独特性不仅源于斯拉夫人异教,而且也源于乌拉尔-阿尔泰萨满教的独特状貌;萨满教在俄国土地上广为流传,直至19世纪,而且至今还保存在西伯利亚乌拉尔-阿尔泰各部落中间。”[5]
再次,鞑靼蒙古的统治给俄罗斯带来了大量的东方文化因素。公元1240年鞑靼蒙古人占领了俄国,建立了金帐汗国,结束了俄国西方化的进程,开始了东方的统治。当欧洲大陆开始其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并发生剧烈的世俗化历史转型的时候,俄罗斯却沦为鞑靼蒙古铁蹄下的牺牲品。在1240年至1480年的两个多世纪中,俄罗斯一直深受东方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影响。在此之后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大规模的西化改革,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才又转向西方,可其步伐却已远远落在欧洲大陆之后。普希金曾说:“毫无疑问,教会分裂把我们与欧洲其他部分分割开来,因此我们没有介入那些震撼欧洲的重大事件中的任何一件,但我们有自己特殊的使命。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她吞没了蒙古入侵者的广袤疆土。鞑靼人未敢跨过我们的西部边界并把我们甩在身后。他们退回到自己的沙漠,基督教文明因而得救。就这一成就而言,我们只得保持一种特殊的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仍然身为基督徒,但却使我们隔绝于基督教世界,这样一来,我们的苦难却为欧洲的蓬勃发展扫清了种种阻碍。”[6]在普希金看来,是俄国人挡住了蒙古人毁灭整个欧洲的步伐,拯救了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但实际上,恰恰是这一事件使得俄罗斯与欧洲的现代文明相隔离。不可否认,鞑靼蒙古的入侵对俄罗斯的欧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根据俄罗斯古籍《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记载:13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蒙古军队进入到了基辅罗斯地区。编年史的作者们称:“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也不清楚他们在何处把自己隐藏;我们犯下了罪行,上帝知道从哪里将他们召来惩罚我们。”[7]我们可以从这段描述中看到当时遭受侵犯的基辅罗斯人的恐惧与无助。
很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俄罗斯学者对鞑靼蒙古的统治是持全面否定态度的,并且认为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东方,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应该看到,文化是随着民族生存空间的发展而变化的。鞑靼统治时期的罗斯文化就不同于10世纪以前的罗斯文化,成为欧亚封建军事帝国的俄罗斯也不同于鞑靼时期的罗斯。我们能够发现,13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民间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音乐文化、民俗文化和建筑文化都与东方的特别是亚洲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8]。可以说,由蒙古帝国所传递来的东方文化从多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对此,冯绍雷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第一,蒙古帝国当时施行的是宗教宽容政策,“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俄罗斯的东正教会正是由于这种宗教宽容政策而得以保存。第二,“在蒙古占领时期,金帐汗国甚至不反对基辅大公与天主教欧洲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当时,金帐汗国还与东欧、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展开外交,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蒙古帝国隔断了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第三,“金帐汗国留给俄国不少重要的制度遗产,其中包括:税收制度、征兵制度、户口制度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间接地通过这些制度在俄罗斯产生了影响。同时,这些制度的实施也为在蒙古占领时期之后俄罗斯中央集权的出现作了一定的体制准备”。第四,“蒙古占领时期的长期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蒙古人与东北罗斯的居民相互融合,人种的融合对于俄罗斯与东方的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俄罗斯文化与习俗中,不光是服饰、建筑等方面留下了蒙古文化的痕迹,而且俄罗斯人的语言中也夹杂了蒙古词汇”。第五,与拜占庭帝国的影响相比,“两百多年蒙古帝国的占领对于俄罗斯更为直接,更有切肤之痛。特别是在蒙古占领晚期,当俄罗斯民族意识复兴之时,蒙古帝国的昔日霸业不可能不成为这个新兴帝国历史记忆中的重要部分”。综上可以看出,鞑靼蒙古的占领对俄罗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只是消极地阻隔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相反,在对于俄罗斯与西方交往并未产生太大实质性阻碍的同时,也为俄罗斯今后的发展取向打上了东方的深刻烙印”[9]。
或许可以说,直到今天,俄罗斯的政治及其文化仍然具有某种边际文化的特色。我们经常发现“俄罗斯文化在两端之间移动的独特现象:要么是普世同情心的迸发,要么是自我独尊式的扩张;要么是肩负救世重任的世界主义者,要么是民族自我利益的坚定卫道士;要么是各不关联的极端之间的综合,要么是其各极之间的戏剧性的分裂,持续着无法妥协的抗争。俄罗斯的这种不确定的政治文化品性为欧洲历史所罕见”[10]。“俄国向何处去?究竟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还是西方式的道路?”这一命题被19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称为俄国的斯芬克斯之谜。这一命题恰恰说明了俄罗斯文化的东西方性,不过,今天来看俄罗斯文化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我们可以说俄罗斯文化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她就是独立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也可以说,正是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源流的文化在俄罗斯精神空间的激烈碰撞,决定了俄罗斯文化独一无二的特殊性。我们在这里探讨俄罗斯文化的东西方性,旨在说明俄罗斯文化与东北文化具有相似的因素,相似性可以显示许多东西,也可以说明许多东西,而且这种相似有利于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当然,俄罗斯文化与东北文化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则为东北文化和文学提供了异质文化的新鲜血液,从而催生出强壮而又美丽的混血文化形态来。
乐黛云曾指出:“一种文化能否为其他文化所接受和利用,决非一厢情愿所能办到的。这首先要看该种文化是否能为对方所理解,是否能对对方做出有益的贡献,引起对方的兴趣,成为对方发展自身文化的资源而被其自觉地吸收。”[11]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并产生长远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它与东北文化有很多内在的契合点,从而引起了对方的兴趣,适应了对方文化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与其传播方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