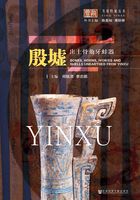
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
李志鹏 何毓灵 江雨德(Roderick B. Campbell)[1]
殷墟出土的制骨作坊遗迹以及与制骨有关遗存的发现表明制骨手工业是晚商手工业产生的重要部门。严格地讲骨器包括利用动物的骨、角、牙制造的各种生活用器、生产工具、武器、乐器、装饰品、雕刻艺术品以及其他杂器等,既包括各种实用器(如针、锥、刻刀、匕、笄、梳、勺、镞、铲等),也包括各类装饰品以及与礼仪活动有关的器物(如珠、环、埙、雕刻艺术品等)。骨器的种类多样,用途广泛,在晚商时期人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礼仪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骨器对于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有着特别的意义。殷墟的考古发掘揭示,晚商时期生产骨器的作坊已经发现数处,与骨器制造有关的骨料等遗物数量惊人,这些都显示了晚商时期制骨手工业的规模巨大,专业化程度很高。研究殷墟的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对于复原骨器手工业的工艺与流程、生产规模以及从制骨工业的角度探讨当时手工业的专业化、经济乃至社会政治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前辈学者对殷墟的骨器与制骨手工业做过一定的探讨,本文拟在其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我们对殷墟制骨作坊遗址和其他遗址出土的骨料等所做的初步研究,对已发表的考古材料进行再检讨,为今后殷墟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进一步研究铺垫基础,并求正于学界。
一 研究回顾
李济先生在《安阳》一书中对制骨业有过简略的介绍。他认为殷商时期制骨产业已进入非常高的发展阶段,并指出历史语言所在安阳的发掘中,发现在不少储藏坑中有一半填的是未加工的骨料,明显是为制骨作坊收集的。他认为安阳出土的骨器可分为两组:(1)占卜用的肩胛骨与龟甲;(2)其他骨制品,如骨箭头、针、锥、削、骨笄、骨柶等。前者是由专人收集,由有一定技术和技能的专门人员整治,这些人可能属于特权阶层;而其他骨制品也需要有经过一定训练的制骨工人制作。《安阳》“殷商的装饰艺术”一章则对骨雕艺术和工艺做了一些介绍。总体上说,李先生对殷墟的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论述较为概略。[2]
陈志达先生对于殷墟制骨工艺与流程、制骨作坊性质与制骨手工业的某些相关问题做过研究。如骨料采用的动物骨骼部位,动物种属及其相对数量比例,骨料的形状分类与适宜制作哪一类骨器,特定制骨作坊的主要产品推测,制骨技术和骨器的制作程序,骨器取料与加工的工具推断,锯痕、锉痕、钻孔、削痕、磨痕分析及相关取料、加工方法的推测,对某些骨器如活帽插杆式骨笄的工艺流程的复原。难能可贵的是,陈先生等还做过骨器锯切、锉磨的实验,以考察不同的锯切工具留下的不同锯痕,这实际是一种初步的实验考古。对于制骨生产的性质,陈先生认为北辛庄与大司空制骨作坊都是以生产骨笄为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卖,可能属于商品性生产。另外他还根据考古发现推测当时除了专业性的作坊外,一些平民可能也自行制造骨器,这种推测是合理的。[3]
杨锡璋先生对殷墟骨器的制造者作过简要的探讨,认为镶嵌绿松石的刻花骨器、象牙器是在王室或贵族控制的工场中制造出来的,而大辛庄与大司空村的制骨作坊的所有者是生产普通骨笄的专业手工业者。此外,他提出,除了专业手工业者外,在殷墟的一些房屋基址和灰坑中,经常发现有成品或半成品的骨器等,其中有些可能是一般平民利用生产的空隙时间从事的家庭手工业产品,有的可能也是交换来的,因此制骨这种与平民日常生活有关的手工业,既有专业的,也有副业性的。[4]
孟宪武、谢世平先生对殷墟制骨场所的分布、规模、作坊的控制者或经营者、手工业生产者的身份、制骨工艺流程与步骤、产品种类以及晚商骨器制造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动因与意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5]鉴于该文涉及的主题较多,将在下文具体问题的讨论中论及。
1935~193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大司空村南做过两次发掘,近年经对高去寻先生遗稿中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其中遗址的第一期小屯期即指殷墟文化时期。李永迪先生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殷墟文化分期成果研究,认为史语所发掘出土制骨有关遗物的灰坑可以依据层位关系进一步认定为殷墟2期或更早,考古所发掘的骨料坑年代分属殷墟2期与3期,与作坊有关的半地穴式房子则为殷墟3期,史语所发掘地点内殷代制骨活动的规模不大,可能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8~1960年发掘的制骨作坊的边缘。[6]
此外,在殷墟历年的发掘简报与报告中,凡涉及骨料与制骨作坊的研究也分别对有关问题作过一些讨论。
总结殷墟出土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这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较为单薄。归其原因,一个方面是因为骨器生产涉及对动物骨骼的认识,古人制作骨器也往往根据动物的骨骼特性发展了制骨工艺,因此缺乏动物考古学知识的专门研究人员参与骨器生产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制骨工艺的深入研究。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往的中国学者缺乏在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视角下进行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具体到制骨手工业很难系统深入探讨涉及手工业生产的各个层面的学术课题。这也是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密切相关。难得的是探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已经努力从各种角度尽可能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有的方面的尝试如运用类似实验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对骨料加工方法的探讨则尤为难能可贵。
鉴于这些问题,我们对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于2006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分析研究,设计了对所有骨料按单位称重、浏览与对抽样单位出土动物骨骼全面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第一次有动物考古学的专门研究人员介入,设计了对骨料鉴定、观察、测量、称重的记录方法与要点,并在分析完一个具体考古单位的样品后进行总结,对记录方法进行适度的调整,有时候还返回原单位进行再观察。在分析抽样单位出土的动物骨骼时,对每一件骨骼进行了编号。鉴定动物具体种属时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不能鉴定到具体的种则不过度鉴定,例如对于可能为黄牛的骨片有的只鉴定到如大型牛科动物或大型哺乳动物的动物分类单元中。在鉴定动物骨骼为哪一类骨骼时,结合骨骼的形状、厚度、大小以及骨骼内壁的形状、纹路、是否有松质骨等具体特征来全面分析,最终把大多数的骨片鉴定到具体的骨骼类别,为深入、准确地分析具体骨骼的取料、加工方式提供了形态学鉴定和定量统计的基础。通过第一阶段的鉴定与初步分析,我们对殷墟时期铁三路制骨作坊反映的选料、取料、预成形、加工等一系列制骨手工业流程和工艺以及制作的骨器种类和主要产品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对制骨工业的规模和相关的手工业生产组织有了一定的了解。[7]
二 骨器与制骨手工业产品的性质
在人类学与考古学对物品的研究中,因物品被赋予的价值、功用以及在古代特定社会的“意义”不同,对物品进行界定与分类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手工业产品自然也是物品,对其界定和分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人类学理论中对物品或手工业产品的分类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将之划分为必需品(Necessities)与威望物品(Prestige Goods)。必需品是指满足基本的家庭需要(主要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能使生命赖以延续、繁衍的需求)的物品,是一个社会内部所有个体都要用到、有着普遍价值的东西,而威望物品只是社会某一或某些群体、集团、阶层能够得到的贵重物品。必需品又被称为主要产品、实用品、日常用品、生计物品等,威望物品也被称为财富物品、贵重物品、奢侈品等。威望物品等一类用语强调的是物品在政治意义上的作用,通常是指如夸富、炫示身份地位等方面竞争性的炫示,而必需品等一类用语则强调的是物品在经济意义上的作用。但是,有时候这种划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某种物品可能既是威望物品又是实用品。必需品与威望物品的划分并不是物品本身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中被赋予的功能性属性或社会文化属性。[8]
骨器一般多数被视为实用器、日用品等,如骨针、锥、刻刀、匕、笄、梳、勺、镞、铲等,属于必需品一类范畴,但骨珠、环、象牙杯等雕花骨器又被看作奢侈品、贵重物品,属于威望物品一类范畴。骨笄既是实用器、必需品,又可能是贵重物品、威望物品,任何阶层都需要使用骨笄,但是贵族使用的精美骨笄又可以是威望物品,如妇好墓中出土的精美的成组雕花骨笄,显示了妇好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因此一件骨器到底是必需品还是威望物品,需要在具体背景中具体分析。
殷墟的制骨活动中,一类制骨活动的产品是大宗日常生活使用的实用器,如骨锥、笄等,一类制骨活动的产品则可能主要是熟练工匠或巧匠制作的雕花骨器等贵重物品。产品的性质与潜在消费者不同,也决定了这两类制骨活动的性质与组织管理方式不同。
三 殷墟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若干相关问题
殷墟的制骨作坊迄今已经发现多处。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孟宪武、谢世平认为存在花园庄、薛家庄村南、北辛庄3处大型制骨场所以及大司空村、小屯村附近的两处小型制骨场所,而且认为花园庄与薛家庄村南两处制骨场所应是王室直接控制,北辛庄制骨作坊的经营权则推测隶属当时某一个部族。[9]但是通过对已发表的材料的检验和我们近两年对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即薛家庄村南制骨作坊)材料的分析,认为孟、谢二位先生的一些认识还需要推敲。下面结合考古材料对制骨作坊的界定、殷墟制骨作坊的确认、分布、年代、规模、性质、组织管理、生产运营链、制骨流程以及发展动力条件等作一些探讨。
1.制骨作坊的定义和确认
马萧林先生认为制骨作坊是指生产骨器的场所,在考古遗址中界定制骨作坊一般应满足三个基本条件:①有比较固定的生产活动空间;②作坊内(即原生堆积)或次生堆积中出土有骨器加工工具;③作坊内或次生堆积中出土有骨器成品、坯料和废料,它们之间具有制作工序上的关联性,即能够清晰地看出骨器加工的整个流程。他指出,在实际的考古发掘中,很少发现原生的作坊遗迹,常见的是次生堆积,而通常情况下,原生作坊很可能就在次生堆积附近,要么还残留基址,要么荡然无存,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往往把一些集中出土相关制骨遗物的次生堆积视为作坊遗迹。[10]
马萧林先生界定制骨作坊的要素我们基本认可,但是应该注意,骨器成品、坯料和废料必须有一定量的发现和规模,否则有可能只是家庭副业的一部分,不足以构成一个作坊。史前遗址的灰坑或地层中有时候能发现构成“操作链”的骨器成品、坯料与废料,也发现有制骨工具,但其骨器制作活动可能只是为了供家庭内部需要。
2.殷墟制骨作坊确认及相关问题
目前殷墟遗址公认的制骨作坊有北辛庄、大司空、薛家村南(或铁三路)制骨作坊,至于花园庄、小屯两个地点是否存在制骨作坊尚有不同看法。下面将逐一梳理殷墟与制骨有关的发现,讨论存在哪些可以确认的制骨作坊及其相关问题。
(1)大司空村制骨作坊
目前学者公认大司空村附近存在一处制骨作坊,虽然对其规模存在不同的认识,如陈志达先生认为该作坊是殷墟范围内目前已知最大的制骨作坊,孟宪武、谢世平二位先生则认为该作坊只是一处小型的制骨作坊。
大司空村制骨作坊位于洹河北岸的大司空村南地与东南地。早在1935~1936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就在村南做过两次发掘,其中第二次发掘面积为1100平方米,发现有骨角器、料以及与铸铜有关的遗物,考古报告直到2008年才出版。[1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1955年在豫北纱厂宿舍西南角(大司空村东南)发掘2米见方的探坑(小探方)2个,其中北部探坑1的晚商文化层中出土大量带有锯痕的骨料和经过加工过的成品和半成品(就器形来看,多系骨笄和笄帽),骨料总计不下千件。[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1950年以后又在大司空村附近陆续做过多次发掘,其中1953~1954年发掘时出土过零星陶范等铸铜遗物,1960年发掘的第四区发掘面积为250平方米,发掘者估计制骨作坊遗址约1380平方米左右,发掘了作为制骨“工房”的半地穴式房子一座,属于殷墟文化3或4期,[13]出土大量骨料、半成品、废品以及角料等与制骨有关遗物的灰坑12个,其中两个坑属于殷墟文化2期,其余均属殷墟文化第3、4期。史语所发掘地点晚商制骨遗存可能属于考古所1960年发掘的制骨作坊的边缘,最早的遗迹可进一步定为殷墟文化2期或更早。[14]可以看出,大司空村制骨作坊的使用年代从殷墟文化2期一直延续到殷墟文化4期,其中殷墟文化早期(1、2期)的制骨遗存发现较少,而以殷墟文化晚期(3、4期)制骨遗存发现最丰富。
大司空村制骨作坊目前发现有半地穴式制骨“工房”,口部东西长1.55米,南北长4.4米,周壁平直,坑壁抹有草拌泥,底部不甚平整,东侧有一条斜坡通道,房内遗留有大量骨料、半成品和一些制骨工具,如铜锯、铜钻等,这些应该都属于原生制骨作坊及制骨时留下的原生堆积。骨料坑大部分分布在房子的南北两端,当属于弃置作坊的制骨活动垃圾的次生堆积。根据大司空村制骨作坊内出土的制骨坯料、废料、半成品可以大致看出当时的制骨基本程序以及某些骨器制作加工的全过程,[15]并且出土有锯切、加工骨料的青铜锯、钻与磨石等制骨工具,而考古所发掘的区域出土骨器半成品、坯料和废料有3万余块。史语所、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社科院考古所各自发掘的与制骨活动有关的区域应当属于同一制骨作坊,从几家单位发掘的区域与制骨活动有关的遗迹分布范围来看,作坊面积可能超过1万平方米。
从上述现象可以看出,大司空村制骨作坊不仅符合界定制骨作坊的所有要件,可确认为一处制骨作坊,而且是晚商时期殷墟一处沿用时间长的大型制骨作坊。在该作坊出土的骨制半成品中以笄杆和笄帽占大部分,其次为锥,镞和匕较少见,与骨料中多数适宜制作笄杆和笄帽相一致,因此该地点很可能是一处生产骨笄为主的制骨作坊。
(2)北辛庄制骨作坊
北辛庄制骨作坊位于洹河南岸,在孝民屯正西约600米,东距小屯村约3公里,遗址在北辛庄村南300米处,属于殷墟西部边缘。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在该处发掘约250平方米,发现属于制骨“工房”的半地穴式房址1座和骨料坑多个,出土大量骨料、骨器半成品以及比较齐全的制骨工具,[16]1973年在该遗址附近又进行了一次发掘,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发现大型骨料坑1个和灰坑5个,出土了大量骨料、半成品、骨器和制骨工具,[17]2003年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联合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钻探、发掘,钻探得知在4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商代骨料层和骨料坑的堆积遗存。[18]这可能是该作坊遗址的大致范围,发掘了可能是制骨作坊管理者居住的夯土建筑2座和多个骨料坑与窖穴,出土丰富的骨料、半成品与铜锯、铜刀、石钻扶手、磨石等制骨工具。[19]就目前考古所发掘材料来看,该遗址的年代属于殷墟文化晚期。
北辛庄制骨作坊的制骨“工房”与大司空村的一样也属于半地穴式建筑,其口部呈长方形,东西长2.8米,南北宽1.95米,南部有台阶,房内地面平坦,通道口东侧有一堆废骨料,可能为骨器制造后废弃物的原生堆积。属于管理者居住的夯土建筑均为东西向,其中保存较好者东西宽5米左右,南北长12米多,东西两排柱础排列有序,东西进深约4.5米。
可以看出,北辛庄制骨作坊也符合界定制骨作坊的要素,而且规模巨大。其面积虽然不一定像钻探资料所说能达到45000平方米,但估计相差不会太悬殊。作坊采用的骨料多数适宜制作骨笄和笄帽,其主要产品应是骨笄,可能附带制作骨锥、骨刀和雕花骨块。
(3)铁三路或薛家庄制骨作坊
1957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薛家庄南地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制骨遗迹一处。[20]2002年、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薛家庄村南的铁三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进行了两次发掘,其中2002年发掘面积约1050平方米,2006年发掘面积约2400平方米,在整个发掘区内均见到有废弃的骨料、半成品与磨石等制骨工具。2008年10月,在芳林花园曾发掘到一处出土大量骨料的骨料坑,这可能是铁三路制骨作坊最西部。结合历年的钻探材料,发掘者何毓灵保守估计该制骨作坊的面积至少有17600平方米。[21]该遗址发现有房址、骨料坑以及制骨工匠及其管理者的墓葬等丰富遗迹,仅2006年铁三路制骨作坊发掘出土的骨骼就重约32吨,其中绝大部分为骨料、半成品等加工过的动物骨骼,生产的主要成品为骨笄,也生产骨锥、骨匕、骨镞以及牙器、角器等。
该处制骨作坊的确认也没有问题,同样是一处规模巨大的制骨作坊,沿用时间从殷墟文化2期到殷墟文化4期。
(4)花园庄与小屯村附近的制骨遗存
孟宪武、谢世平先生认为,在殷墟中心区花园庄存在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制骨场所,并认为是专为宫廷选用占卜用骨(牛肩胛骨)所设立的作坊,由王室直接控制。[22]但是,如果我们对相关发掘资料进行细致分析,会发现其结论还有待商榷。
1986~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村南的花园庄西南角(殷墟宫庙区围沟之内)进行了发掘,发现一个大型“废骨坑”H27。该坑面积约550平方米,出土大量破碎的兽骨,总数近30万块。经周本雄先生鉴定,其中98%以上为牛骨,其余是猪骨、狗骨、鹿角及破碎的人骨等。从骨骼部位来看,多数为破碎的牛头骨、下颌骨、牙齿、脊椎骨、肋骨、盆骨等,少数为肱骨、尺骨、桡骨、股骨、胫骨等长骨的两端及掌骨端部。多数兽骨均无加工痕迹,有锯、切痕迹的兽骨仅80余块,不到兽骨总数的千分之一,多为牛股骨与肱骨骨臼上端,少数为牛髋骨,锯痕断面齐直,似青铜锯所为。根据报告介绍真正称得上骨料的(报告可能指只为兽骨骨干坯料或废料)仅5件,鹿角料少量。据我们观察发表的照片,另有一件圆角垫实际是带柄部与角环的鹿角,只是两端被锯掉,这种情况其实一般是从鹿角上去角料时不用的余料,另一件角镰也可能是残破的角料。H27还出土过陶网坠、纺轮、方套头、刻字陶片、铜镞、石斧、匕、刀、玉斗、骨锥(其中一件实际是牛胫骨脊,一般是取料时不用的余料)、骨笄(一端有穿孔的骨笄杆,出土时笄帽已失落),带钻、凿与灼痕卜甲与卜骨残块。该坑第3层年代属于殷墟文化3期,第1、2层则可能属于殷墟文化4期早段。距该坑约五六百米的小屯南地,1973年曾发现5000多片刻辞甲骨,其中绝大多数是牛骨,还发现一些未经占卜的完整牛肩胛骨。这批甲骨的时代从武丁至帝乙,多数属于康丁、武乙、文丁时期,遗址时代则自殷墟文化1期至4期初,其繁荣阶段属于殷墟文化3期至4期初。[23]报告认为“小屯南地遗址的繁荣阶段与花园庄附近,可能有屠宰牲畜或收取骨料的场所。牲畜被宰杀或食用后,将其骨骼分别处理,如肩胛骨作为占卜的材料,肢骨、肋骨可作为制作骨器的原料,没有用的头骨、下颌骨、牙齿、脊椎骨、盆骨等,作为垃圾成批地扔掉”,这种分析十分精辟,我们完全赞同。报告还认为,“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成立的话,当时这一带可能有制造骨器的作坊,其位置必定离废骨坑不远,也许就在花园庄现在的居民住宅之下”,这种推测很注意把握分寸,只提出附近有制骨作坊的可能。孟宪武等先生则径直认为该地存在一处大型制骨作坊,两种看法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我们认为当时花园庄附近可能存在制造骨器的活动,但是这种制骨活动是否构成大型作坊式的制骨活动,还不能肯定。在小屯村北,曾发现一处为王室磨制玉石器的场所,出土了雕花骨饰与笄帽上镶嵌小片绿松片的骨笄、骨镞以及蚌戈、蚌镢,该地点可能除了制作玉石器外,还为王室成员制作精美骨器、蚌器,因此H27中出土的骨料也有可能是制作这类骨器活动有关的遗存。至于大量的牛骨的肢骨、肋骨、角料也可能被取送至铁三路等大型制骨作坊中作为制骨原料,花园庄附近的宫庙区内是否存在大型制骨作坊目前还不得而知,甚至是否有专门的制骨作坊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发掘材料才能证明,目前谨慎的说法只能说在宫庙区存在制骨活动。至于是否存在制作卜骨原料的场所则另当别论,毕竟这与通常意义的制骨作坊还是有区别的。H27内玉器、铜器等各类遗物都有发现,说明其也可能是宫庙区的王室成员的生活垃圾弃置的场所。其中兽骨的发现及鉴定表明,当时对宫庙区内活动人群食余的兽骨存在明显分选的活动,尤其是与制骨、占卜等活动有关的动物的肩胛骨、肢骨、肋骨等骨骼部位的数量极少,与这两种活动不需要的其他骨骼的大量发现极不成比例,为我们对殷墟制骨作坊的原料来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也就是说殷墟制骨作坊的很大一部分原料来自商王、王室成员(可能也包括在宫庙区的服务人员)的肉食消费或祭祀活动遗留下来的骨骼,当时存在专门到宫庙区选取骨骼做原料的活动。因此殷墟制骨作坊与商代王室的关系十分密切,至少可以确认其中部分制骨作坊是直接由王室供应原料的。
(5)殷墟遗址其他地点发现的零星制骨遗存
在殷墟遗址的不同地点曾发现零星分散的骨料,我们在整理殷墟黑河路与孝民屯遗址的动物骨骼时也发现少量骨料,这些骨料可能是当时一些居民制作供自己使用骨器的活动遗留,其性质可能如杨锡璋先生所说的家庭副业活动的遗留。
3.殷墟制骨作坊的特点与性质
殷墟晚商制骨作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其规模巨大,都属于大型制骨作坊。根据我们对铁三路制骨作坊的抽样分析,在我们抽样区内,平均每平方米区域出土作为骨料的牛骨保守估计约有6~7头牛的骨骼。[24]三个作坊的面积保守估计可能也在6万平方米左右,则可能有三四十万头牛的骨骼被消耗。不考虑制作的其他骨器,这三个制骨作坊光制作的骨笄最保守的估计也有近千万件之多。如此大量的骨笄,远超过王室与贵族的消费需要。此外有学者对1986年以前的殷墟出土骨器进行过粗略统计,约有24000多件,其中主要是骨镞,约有20400件,大部分出于大墓中,骨笄数量次之,约有1590多件,遗址墓葬都有较多的发现。[25]但考古资料又显示,殷墟制骨作坊的主要产品是骨笄。遗址出土的骨笄数量与骨镞数量的比例有如此大的差异,一方面可能因为骨笄的使用时间比骨镞使用时间更长,而骨镞属于一次性消耗的器物,或制作骨笄的技术要求更高,残次品的发现比骨镞要多,而制骨作坊区域一般发现的骨器半成品与成品主要是残次品;另一方面则很可能是因为殷墟制骨作坊生产的产品不仅仅面向都城居民,作坊制作的部分骨笄还要销售到都城以外供其他聚落居民使用。因此,殷墟这几处作坊骨器生产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出卖骨器产品,以商品性生产为主。[26]
从妇好墓等王室与贵族墓葬来看,当时商王室成员及贵族消费的骨笄似乎多数并不是目前所知的三个大型制骨作坊的产品,这些骨笄多数雕镂精美,有的是成组合出现。作坊的骨笄产品也有笄头为鸟形的骨笄与活帽插杆式骨笄,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并不是大中型贵族墓中出土骨笄的主要类型,而多与生活遗迹中出土的骨笄类型相近。王室使用的某些精美骨器,如镶嵌绿松石的骨器,各类雕花骨器,某些类型骨笄如小屯村北M18与妇好墓所出笄头为夔形、锯齿冠鸟头形的骨笄以及王陵中所出蝎子形骨笄等[27],未在各制骨作坊发现接近的半成品或残件,这类骨器可能由一些技艺高超的专门工匠制作,或由类似前文所说小屯村北制玉作坊内的工匠兼制。因此,大型制骨作坊的主要产品如骨笄的消费者不仅不限于王室与贵族,而且很可能主要面向大众。晚商时期无论男女都有束发插笄的习俗,[28]因此骨笄的消费需求量无疑很大。这种以大众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生产,可能是控制骨器生产的王室或某些贵族获取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么这些制骨作坊与商王室是否有直接的关系,还是由其他贵族控制,抑或商王室并不直接控制而由某些贵族代理控制?前文对殷墟宗庙区的大“废骨坑”的讨论表明,殷墟制骨作坊与商代王室的关系密切,至少可以确认其中部分制骨作坊是直接由王室供应原料的。既然王室参与原料的供应,那么,最少可以肯定王室是某些制骨作坊的赞助人。至于其是直接管理制骨生产还是由王室派贵族或官吏代为管理,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总体来说,殷墟制骨作坊可以称为依附性的制骨作坊。中国古代文献中“食于官”的工匠即是这类依附性作坊的工匠,从卜辞材料来看,这种制度可能可以追溯到晚商。在当时为了便于管理工匠,还可能存在一定的组织,如“右工”与“左工”(或左、中、右工)的编制。[29]而同一作坊的制骨工匠以及某些管理者可能主要以宗族的形式集居、共同生产。
4.殷墟制骨作坊的分布特点
制骨作坊是殷墟手工业作坊群的有机组成部分。殷墟制骨作坊与铸铜作坊往往成对出现。这可能与制骨作坊所需青铜工具便于从铸铜作坊就地获得有关,但当时不同类别的手工业作坊聚群,也可能是为了更便于管理。制骨作坊设立在殷墟遗址的东北、东南、西部等不同地点,一方面是制骨手工业大规模发展的结果,原有的作坊空间无法容纳更大的发展,另外也便于从不同地点采集原料,如果产品直接面向市场,也有可能方便面向不同方向的消费市场以及节省销售转运的成本等。
5.殷墟骨器的生产运营链与制骨流程
骨器生产实际上是社会生产、供给交换、消费分配系统中的一个复合体,其生产运营链包括原料采备、骨器生产、废料与废片处理、产品分配或交换与销售等。复原骨器的生产运营链对于重建古代社会的生产消费、手工业经济运转机制等有着重要意义。
原料采备包括对制骨原料的选择、采集、运输、交换、储备。制骨原料来自动物骨骼,其丰富程度、原料特性、可获得性,制约着骨器制造技术、制骨手工业的发展。因为骨器的原料是动物骨骼,一般是人们食用后废弃的动物骨骼,因此原料的丰富程度与人们食用的动物的多寡有关联。一般而言,商王、王室成员与贵族食用的动物较为丰富,普通平民与奴隶食用的动物较少,相比起来,从前者获得制骨所用的原料自然更丰富。因此,原料的丰富程度制约了制骨工业的规模,与社会复杂化、等级化有一定关联。社会等级化程度越高,社会上层对美食的追求以及祭祀礼仪的日趋频繁可能刺激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如晚商养牛业的发展,而牛骨是殷墟制骨的最主要原料。
根据我们对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骨料来源为黄牛、水牛、猪、羊、鹿等动物的骨骼,其中以黄牛的骨骼占绝对多数。骨料既有动物的肢骨也有动物的下颌骨、牙齿,还有角,其中以肢骨占多数,其次为动物的下颌骨和鹿角。动物的肢骨骨料以家养动物的肢骨为主,少见野生动物肢骨,具体到种属来说以普通黄牛的肢骨为主,另有少量的圣水牛、绵羊、猪、鹿的肢骨,偶见马的肢骨。黄牛的肢骨骨料来源包括除指/趾骨外的所有长骨,而以掌跖骨为多。用来制作骨器的骨骼基本上是完整骨骼,因为发现的制骨的余料基本都是骨骼的关节部位和带锯口骨干残片,未见有普通消费肉食时截断骨骼的断口方式。但骨骼上也常见割痕等屠宰痕迹,说明当时选取的为剔取肉后的完整骨骼。[30]据北辛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骨料报告称,可以辨识的有牛、马、猪、羊、狗等骨骼,而以牛、猪居多(据我们对铁三路制骨作坊的骨料分析,及其他制骨作坊遗址已发表图片的动物骨骼来看,猪骨极少,因此北辛庄的骨料中是否有较多的猪还是一个疑问),还有少量的鹿角和鹿骨。[31]大司空制骨作坊能辨认出的有牛、猪、狗、羊、鹿等动物的骨骼,也是以牛居多,角料则多采用鹿角,主要是动物肢骨,少量的利用肋骨和盆骨。[32]制骨作坊出土骨料的动物种属构成和骨骼种类、部位组成都与以往经过动物考古学分析的殷墟白家坟东地、孝民屯、机场南路(郭家湾新村)等地点日常消费的动物骨骼组合存在较大的差异,其骨料来源应该不仅限于制骨工匠日常消费的动物,可能还从来自王室、贵族或其他群体日常消费、宴享中食用的动物的骨骼中挑选获得,并且在此之前割取肉块时有意保存骨骼的完整。商王、贵族的宴会(包括与祭祀礼仪有关的宴会)能一次就遗留下较多的牛骨,宴会的频繁程度也会影响制骨原料的丰富程度。前文提到的花园庄的大型废骨坑,就与这种制骨原料的采选有关,而且不能排除与王室的某些宴会有关系的可能。

图1 殷墟制骨作坊股骨、桡尺骨与掌骨取料模式图解[33]
骨器生产包括坯料预制、粗坯成形、成品完工或半成品细部加工等骨器制造活动以及生产的管理组织。
坯料预制,即一般所说的取材、取料,包括分割骨骼、截取坯料(或称毛坯)等。一般首先将动物骨骼的两端关节部分截掉取骨干部分,因为动物骨骼的关节形状不规则而且主要是松质骨,不适宜制作骨器;其次根据要制作的骨器的特点,针对不同骨骼部分的形态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截取坯料。截取粗坯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因形取料、省工原则”。截取骨料时为了效率起见,一般在将骨骼锯至一定深度后,在相对的另一侧重新锯切,锯开大部分后,骨骼用工具或手折断;根据不同骨骼的具体形状和其他骨骼特征一般有相对固定的锯切方向,如掌骨因为后侧的骨壁呈长方形的规整骨片,前侧骨壁呈半圆形,故多从后侧下锯使后侧骨壁保存更好,能获得制作骨笄的理想坯料。锯取骨干后再根据不同的骨骼的形状、尺寸、骨质密度在不同部位下锯,截掉骨骼的不规则部位,获得制作预制骨器所需要的理想坯料。与取材活动有关联的骨骼遗物包括坯料(多为出现意外破损、开裂的坯料)、边角料、余料,从保留和“遗失”的骨干残片所在部位我们可以复原各种骨骼的取料方式和预想获取的制骨坯料是什么。从观察分析的结果来看,殷墟不同时期不同骨骼的取料方式总体上较为固定,每种骨骼都有相对一致的几种模式化的取料方法,但也有所变化(图1)。制骨作坊的产品还包括牙器和角器。从铁三路制骨作坊来看,牙器的原料来自公猪的下颌犬齿。在遗址曾发现有锯痕和加工痕迹的猪下颌骨,犬齿都被抽取。为了抽取公猪犬齿,一般将猪下颌联合部锯开,并将犬齿后延尽头之后的部位砍断。我们还发现有加工过的犬齿残片,结合以往殷墟遗址发现的公猪犬齿加工成的牙器,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类特征的猪下颌骨骨料就是为了获取公猪犬齿来制作牙器。取下公猪犬齿后根据所要制作的牙质制品的形状截取合适大小的坯料。角料主要为麋鹿、梅花鹿等大中型鹿的角,一般为锯取坯料后的余料,以及少量作为坯料的角片。截取角料时一般截取主枝和分支的角干部分,分叉部分和角环一般废弃不用。[34]晚商时期截取坯料的工具已经主要采用青铜锯,少量用石刀锯切。前辈学者曾用北辛庄制骨作坊出土的青铜锯和石刀锯出土的骨料,结果证明多数锯痕是铜锯的遗痕,仅少数锯痕为石刀的遗痕。[35]根据我们对铁三路遗址出土的骨料锯切痕迹的观察,也基本为铜锯的遗痕。殷墟时期制骨工业的发展,与青铜工具的普遍采用有很大关系。
坯料成形:骨器坯料截取后,根据所需制作的骨器特点对坯料进行加工,一般需要经过锯切、刮削、刻凿、掏挖、锉磨等方法,需要钻孔的则进行钻孔,使毛坯经过减序加工(Reduction)的方法成为器物的雏形。这个阶段的最终产品保存下来的遗物即为通常所说的半成品。不同器物的具体成形方法是不同的。从骨笄的加工方法来看,殷墟制骨作坊中有的器物的生产已经呈现出标准化生产的特点。
成品完工(或半成品细部加工):一般指坯料被加工为器物雏形后,对器物进行打磨抛光等细部加工,如果是组合型骨器,如活帽插杆式骨笄,还需要将各个元件黏合或粘嵌在一起。这个阶段最终产品就是成品,还处在该阶段中的骨器即半成品。
废料与废片处理:一般指对骨器制造过程中的制骨废料、余料、边角碎料、残破坯料、残次半成品与成品等工业垃圾找地方进行堆埋、焚烧等处理。一般俗称的骨料坑就是制骨废料与废片的弃置场所。另外,在有的作坊出土的骨料中还发现了大量被焚烧的炭化或半炭化制骨废料,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中这种被焚烧过的骨料即占了一定数量,这也是当时制骨工业规模的一个体现,因为制骨的垃圾量太大,以至于需要焚烧处理。
至于制骨生产的组织管理包括对制骨活动的组织、各种工序阶段产品的督检、工人的协调管理等。广义地讲,制骨生产的组织管理应该贯穿在整个手工业生产运营链的全过程。
产品的分配或交换以及销售都是同一类型活动的不同实现方式。骨器产品制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不管是为了供自己消费还是为了交换。而殷墟大型制骨作坊的主要产品很可能是通过市场销售出去,而晚商时期铸铜手工业的产品则可能主要以一种王室控制的分配方式流通,这实际显示了晚商时期手工业经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6.殷墟制骨工业发展的条件动力
(1)青铜工具的利用。青铜锯、钻等金属工具在殷墟制骨工业中的广泛应用给骨器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带来了技术性变革,不但极大地提高了骨器制作的生产效率,而且为骨器形制的规范化、精细化提供了技术条件。[36]铸铜工业的发展则是青铜工具广泛应用的基础。
(2)畜牧业的发展。晚商时期畜牧业较之以前时代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养牛业的发展,牛骨在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组合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猪骨。晚商都城无论是王室贵族的祭祀、宴享与日常消费还是普通平民的日常肉食消费都消耗了大量的牛,而牛骨的尺寸大、硬度高,是制骨的理想材料,因此成为殷墟制骨作坊的主要原料。晚商养牛业的发展以及都城居民大量消费牛而留下了大量的牛骨,为制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
(3)晚商时期开始注重发展面向普通市场的商业生产以获得王室或贵族所需的财富,可能是制骨手工业发展最根本的内在动力。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编辑的《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
[1] 李志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江雨德(Roderick B. Campbell),纽约大学,教授。
[2] 李济著、李光谟译《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英文原版)。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5] 孟宪武、谢世平:《殷商制骨》,《殷都学刊》2006年第3期。
[6] 高去寻遗稿,杜正胜、李永迪整理《大司空村(河南安阳殷代、东周墓地及遗址)》,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
[7] 李志鹏、江雨德、何毓灵、袁靖:《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制骨遗存的分析与初步认识》,《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7版。
[8] Rowan K. Flad & Zachary X. Hruby,“Specialized” Production in Archaeological Contexts:Rethinking Specialization,the Social Value of Products,and the Practice of Production,In Rethinking “Specialized” Production:Archaeological Analyses of the Social Meaning of Manufacture,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No. 17,ed. Zachary X. Hruby and Rowan K. Flad,pp. 1~19.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9] 孟宪武、谢世平:《殷商制骨》,《殷都学刊》2006年第3期。
[10] 马萧林:《关于中国骨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
[11] 高去寻遗稿,杜正胜、李永迪整理《大司空村(河南安阳殷代、东周墓地及遗址)》,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
[1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13] 在《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中将殷墟遗址分为三期,其中第3期相当于大司空村3、4期(见注[2]),李永迪将大司空村报告中最初定为遗址第3期遗迹的年代都定为殷墟文化3期(见注[5]),陈志达先生则定为殷墟文化第3或4期,应以后者为是。对殷墟文化分期的看法的变化与各家不同,参见郑振香先生《殷墟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一文(见注[2]《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14] 高去寻遗稿,杜正胜、李永迪整理《大司空村(河南安阳殷代、东周墓地及遗址)》,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18] 李阳:《殷墟北辛庄商代遗存》,《安阳历史文物考古论集》,大象出版社,2005。
[19] 孟宪武、谢世平:《殷商制骨》,《殷都学刊》2006年第3期。
[20]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薛家庄殷代遗址、墓葬和唐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8期。
[21] 李志鹏、江雨德、何毓灵、袁靖:《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制骨遗存的分析与初步认识》,《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7版;Roderick B. Campbell,Zhipeng Li,Yuling He and Jing Yuan,Consumption,Exchange and Production at the Great Settlement Shang:Bone-working at Tiesanlu,Anyang Antiguity,Volume85(330),2011,1279-1297.
[22] 孟宪武、谢世平:《殷商制骨》,《殷都学刊》2006年第3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
[24] 李志鹏、江雨德、何毓灵、袁靖:《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制骨遗存的分析与初步认识》,《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7版。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语言所,2008。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29] 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
[30] 李志鹏、江雨德、何毓灵、袁靖:《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制骨遗存的分析与初步认识》,《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7版。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33] 图中完整骨骼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动物考古实验室现存牛骨标本,骨料则系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
[34] 李志鹏、江雨德、何毓灵、袁靖:《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制骨遗存的分析与初步认识》,《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7版。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36] 马萧林:《关于中国骨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