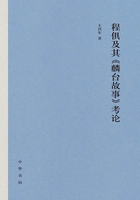
前言
宋代程俱撰《麟台故事》五卷,是一部全面记载北宋馆阁典藏文物及典章制度的史料笔记类专著。该书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追述北宋秘书省与馆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制度的历史沿革、机构建废、舍址变迁,及其官员的设置、职掌、选任、升迁、恩荣、禄廪等的日常情况;二是追述有关北宋政府对馆阁所藏典籍的征集、储藏、整理(如政府组织校雠、辑刊经籍等)、修纂(如重修前代史书、撰集前贤文籍和新修当朝国史等)、利用之类的基本工作。鉴于该书具备专史的特性,且所载内容绝大多数都源于北宋旧本《实录》、《会要》、《国史》等后世已失传的文献,而且还有极个别部分是作者任职馆阁期间的见闻,故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向为研究北宋馆阁藏书、文士、制度以及古代图书馆史、校雠学史、目录学史,制度史方面的学人所重。也正是因为该书对研究北宋馆阁藏书与制度以及我国古代藏书文化事业有着不同寻常的文献价值,所以才决定了其在宋代诸多文献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然而,《麟台故事》及其所记载的北宋馆阁藏书制度虽对于宋代文化史研究有着十分重大的价值,但到目前为止,针对该书所深入展开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且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文献本身的整理方面。从时间而言,学界先后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以下两个相对较为突出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清代至民国,这一时期所针对的主要问题是《麟台故事》的辑佚、整理以及版本、内容、体例、价值等方面的探讨。
《麟台故事》自南宋绍兴元年(1131)成书之后,便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起初是在一些公私书目中均有著录、介绍以及对其内容的评价。后来由于该书刊刻、流传中的诸多历史因素,又出现了对该书本身的研究成果,包括辑佚、整理以及版本、内容、体例、价值等方面的探讨,且集中出现于清乾隆至民国初年。
首先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麟台故事》的许多散见内容,又参照了同见于《说郛》的六条内容,再依据同为《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陈骙《南宋馆阁录》的篇名,顺次排出《麟台故事》五卷本,即《永乐大典》本,或四库辑本(本书以下简称之为“辑本”)。辑本初收入《四库全书》时为写本,后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时为活字本,亦称殿本。于是此后流传于世的清四库辑本,一般有写本和活字本两种版本,其中殿本的流布范围较广,且据此又产生了一些如浙江本、江西本等的地方书局刊本,共同构成了《麟台故事》五卷的辑本系统。从学术研究的价值而言,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在辑本形成的过程中,四库馆臣广征博引如《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容斋随笔》、《玉海》、《东都事略》、《南宋馆阁录》、《北山小集》、《玉壶清话》等诸多文献记载,几乎对每一条材料都反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订,并在卷首加四库馆臣所作《提要》,卷后附源于程俱《北山小集》中的《麟台故事后序》一篇。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清四库辑本是《麟台故事》散佚之后的又一次成书,也不得不肯定清四库辑本五卷九篇所编排的八十余条材料和夹在材料中的八十余条颇具考证价值的馆臣按语,均成为令后世学人倍加赞赏的研究成果。尽管我们认为:清代四库馆臣对所辑出的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麟台故事》的材料,先作分类归属,然后定篇目而编缀成卷的做法不尽合理,也确实存在着主观臆断、凭空编排的成分,甚至所加按语也有考证不够严谨而出现一些失误的地方。但是,从整体而言,四库馆臣的这一编纂成就却不容忽视。及至今日,学界已形成的所有对《麟台故事》进行辑佚、校证等整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深受其影响。尤其学界凡论述北宋馆阁藏书及其制度的相关问题时,所征引材料也往往以此本为据。
然后是在清嘉庆年间,书商手头又出现了残存不足三卷的、明代苏州府前杜氏书铺收藏过的、据《麟台故事》宋刻本影写的残本(学界有称之为“影宋本”、“影宋抄本”、“明影宋抄本”、“影宋刊本”、“影写宋刊本”、“明影宋刊本”之类者,均属此本,本书以下简称之为“残本”或“影宋残本”),黄丕烈经眼,遂定其为善本,后又为之作《跋》。于是,自黄跋起的一段时期内,学界对《麟台故事》一书关注者较多,继黄氏之后,既有李光廷、孙星华、钱大昕、胡玉缙等人,分别再为其作跋语,又有张元济将残本与辑本相参校,作跋语,出校记,并考其篇目、卷帙、条次、记载之异同。同时,基于多方面的缘故,清人陈墫、惠栋、王士祯、于昌进、戴植、陆心源等著名书画收藏家也纷纷传录并收藏该书,经由此途流传至今的该书清抄本更不在少数。及至近人傅增湘又作题记,逐一记述其前后得见“此书归蒋孟 (己未)”、“李木斋遗书(辛巳)”、“古书流通处送阅(壬戌)”
(己未)”、“李木斋遗书(辛巳)”、“古书流通处送阅(壬戌)” 三个本子的基本概况。
三个本子的基本概况。
以今观之,这些围绕着残本和辑本异同所形成的诸多跋语和题记,则又构成了现今对《麟台故事》进行深入研究的另一种珍贵材料。诸如此类因残本出现所引起的一系列《麟台故事》的问题,则足以说明:残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原本的旧貌,且与四库辑本的篇目和内容均存在很大的差异。于是,之后的学术成就,又主要体现在残本与辑本相结合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尤其是学术界围绕着辑本与残本的异同,所展开的研究与整理工作的成果较为显著,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编纂方式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新本子:
一是为存《麟台故事》宋本旧貌,清陆心源便以辑本补残本的方式重新纂辑,因此形成了既有别于辑本,又不同于残本的《麟台故事》四卷后又附《补遗》一卷的新本子,亦可称之为《麟台故事》明影宋刊残本的补遗本。后来收入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三集》,现所见台湾新文丰公司影印的《丛书集成新编》本即据此本。很显然,陆氏重辑本的出现,体现了整理文献一贯坚持的求真至善的原则。
二是欲求《麟台故事》辑本全貌,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时,又由孙星华以残本补缀辑本的方式再次纂辑,形成了另一种有别于陆氏补遗本乃至以往辑本、残本的新本子,为以四库辑本为主重新编纂的拾遗本,即《麟台故事》五卷加上《拾遗》二卷和《考异》一卷,亦可称之为《麟台故事》殿本(即等同于清四库辑本)。后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刊刻时,所据之本即为孙氏拾遗本。此本一经刊刻,即在社会上流布较广。今国家图书馆、西北师大图书馆等均藏有此本。很显然,孙氏拾遗本的出现,体现了整理文本旨在求全至善的目的。
总之,清代陆氏补遗本和孙氏拾遗本作为重辑本出现,已表明:二者保存材料的全面性,均非清四库辑本(或殿本)和明影宋残本所能比及。只是因陆氏坚持了整理文献的求真至善原则,故其补遗本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在学界的评价也很高。
然后是民国初期至今。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一阶段的出版成果集中体现了四部文献整理方面的创获。
首先,第一阶段从民国初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为冷寂,除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民国初年任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时,曾对所见的三个“《麟台故事》五卷” 的残本分别做过较为详实的著录之外,学术界对该书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情况可言。
的残本分别做过较为详实的著录之外,学术界对该书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情况可言。
然后是一个较为活跃而成绩显著的阶段。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的三十余年,学术界对该书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既有当今学者以《麟台故事》为研究对象所公开刊发的一些颇具学术研究价值的论著,也有该书先后被不同的学者整理出版的四项较为重要的学术成就。具体情况即如下述两个方面:
其一,先后有四篇较为重要的单篇论著,集中论述《麟台故事》的作者、篇目、著述特点、史料价值等的概况,对我们现阶段全面而系统地展开《麟台故事》及其著者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从论著方面来看,最初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宋立民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上发表《<麟台故事>版本考》一文,对《麟台故事》内容及条次、刊刻及流传、版本及种类、辑佚及补遗等诸问题予以探讨,其中虽多有真知灼见,但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还是缺乏必要的深细度,例如认为该书“分为沿革、省舍、官联、选任、书籍、储藏、校雠、修纂、国史、恩荣、职掌、禄廪十二篇”的看法,即是如此,因为该问题截至目前,仍处在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而无法界定的状态,所以完全不能如此简单而轻率做出这样的结论:四库辑本的九个篇目加上明影宋残本的六个篇目后减去重见的三个篇目,剩下即为其所谓的十二个篇目。深究之下,就会发现这一做法及其结论,既不符合文献整理的常规,又缺乏科学而严谨的态度。实属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
紧接着宋先生又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上发表《试评<麟台故事>》一文,从《麟台故事》产生的客观原因、如何选取史料进行著述的特点、所发挥出的实际作用和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四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即称:“《麟台故事》为宋程俱所撰,共五卷,分十二篇,是今天仅存的记载北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简称三馆)、秘阁以及秘书省的文物典章制度的一部专著。《麟台故事》一书对于研究北宋时期的馆阁制度以及我国图书馆史、校雠学史、目录学史等,都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对《麟台故事》著述的特点,具体概括为五点:一是“较全面地记述了北宋时期的馆阁制度”;二是“从其史料来源看,所记史实的可靠性较高”,认为“由于史料来源于文书档案或官修史书,以及程俱本人的亲身见闻,所以史料的可靠性较高,具有一定的价值”;三是“从著述的方式上看,主要有两种方法”,认为“凡为亲身经历及道听途说之事,程俱皆亲自下笔撰述。凡为国史、会要等官书及文书档案所记,则往往照录原文,时而于引文之后加以简短的评语”;四是“在史料的取舍上,程俱所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巩固南宋朝廷的封建统治”;五是“程俱也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融合到《麟台故事》一书中去”。应该说,这是一篇较为全面评述《麟台故事》一书的文章,尤其是所提出的诸多观点,确实有助于深化此后学术界围绕该书展开的深入研究。不过,其所明显存在的问题又在于:仅以一些评论性的言辞或论断,确实很难形成有一定深度的、更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在此尤其值得赞赏的,乃是宋先生在评述之余,也热切期盼该书“在我们今天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应该对此书作进一步的整理,以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
。
第二年,姚伯岳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刊发《<麟台故事>整理前言》一文,主要对《麟台故事》一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史料价值、体例及其内容、流传及其版本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唐、宋是秘书省制度的巅峰时期,相应地也产生了记录其活动的情况的专书。南宋初年程俱所编撰的《麟台故事》就是现在唯一的一部记述北宋王朝秘书省、三馆、秘阁建制、活动及其沿革发展的专著。它载录史料的丰富严谨和体例的完善赅备,以及所蕴含思想的深远独到,使它的价值日益为今日的图书馆学界所重视,从而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的一部弥足珍贵的文献。这就是我校点整理这部书的缘由” 。再至一九九三年,张富祥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程俱<麟台故事>考略》一文,一方面以我国古代的文馆制度伴随着政府图书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为视角,另一方面以有关北宋文馆制度的诸书对《麟台故事》地位和影响的载录为线索,将程俱所撰专门记述馆阁制度的《麟台故事》一书,准确归位于北宋馆阁制度沿革的大背景下,展开探讨的主要内容分为“作者和编撰”、“版本和流传”、“内容、体例和史料来源”、“现存史料的分析”
。再至一九九三年,张富祥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程俱<麟台故事>考略》一文,一方面以我国古代的文馆制度伴随着政府图书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为视角,另一方面以有关北宋文馆制度的诸书对《麟台故事》地位和影响的载录为线索,将程俱所撰专门记述馆阁制度的《麟台故事》一书,准确归位于北宋馆阁制度沿革的大背景下,展开探讨的主要内容分为“作者和编撰”、“版本和流传”、“内容、体例和史料来源”、“现存史料的分析” 四个方面。以今观之,在姚、张二位先生的论著中,相关的认识和论断,不乏真知灼见,确实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然,这也应当与姚先生着手点校《麟台故事》、张先生倾力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和残本有关,事实上也是完成一项古籍整理任务时必须做好的首要工作。这两篇文章经进一步完善,修订为姚先生后来点校出版《宋麟台故事》之卷首的导读和张先生校证出版《麟台故事》之卷首的前言。可见,这两种研究成果的形成,均有着比较接近,甚至是完全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各自整理《麟台故事》一书而所做的前期准备,并不是针对该书内容及其著者所做的专门研究。不过,二作学术价值固然重要,但只是有关深入研究工作的良好开端,实则很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和拓展。
四个方面。以今观之,在姚、张二位先生的论著中,相关的认识和论断,不乏真知灼见,确实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然,这也应当与姚先生着手点校《麟台故事》、张先生倾力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和残本有关,事实上也是完成一项古籍整理任务时必须做好的首要工作。这两篇文章经进一步完善,修订为姚先生后来点校出版《宋麟台故事》之卷首的导读和张先生校证出版《麟台故事》之卷首的前言。可见,这两种研究成果的形成,均有着比较接近,甚至是完全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各自整理《麟台故事》一书而所做的前期准备,并不是针对该书内容及其著者所做的专门研究。不过,二作学术价值固然重要,但只是有关深入研究工作的良好开端,实则很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和拓展。
其二,是从一九九〇年至今,先后有四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出版,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我们系统而全面地展开《麟台故事》及其著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一部是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三集》本的姚伯岳校点本。
一九九〇年七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徐雁、王燕均主编《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一书,收入了姚伯岳的校点本——《宋麟台故事》,本次标点的底本便是陆心源残本补缀辑本的本子。而且姚伯岳在《宋麟台故事·导读》中称:“陆氏此本即其《十万卷楼丛书》本。此本编排得法,校勘也比较精审,是《麟台故事》现存版本中最好的一个本子。”不过,各篇之下所加附录,并非此次校勘和校订方面的内容,而是较多地承继了四库辑本中所存四库馆臣所加的按语,正如其所云:“当初四库馆臣辑录《永乐大典》本时,亦曾做过一番考据工作,附于原文各条之下,不为无益。现皆附录各篇之末,以资参证。” 本著作为读本,重在于做好点校文字方面的工作,出于体例所限,对文献所载材料进行必要的、更为深细的考证,往往被忽略,以至于该著会因袭清代馆臣旧误,并未予以更正。再以残本补辑本的广雅书局覆刻本与陆氏辑本相比而言,则因各方面的缘故,至今还未出现过校点,或者校证方面的整理成果。
本著作为读本,重在于做好点校文字方面的工作,出于体例所限,对文献所载材料进行必要的、更为深细的考证,往往被忽略,以至于该著会因袭清代馆臣旧误,并未予以更正。再以残本补辑本的广雅书局覆刻本与陆氏辑本相比而言,则因各方面的缘故,至今还未出现过校点,或者校证方面的整理成果。
第二部是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三集》本的中华书局标点本。
即一九九一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麟台故事(及其他一种)》,其所依据的底本是《丛书集成初编》本,且据其卷首有“《丛书集成初编》所选《聚珍版丛书》、《十万卷楼丛书》皆收有此书,《十万卷楼》本虽后出,然经陆心源校订,故据以排印” 一语,可知《丛书集成初编》所据底本则为陆氏《十万卷楼丛书》本。此次整理,仅有句读,并无校勘,故不见有关校订或校证方面的文字内容。
一语,可知《丛书集成初编》所据底本则为陆氏《十万卷楼丛书》本。此次整理,仅有句读,并无校勘,故不见有关校订或校证方面的文字内容。
第三部是张富祥对《麟台故事》四库辑本和影宋残本二者分别校证,最后汇为一书,形成二者既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为一体的整理成果。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以先辑本后残本排序方式,对辑本和残本的材料逐条进行分别校证,虽然二者前后之间有各本相同材料的彼此照应和相异材料的比照,但二本属于独立的单元,相互之间并不统属,最终,校正后的辑本与残本又被合为一书刊出。依据张先生所作的卷首前言可知:校正后的辑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为底本,残本以《四部丛刊续编》所收录的影宋抄本为底本,“并为简便和明确起见,分别定名为《麟台故事》辑本和《麟台故事》残本” 。即在《麟台故事校证》一书中的《麟台故事》辑本和残本的校证成果表现为各自独立而并存的两个版本。
。即在《麟台故事校证》一书中的《麟台故事》辑本和残本的校证成果表现为各自独立而并存的两个版本。
第四部是黄宝华对《麟台故事》四库辑本和影宋残本分别整理,形成二者独立而并存的整理成果。
二〇〇六年一月,由郑州大象出版社出版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戴建国主编《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九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收入黄宝华整理本,校点时黄先生在《校点说明》中称:“辑本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为底本,残本以《四部丛刊续编》本为底本,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玉海》、《皇宋事实类苑》、《南宋馆阁录》及《续录》诸书参校,二本并收,以存其旧。” 即收入《全宋笔记》第二编中的《麟台故事》辑本和残本的整理成果,也同样表现为各自独立而并存的两个版本。
即收入《全宋笔记》第二编中的《麟台故事》辑本和残本的整理成果,也同样表现为各自独立而并存的两个版本。
此外,还有一些将程俱及其撰述相结合,加以研究的成果,较早期的如叶渭清的《程北山先生年谱》四卷(附录二卷) ,近年来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单篇论著,如李欣、王兆鹏所著《程俱年谱》等。总之,至今有关《麟台故事》的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对文献本身校点、校证等方面,对其著者、成书、流传、版本、体例、内容、价值等基本情况的全面的清理,便显得十分薄弱。尤其长久以来,对著者的考察,也只是作为整理文献前的一部分必备工作,仅在前言中予以简单的概述而已,尚没有将程俱与其著述相结合的、相对完整而系统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单篇论著,如李欣、王兆鹏所著《程俱年谱》等。总之,至今有关《麟台故事》的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对文献本身校点、校证等方面,对其著者、成书、流传、版本、体例、内容、价值等基本情况的全面的清理,便显得十分薄弱。尤其长久以来,对著者的考察,也只是作为整理文献前的一部分必备工作,仅在前言中予以简单的概述而已,尚没有将程俱与其著述相结合的、相对完整而系统的研究成果。
面对以上情况,我们该如何做,做出什么结果才能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据宋人程俱为其好友贺铸所作《贺方回诗集序》云:“方回落落有才具,观其书可以知其人。” 此说之精要在于:以文知人识人。其所坚持的评价原则,是一种文如其人的一致性;其所依据的准则,是著述者个人的人格、修养、学识、思想、情趣等与其文学创作及其学术研究的高度统一;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最终要达到文以载道、道以弘仁的至高境界。可见,这是既关注由文到人、再提升到道与仁的准则,又反观其文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术批评方式。其所重者等同于现今所谓的风格,主要有“创作个性是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风格存在的基本条件”和“语言组织和文体特色是风格呈现的外部特征”
此说之精要在于:以文知人识人。其所坚持的评价原则,是一种文如其人的一致性;其所依据的准则,是著述者个人的人格、修养、学识、思想、情趣等与其文学创作及其学术研究的高度统一;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最终要达到文以载道、道以弘仁的至高境界。可见,这是既关注由文到人、再提升到道与仁的准则,又反观其文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术批评方式。其所重者等同于现今所谓的风格,主要有“创作个性是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风格存在的基本条件”和“语言组织和文体特色是风格呈现的外部特征” 三个方面的特点。于是,程俱此说,往往被今人认为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风格即人”之说暗合
三个方面的特点。于是,程俱此说,往往被今人认为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风格即人”之说暗合 。应当肯定,这种由文而关涉到人的整体性研究思维,不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也更加合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
。应当肯定,这种由文而关涉到人的整体性研究思维,不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也更加合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
反之亦然,我们在此下所进行的研究,似乎颇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即采用的是知其人而论其文,进而论其世的做法。正如《孟子·万章下》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知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之语,对后世最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的基础阶段,即欲知其诗书,必先知其人,若其人诚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则其书所关乎者,终究不离于正道;第二层面是认识升华阶段,即欲知其世,必先观其文,而这也正是我们长久以来秉持的传统治学途径,亦即:“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
,则其书所关乎者,终究不离于正道;第二层面是认识升华阶段,即欲知其世,必先观其文,而这也正是我们长久以来秉持的传统治学途径,亦即:“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 于是,“知人论世”既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成为中国学人治学的优良传统
于是,“知人论世”既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成为中国学人治学的优良传统 。其所具理论依据在于:人的生存虽然离不开自然界,但是社会环境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亦即某一社会的人,必定是其所生活的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的结果,包括其诗文在内,与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都是由人的存在及其时代所具有的社会性决定的。这是因为: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决定了人的存在,人的存在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规定,而是人的活动过程本身及其成果即社会。
。其所具理论依据在于:人的生存虽然离不开自然界,但是社会环境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亦即某一社会的人,必定是其所生活的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的结果,包括其诗文在内,与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都是由人的存在及其时代所具有的社会性决定的。这是因为: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决定了人的存在,人的存在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规定,而是人的活动过程本身及其成果即社会。
据此知人论世而以意逆志的思路,我们在系统地研究程俱及其所撰《麟台故事》时,首先要从著者入手,必须结合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对其生平经历、思想认识等基本问题,进行一番较为全面而又细致深入的考察,形成一种较为准确而又清晰的客观认识;然后才能够做到更为精确地把握和理解其著述的基本内容,进而才能够更为客观而公正地评论其著述的宏旨大义,断定其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最终在探究天人之际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中,顺理成章地形成一项内外结合的整体性研究结果,以企其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发展有所裨益。
正是这一传统的治学途径和方法,既形成了我们对作者与著述相结合进行整体研究的认识和思路,也最终决定了本书撰写及其结构以总分总式安排。具体呈现为以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关程俱的考论。本部分先对程俱生平事迹进行较全面而细致的考述,形成概貌性基本认识,然后考辨不同文献中有关程俱的一些记载,主要有不同文献对程俱称谓异同之缘故的分析、程俱本传与行状的关系及其信实性的探讨,以及对《新安文献志》、《麟台故事》四库提要等所载程俱“举进士”属于误载的考证。基于以上考述,最后又对程俱行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重点评述。这一部分的关键在于,考证出有关文献中一些误载的情况,如《新安文献志》、《四库全书》等,对程俱科举入仕之事的误载;又如《直斋书录解题》、《新安文献志》、《北山小集》等,载录程俱籍贯的“新安”或“信安”,存在记述不够精确之处。
第二部分是有关《麟台故事》的考论,包括成书、刊刻、流传、体例、版本、辑佚、内容、价值等诸多方面。首先,是对《麟台故事》成书及其经过的探讨。即从《麟台故事》成书的历史背景出发,陈述了其具体的成书经过,进而揭示了程俱编著该书,一方面既有利于刚刚重建的南宋馆阁制度步入正常轨道和趋于完善,又有利于指导南宋馆阁征集、整理、储藏、修纂、利用图籍等日常工作进行得愈加规范;另一方面是政治目的,即凝聚北宋灭亡之后的士人之心,树立宋高宗继续崇儒尚文的形象,竖起宋王朝中兴的大旗。其次,是对《麟台故事》于南宋刊刻及后世流传加以考证。即依据现存《文苑英华》所载《麟台故事》刊刻信息,并结合程俱所作《进麟台故事申省原状》和《麟台故事后序》、该书影宋残本所存避讳字、《宋会要辑稿》引证该书内容等相关情况,确定了该书在南宋即已刊刻,并进一步推断其刊刻时间和地点;此外,又以南宋以来公私书目对《麟台故事》的著录为主,结合其他文献所载,考证了该书的流传情况。第三,是针对《麟台故事》版本的分析及其佚文的校证。既分析该书辑本与残本出现的缘由及其流布概况,又总结辑本与残本相互补充所形成的一些新成果,及其所存在的缺憾;此外,既以藏书印为主对宋残本的收藏与流传予以考察,又对《宋会要辑稿》新辑出的《麟台故事》六条佚文予以校证,并考其缘由而述其文献价值。第四,是对《麟台故事》体例、篇名及其内容的考论。即从该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事以系年、分门别类、有始有终的特殊编撰形式,分析其学术性质,界定其体例属性;以比较该书现存辑本与残本篇名及内容的异同,来说明该书内容不仅残缺不全,而且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舛误,目前据此并不能较为全面地反应北宋馆阁制度的全貌,尤其是不能准确呈现北宋馆阁藏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情况;同时,再以《永乐大典》现存《麟台故事》材料的疏证、《说郛》所见《麟台故事》六条内容的比勘,来进一步补充说明《麟台故事》辑本引据材料的来源与实际参照情况。最后,是对《麟台故事》学术价值的探讨。即《麟台故事》引证旧史与采摭旧闻的价值、所载馆阁专门史的史料价值,校勘宋代文献的价值、所具史料笔记与文学史的价值。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五个方面:一是考定《麟台故事》确有南宋刊行本,发现《麟台故事》应当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至嘉泰元年(1201)周必大、胡柯和彭叔夏校订始刻《文苑英华》之前,已经刊刻,且找到其他信实文献可为佐证。二是以《麟台故事》所载内容为依据,论述其学术价值,即结合北宋馆阁藏书问题,讨论《麟台故事》在研究北宋馆阁藏书方面的史料价值、校勘同类史籍的文献价值和记载馆阁文士文学活动的文学史料价值。三是通过深入研究《麟台故事》的相关内容,考察北宋馆阁藏书对当时整体文化水平的推进所起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四是通过对《麟台故事》辑本与残本内容异同的对比分析,特别是通过考索现存于《永乐大典》和《说郛》本的部分重要材料的来源,还原了四库馆臣辑出辑本时整改原材料的大致情形,得出了《麟台故事》辑本材料全部来源于《永乐大典》的结论。五是从《宋会要辑稿》中新辑六条《麟台故事》内容,并逐一校证,考证其中的五条确属现存该书辑本和残本均不载的内容,当可补其所缺,为自清人陆心源以来中断了百余年的《麟台故事》辑佚工作,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