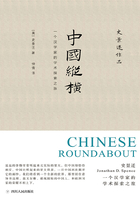
门德斯·平托的远游
门德斯·平托(Mendes Pinto)的《旅行》(Travels)写于1569年至1578年,原文为葡萄牙语,是一本风靡一时、梦幻迷离、引人入胜的小书。1537年到1558年期间,门德斯·平托居住在亚洲,并且游历了很多地方,《旅行》这本书便是他对自己的经历、幻想和反思的记录。这些冗长而散漫的手稿最终在1614年出版,一经面市便轰动一时,但这距离平托去世已经三十一年了。该书的西班牙语精装本于1620年出版,法语全译本于1628年出版,英语删节版于1653年出版。平托将本书的题目定为“远游记”(The Peregrinations),似乎与“旅行”有所不同。“旅行”听起来是有目的或者至少是观光性的,而“远游”则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可以随心所欲地不断更改,甚或完全没有目的和目标。
编辑和译者试图将平托的文字加以整理,但总是困惑不已。西班牙语译者试着给原文加上适当的巴洛克风格的阐释,而英语译者则将其编辑成了一部精致的历史论文,试图以此来证明平托的精确性。但是英文读者并不信服,正如在此书的英文版刚刚付梓之时,多萝西·奥斯本(Dorothy Osborne)在写给丈夫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的信中所说,“他的谎言/如所有的美丽谎言一样/愉悦而无害,他有说谎的自由/无所谓边界”。1695年,戏剧家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在《为爱而爱》(Love for Love)中,借一个角色之口责备另一个角色说,“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说的就是你这种人,一等一的大骗子”。
平托最终遇到了知音丽贝卡·卡茨(Rebecca Catz)。这位出色的编辑和译者聪明地指出,长期以来对平托作品的史实性和准确性的争论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平托的杰作并不属于历史,而是属于文学,特别是讽刺文学”。 因此,“《远游记》一书当中的断断续续、虚虚实实,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难题,是整本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想把平托的冒险日记与史书记载妥帖联系起来的历史学家应该保持缄默,因为平托作品中的年代“具有明显且大胆的不准确性,甚至是荒谬可笑的”。
因此,“《远游记》一书当中的断断续续、虚虚实实,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难题,是整本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想把平托的冒险日记与史书记载妥帖联系起来的历史学家应该保持缄默,因为平托作品中的年代“具有明显且大胆的不准确性,甚至是荒谬可笑的”。
卡茨的解读让我们摆脱了把平托的作品当作历史的束缚,可以轻松泰然地将平托的作品看作一本兼具讽刺文学和流浪文学要素的小说。卡茨认为,其中心目标是对葡萄牙建立海外帝国的行为、其背后的基督教十字军精神进行深刻而持久的批判。因此,平托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从事这两项事业的参战人员和神职人员。对亚洲人信仰和行为的描述主要是用来突显葡萄牙的荒谬和虚伪,而在16世纪下半叶,这些都很难公开地表达出来。我反复注意到,平托确实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笛福和戈德史密斯等人的前辈。然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平托是日益崛起的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传统的继承者。
卡茨敏锐地指出,平托和他一个卑鄙雇主的关系近似于《托梅斯的导盲犬》(Lazarillo de Tormes,1954)中主人公与第五个主人——兜售赎罪券的商贩——之间的关系。卡茨说:“因为流浪汉远不如这个社会腐败堕落,他需要学会交易的伎俩,这种伎俩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读者去理解、揭露和分析。”
卡茨相信,为了达到讽刺的目标,平托借助一个中心人物来展开叙述,并让四种不同的声音遥相呼应、彼此印证。这四种声音分别来自四个勇敢的男人:以其不言而喻的真诚赢得了信任的正直善良者、以其对恐怖的天真无知赢得了同情的淳朴者、勇往无畏地对抗邪恶的英雄和爱国者、参与了自己所谴责的邪恶活动的流浪者。
平托作品的结构笨拙,读者需要慢慢习惯。在平托撰写的原著(在芝加哥版中,他的原文有五百二十三大页)中没有任何章节划分。17世纪初平托去世后,编辑将其书划分成了二百二十六节,每一节都有一个描述性的标题。除英文版外,西班牙译本和法语译本都遵循了这一划分,这也被卡茨保留下来。这一划分有利于分节阅读,因为大多数小节都类似于小片断,而一个叙述的展开往往横跨十几、二十小节。根据我自己阅读这本奇异而强大的书的经验,就总体而言,它有十大主要的完整叙述板块,这十大板块都有简单的开头和结语,有对人物的详细介绍以及平托对于命运和自身生活的看法。特别是开头,往往有效地传达了叙述者平托的声音,混杂着抱怨、信念以及明显的环境要素:
每每回首我孩提时代及而后青春韶华期间所经受的种种艰难困苦时,我认为,我对命运的抱怨不无道理。似乎,时运对我尤为关心,偏重,无时无刻不追逐、折磨我,将此视为一种大振声名、无上荣光的事情。原因是我看到,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就不甘屈身于自己的国度。在故乡,我一直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时时担惊受怕,饱经风险。我决定只身前往印度。在那里,我非但未摆脱贫困,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更多的艰辛坎坷。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每当我看到,在这千难万险中,上帝总是救我于危难,佑我平安,又觉得对我经受的磨难不可多责。仅此一点,应对上帝感恩不尽。上帝愿我活在人间,草成拙作,留给孩子们——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将我在二十一载中饱经的沧桑告知后人。二十一年岁月中,在印度、埃塞俄比亚,沿阿拉伯海、中国、鞑靼、望加锡、苏门答腊和亚洲东部群岛的许多地方,我曾十三次被俘,十六次被卖。上述群岛在中国、暹罗、格乌斯、琉球作者的地理著作中被称为“世界的边缘”。对此,下文我将加以详述。
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平托,只是见到不同的学术著作中引用他的作品。然而,仅仅是这些被引用的文字,就已经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无论这些文字最终将导向何处,我都决定要阅读平托。之后我发现,他并没有十三次被俘,也没有十六次被卖——或者说至少无法从他的书中找到证据,但这就是平托作品的特点。他确实记录过在不同地方八次被俘和七次被卖为奴的经历,而且被卖给卑鄙程度各异的主人,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够受的了。但他却机智地发现,在一次交易中根本没有人想要买他,他怯懦地站在拍卖台上,不受垂青,肮脏不堪,半饿半饱,“像一匹悲伤的老马,被赶到了牧场上”。
对于平托来说,世界是不可预测的,充满了对比扭曲的排列组合:疯狂、可怖的残忍与温柔和关怀如影随形,一无所有与炫目的财富相伴相生,粗俗的迷信与哲学的深思出入相随。通过葡萄牙人和当地统治者的冲突——这常常也是(尽管并非总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描写,这十大板块都不同程度地彰显这些主题。平托的指责是公平的,葡萄牙人并非唯一的虐待者和谎言家。但是渐渐地,葡萄牙人成了最坏的人,因为在他们中间总是有一个沉思的平托,他是这本书的主角,而其他社团和统治者总是登上这个舞台,然后又都有节奏地依次退回到后台。
有些读者可能会对平托作品所划分的二百二十六个章节感到无从下手,甚至被吓坏,所以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十大板块主要叙述的内容。这些部分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所以至少能够让我们了解平托在东方的这些年是如何度过的。
第一部分(第二至十二节),背景是中东和埃塞俄比亚,主要叙述了寻找祭司王约翰后裔的故事,也描述了平托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第乌当奴隶和强盗的生活。第二部分(第十三至二十节)中平托在苏门答腊岛,卷入了巴塔克人(Battak)的战争;第三部分(第二十一至三十七节)继续讲述在苏门答腊的传奇故事,其中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亚路王国和亚齐王国之间残酷的战争。第四部分(第三十八至五十九节)讲述了一种不同的抗争,平托的海盗老板安东尼奥·德·法里亚(Antonia de Faria)追杀那个与他同样邪恶的海盗敌人——海盗哈桑师父(Hassim)。第五部分(第六十至一百一十六节)内容较长,既是关于平托在中国的冒险,也是安东尼奥·德·法里亚对于神秘的中国圣地的执着追求。
“再见,北京!”结束了这一部分,“北京”是本书的重点,也是平托离开欧洲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他缓慢的返程开始于与鞑靼人作战,而后他又探索了日本和琉球群岛,在缅甸目睹了野蛮的马达班战争并且见识了暹罗复杂的政治世界。最后一大部分(第二百至二百二十五节)主要集中讲述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日本的传教,讲述这位传教士的神迹、去世和葬礼。最后回到葡萄牙,平托被背信弃义的统治者剥夺了应得的奖赏,他用极富才华的言辞结束了他的作品,可谓悲情一叹:
尽管事情是这样的结果,但我认为,我的辛苦未得到应有的报酬乃是天意,是因我的罪而应有的下场,而不是受天命处理我这种事情的人的疏忽或过失。因为我在王国所有的国王身上(只有他们是报酬之流的真正源泉,但有时却忘掉理智、受制于好恶的渠道)看到他们有种神圣、感恩的热忱和宽宏的愿望,不仅用来奖赏那些曾为他们效劳的人,还犒劳那些从未为他们出过力的人。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和一些无依无靠的人不会得到努力的报赏,仅仅是因为渠道问题,而不是源泉问题,或换句话说是天意。不得有误。天意会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恰如其分,让所有人各得其所。
因此我要感谢上帝,他用此种方式来实现其神圣意志。我因犯有弥天大罪,不再抱怨世间帝王!
我们没有办法将书中的事实与小说的虚构区分开来,弄清楚哪些是平托真正做过的事情,哪些是他亲眼所见,哪些是他道听途说,哪些是他阅读的各种旅行记录,哪些是他编造的故事。这部书的解读五花八门,卡茨在注释当中勇敢地试图在所有领域(平托的作品被划分成不同的领域)回应学者对平托的各种评价,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指南。
就我从事的中国研究的狭窄一隅看来,我可以大胆猜测平托从未在中国内地游历,尽管他可能到过澳门、海南岛,也有可能到过金门或一些沿海小镇,在那里一些有胆识的中国商人从事着半合法的贸易。但是,他肯定读过一些不幸被中国人囚禁的葡萄牙、西班牙外交家或传教士们 所记载的东西,并且抄录了一些容易辨认的中国官僚使用的术语。
所记载的东西,并且抄录了一些容易辨认的中国官僚使用的术语。
在接近尾声的部分,平托提到曾与一位中国侍从或者说男仆在海上相识,从16世纪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在对琉球群岛的一起海难的记录中,平托同样提到他和一些葡萄牙人曾与“一些妇女”在一起,其中四人在随后的恐慌和筋疲力尽中死去了。平托在该书的其他部分记录过中国农村妇女在葡萄牙人突袭之后被抓走的恐怖经历,这些悲剧人物也可能是真实的,而并非虚构。
无论如何,平托的一些历险确实可以在其他资料中得到佐证。他确实在东南亚执行过外交和贸易任务,他也认识在日本传教的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平托还曾游历东南亚,并在1552年沙勿略死于中国沿海之后,于1555年随使团再次返回日本。但是出于一些避讳的考虑,平托往往没有把那些他本来可以讲的故事讲出来——这原本可以大大增加叙述的真实性。比如,他既没有提到他在1540年代的远东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也没有提到在1551年他将这笔钱的大部分给了沙勿略,让其在日本修建一座教堂。平托也没有提及他自己于1554年加入了耶稣会成为在俗修士,直到1557年才离开教会。这一时期平托居住在果阿,也是他最为虔诚的时期。这就可以理解平托描写1554年2月在果阿迎接沙勿略遗体的动人笔触。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丝毫没有讽刺的意味:
此时,天已渐明。从城中驶来六艘船,上面坐着这位大师生前的四五十个虔诚信徒。他们高举火把,他们的仆人手持火炬明烛。一进教堂,他们跪到大师的墓或称棺材前,热泪盈眶地顶礼膜拜。此时旭日东升,他们出发到城中去。
路上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带着许多人乘坐一小艇。那些人都高举火把、手持明烛,当运送大师遗体的独桅纵帆船与他们迎面而过时,所有人都倒地磕头。后面还有十几艘船也这样做,因此快到码头时,后面已跟了二十多艘船,上面坐着一百五十多名住在中国和满剌加的葡萄牙人。这都是些尊贵的富人,如前所述,他们都手持火炬明烛。他们的水手都拿着蜡烛。凡是见到这一隆重的基督教礼仪场面的人,都为之感动。
平托冗长的讲述颇具活力,这要归功于他有趣的写作风格,比如,他会选定一个特定角色,然后精心地修饰他的语言。东方君主处心积虑的言辞从未使平托感到疲惫,他将插科打诨寓于严肃之中,来表达最为虚情假意的情感。比如说,亚路国王不会仅仅请求葡萄牙人帮助他拖延与亚齐王国的战争,在提出极其实际的要求之前,他首先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面对九天之上、至高无上、万分尊严的上帝,在发自内心深处的悲叹中,敬请我王为我做主,我以国王的名义向二位司令大人求援。我主早在你们的先辈——万顷波涛之上的吼狮阿尔布克尔克(Albuquerque)当政时就已宣誓做印度各族人民及大葡萄牙国举世无双的君主的忠臣。葡萄牙国王作为举世无敌的君主保证永远保持这君臣关系,承担起帮助我们抵御敌人的责任。既然迄今为止我们从未破坏过这种君臣关系,为何你们不履行君主所承担的义务?你们难道不清楚,正是因为我王如同纯粹的葡萄牙人是基督徒,所以亚齐王才来攻打我们的国家吗?他派我此来,把你们当作真正的朋友,向你们求援,在危难之中助其一臂之力,但你们却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们。如果你们不愿帮忙的话,至少可以派四五十名葡萄牙人携带火器,教我们使用,提高我们的士气。给我们四罐火药,两百发短炮用的炮弹,便足以满足我们的愿望并保证我们抵御敌人侵占我们的国土。
据平托回忆,在之后的协商中,亚齐国王给亚路国王写了封回信,信的结尾相当精彩:“你的信使到我的亚齐宫殿的第一天我就把他赶走了,不愿再见他,不愿再听他。这些他会详细告诉你的。”
平托的一个葡萄牙朋友将接待他们的人都喝倒在桌子下面,他被狂喜的缅甸众人抬上了一头大象,他们以赞美诗向他致敬:
百姓们,请你们以欢乐和哺育我们大米的太阳神来欢呼这位伟人。现在你们的土地上来了一位圣人,他的酒量大过世间所有人,我们这里二十个名人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他的声誉与日俱隆。
平托的叙事风格时常也有着令人钦佩的简洁度,卡茨将其完美地翻译成了英文。比如说,平托曾记载了一群利欲熏心的葡萄牙人离开中国前往一个神奇的国度:
载着生丝,怀着发财的希望,十五天内,九条在港内的船就做好了一切出海的准备工作。但准备工作并不充分,有些船没有领航员,只有船主。这些人对航海术一窍不通。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众人扬帆起航。一路逆风,逆潮,毫无理智,完全忘记了大海的危险。他们是如此的固执、盲目,任何不利的事情都不予以考虑。我就在这样的一条船上。
对于被满剌加国王统治着的吉打王国来说,没有人能够提供比这更好的历史场景:
我们抵达时,国王还在为过世的父亲大办丧事。整个葬礼很讲排场,鼓乐、舞伎、哭丧妇(还有为大量穷人提供的免费饭菜),应有尽有。其父乃他所杀,目的是同其母结婚,因为她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平托的《远游记》中有很多古怪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平托几乎没有用过第一人称向我们叙述。卡茨提到的四种不同的角色也都在详尽地转述着别人的话,并宣称绝对准确无误,但是平托自己的讲话和思想则被总结起来置于一旁,作为写给读者的简略箴言,或者像是从别人那里转述过来的。在整本长篇巨著中,我找到了两处例外,平托脱下了保护衣,直接使用了加引号的第一人称。平托似乎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文字风格,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他绝对是有意为之。
当平托面对上文提到的那个吉打王国的暴君时,第一次出现了他自己的话。这个暴君刚刚杀死了平托的游伴——一个穆斯林商人。平托将这种刑罚称为“格雷戈热”, 包括“从手脚和脖子处将人活活锯开,然后再从胸口一直锯到背脊”。国王坐在一头大象上,向平托展示了他朋友已经被肢解的尸体。平托惊恐万分,一头跪在国王的坐骑大象前,哭诉着说:
包括“从手脚和脖子处将人活活锯开,然后再从胸口一直锯到背脊”。国王坐在一头大象上,向平托展示了他朋友已经被肢解的尸体。平托惊恐万分,一头跪在国王的坐骑大象前,哭诉着说:
“大人,我请求你将我收为奴隶吧,而不要像躺在那里的人那样将我处刑。我以基督徒的名义向你宣誓,我不应该那样死。我要提醒你的是,我是满剌加要塞司令的外甥。你要多少钱,他都会满足你。他的儒鲁潘戈(Jurupango)船上有许多货物,你可尽数拿去。”
听了我这番话,他说道:“上帝保佑!怎么回事!我难道是这样坏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别害怕。请坐,休息休息。我看你是惊着了。等你稍微恢复了,我再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让人杀死这个与你同来的摩尔人。如果是葡萄牙人或基督徒,即便是他杀死了我的儿子,我也不会这样做的。”
这个可怕的场景的幽默之处在于,他将暴君平静的言辞与平托可怜的恐惧并列,表现出了气势汹汹的葡萄牙人背后的怯懦,也表现出他们所遭遇、所掠夺以及所征服的外国民族在道德上的含糊不清。
平托第二次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在《远游记》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一次的场景完全不同。平托和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同坐在一条船上,他们正在前往马六甲的路上,试图组建第一支到日本的传教会。然而,他们的轮船遭遇了可怕的风暴,很多人失踪,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在这戏剧性的一幕中,平托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
于是,他(沙勿略)把我召到了他所在的艏楼上。众人令他有所悲伤,问我是否愿意让人给他烧些开水喝,因为他的胃很难受。当时我无法满足他的要求,船上没有炉子,头天晚上风暴来临时我们把甲板上所有的东西都推到海里去了。于是他又对我说,他的头很虚,一阵一阵地发晕,我对他说:“没有什么大事情,是您不习惯这样,因为三天未合眼了,也许又加上没吃什么东西的缘故。这是杜瓦尔特·达·伽马(Duarte da Gama)手下的一个水手告诉我的。”
听罢,他回答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现在很难过。”我十分同情他。救生艇漂去后,他为在船上的侄子阿方索·卡尔沃(Afonso Calvo)哭了一整夜。
我见到大师此时不停地打哈欠,我对他说道:“您到我们舱室中去靠一靠吧,也许能休息休息。”
此时,平托已经从对满剌加暴君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了,并且获得了一种难得的惬意。我把这两段话仔细琢磨了好几天,比较它们的用词,寻找它们的内涵,思考平托为什么会在这两段话中分享他自己的声音,而且仅仅是这两段话。或许,并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大胆地猜想,平托一心要告诉我们两件事:这种恐惧实在是难以抵抗,我们会丧失尊严,变成悲哀的可怜虫在地上卑躬屈膝。但是当我们面对伟大的善良之时,也能够真诚地分享这种善良。即使是平托,这个无赖、闲汉、商人、懦夫、海盗和徒步的骑士,也能够在神圣之人束手无策时,用寥寥数语安慰他。在这两段中,平托出色地为我们概括出了恐怖和神圣的含义,这是葡萄牙16世纪全球探险的伟大历史剧中相互交织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