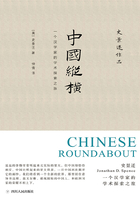
中西交流
黄嘉略的巴黎岁月
对于黄嘉略来说,1713年的秋天和初冬是一段颇为艰难的日子。 巴黎的天气非常恶劣,寒冷刺骨,雾霭浓重。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又似乎永无止尽,民气低落,物价飞涨,货币持续贬值。尽管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克洛德·雷尼埃(Marie-Claude Regnier)在1713年4月成婚,他们婚后的生活也依然十分艰难。这对小夫妇租住的房子位于塞纳河南岸靠近巴黎圣母院的盖奈戈街(Rue Guénegaud),由于没有钱支付木材和煤炭的正常花销,这间小房子始终很冷。他们的家具少得可怜,衣服也很少,根本买不起像样的结婚用的新床。他们甚至连盐都买不起,使得本就简单的饭菜连盐味都没有。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黄嘉略会在某些早上因咯血而醒,在这种情况下,他总会感到筋疲力尽,需要躺在床上休息好几个小时。
巴黎的天气非常恶劣,寒冷刺骨,雾霭浓重。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又似乎永无止尽,民气低落,物价飞涨,货币持续贬值。尽管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克洛德·雷尼埃(Marie-Claude Regnier)在1713年4月成婚,他们婚后的生活也依然十分艰难。这对小夫妇租住的房子位于塞纳河南岸靠近巴黎圣母院的盖奈戈街(Rue Guénegaud),由于没有钱支付木材和煤炭的正常花销,这间小房子始终很冷。他们的家具少得可怜,衣服也很少,根本买不起像样的结婚用的新床。他们甚至连盐都买不起,使得本就简单的饭菜连盐味都没有。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黄嘉略会在某些早上因咯血而醒,在这种情况下,他总会感到筋疲力尽,需要躺在床上休息好几个小时。
黄嘉略到达巴黎的旅程本身就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黄嘉略,1679年出生于中国的沿海省份福建,他的父亲皈依了天主教,受洗入教并取教名保罗。保罗一心想要虔诚地过独身的修士生活,因而一直逃避结婚,但在父母的强迫下他最终还是成了亲,毕竟保罗是家中独子,不能在他这儿断了香火。然而,在保罗的妻子一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黄家人几乎要绝望了。保罗的妻子第五次怀孕的时候,小两口暗暗发誓,若能诞下男丁,便将其献给上帝。这次果真是个男孩,他们便让其受了洗礼,取教名嘉略。保罗在儿子刚七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尽管黄嘉略的母亲不太清楚怎样才能将小儿子献给上帝,但她还是遵守了这一誓言。当时恰逢李斐理(Philibert Le Blanc)——这位四十二岁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到小镇传教,为黄家解决了这个难题。于是,黄母便带着小嘉略去见李斐理,并向他阐述了自己和丈夫的誓言。李斐理深受感动,答应教育小嘉略,并使其投身宗教事业。为了避免李斐理产生误会,也为了遵守清朝的法律,黄母让李斐理正式收小嘉略为义子,从此两人在一起学习、工作了三年。
李斐理很有远见,他为小嘉略请了当地很好的老师,辅导他继续学习中文,同时亲自教他天主教神学和拉丁语。三年后,出于至今尚不得而知的原因,小嘉略被转托给名义上的罗萨利主教梁弘仁(Artus de Lionne),继续此前在李斐理指导下业已开始的各种教育。1695年前后,黄嘉略十几岁的时候,便开始游历中国的南方和中部地区,投奔黄家分散在各地的亲戚,并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后来,黄嘉略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写道,正是在这次游历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帮助他“在国外体面地生活”。
在黄嘉略之前,仅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到达西方。前往西方的旅程不仅仅是迈入陌生境地的可怕的一步,同时也是违背大清律条的,这意味着放弃本土的价值观。黄嘉略之所以能前往,是一系列机缘巧合的结果:黄嘉略的母亲刚刚撒手人寰,大姐有能力也有意愿接管家里的一切事务;而黄嘉略仍然闲不住,旅游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下来,他还在福建的小镇中巧遇了梁弘仁,而在此之前,他们俩已经数年未见。梁弘仁告诉黄嘉略,自己即将被召回欧洲,并建议黄嘉略与他同行,黄嘉略当即一口答应。1702年2月17日,梁弘仁和黄嘉略从厦门出发,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八个月后抵达了伦敦。当时,路易十四深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法国与英国的交战期,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一番努力,两人跟随有外交豁免权的巴伐利亚选侯的使节一道到了法国。1702年底,他们抵达巴黎,经短暂停留后,到达罗马。
如果黄嘉略不那么具有冒险精神,或者是对宗教更加虔诚的话,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留在罗马接受教育,成为神父,并最终回到中国继续传教。但在罗马,黄嘉略似乎对神职人员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在他回到巴黎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生活在一起之后,这种怀疑进一步强化了。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下,黄嘉略结识了法国国王图书馆的馆长比尼昂教士 。比尼昂刚刚接到一项棘手的任务,要对一批新发现的汉语和满语的藏书进行分类编目,这批藏书在国王图书馆当中越积越多。但比尼昂对中文一无所知,他需要一个中国助手,而黄嘉略需要一份工作,两人一拍即合。1711年,黄嘉略自己租了房子,在国王图书馆获得了中文翻译官的响亮称号,以及少量的奖金。
。比尼昂刚刚接到一项棘手的任务,要对一批新发现的汉语和满语的藏书进行分类编目,这批藏书在国王图书馆当中越积越多。但比尼昂对中文一无所知,他需要一个中国助手,而黄嘉略需要一份工作,两人一拍即合。1711年,黄嘉略自己租了房子,在国王图书馆获得了中文翻译官的响亮称号,以及少量的奖金。
在巴黎,黄嘉略专心学习法语。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对于他放弃神职深感遗憾,但并没有因此而记恨他,仍然为他提供住所和各种资料。在他的法语比较流利之后,他利用教会关系获得了一些翻译工作,并且开始追求玛丽。到1713年的春天,通过给教会成员翻译中国往来的信件,并且为法国学者翻译一些艰深的著作,如天文学的文献和中国古代典籍,黄嘉略获得了一些收入。但是,这点儿钱根本不够用来结婚,而且几位教会的长老也提醒他这可能会很麻烦。但是玛丽的父母似乎很喜欢黄嘉略,并且觉得应该给这对年轻人一个机会。他们时常到盖奈戈大街去看望这对年轻人,有时还带点酒和食物作为小礼物,或者借给夫妇俩一些小钱,帮他们偿还宿债。
1713年11月下旬,黄嘉略和妻子走出了经济上的困境。几个月以来,国王图书馆馆长比尼昂一直在为这个中国编目员申请薪水,并亲自到凡尔赛去争取这笔钱。11月中旬,在比尼昂雄辩的言辞下,国王的大臣终于承诺支付五百里弗赫 。比尼昂在信中写道:“虽然您已经对他展示了善心,但我们年轻的中国编目员,如果不能得到国王的赏赐便难以为生了。……他身无分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下令,赐他几枚金币吧。”虽然仍遇上了行政上的障碍,但在11月27日的时候,黄嘉略最终拿到了这笔总数为五百里弗的薪水。黄嘉略和玛丽偿还了所有债务。“所有钱都还清了。”黄嘉略在他的软皮小本记载的随笔日记中高兴地写道。26日,黄嘉略已经预感到会有意外的收获,便给妻子买了两个鸡蛋作为礼拜日的早餐。现在,他又接着买了盐。28日,也就是星期二的早上八点,新购买的一车柴火也送到家里。国际政治局势似乎也在分享他们的欢乐,法国结束了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和平终于到来了。黄嘉略和玛丽与其他巴黎人一起到教堂里去唱赞美诗,表达感恩之情。
。比尼昂在信中写道:“虽然您已经对他展示了善心,但我们年轻的中国编目员,如果不能得到国王的赏赐便难以为生了。……他身无分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下令,赐他几枚金币吧。”虽然仍遇上了行政上的障碍,但在11月27日的时候,黄嘉略最终拿到了这笔总数为五百里弗的薪水。黄嘉略和玛丽偿还了所有债务。“所有钱都还清了。”黄嘉略在他的软皮小本记载的随笔日记中高兴地写道。26日,黄嘉略已经预感到会有意外的收获,便给妻子买了两个鸡蛋作为礼拜日的早餐。现在,他又接着买了盐。28日,也就是星期二的早上八点,新购买的一车柴火也送到家里。国际政治局势似乎也在分享他们的欢乐,法国结束了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和平终于到来了。黄嘉略和玛丽与其他巴黎人一起到教堂里去唱赞美诗,表达感恩之情。
债务还清之后,黄嘉略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奢侈品”:面包条、奶酪、两种馅饼、蛋糕和炖肉用的蘑菇。还请来了裁缝为黄嘉略裁剪三件套的衣服,包括裤子、刺绣背心和黑色外套。还给玛丽买了剪刀、丝绸和针线,她可以做些裁缝活儿。他们还精心挑选了一张新床,但是在最后一刻,玛丽还是不让买了。黄嘉略仍旧时常生病、发烧,但是现在他买得起药品,也看得起医生了。随着政治气候的好转,巴黎也迎来了最温和的12月。
温暖的天气和美食让黄嘉略开始思考未来。他想要一个孩子。从他日记中的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他的兴奋和期待。这些话通常用罗马字母拼成的汉字书写,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有人偷窥日记中的隐私,甚至可能是防备妻子玛丽偷看。这样的内容第一次出现在1713年11月11日,记载了玛丽在一周以前满月时候来了月经。黄嘉略是以此来判断妻子怀孕的征兆么?如果是的话,12月28日的日记就透露出他的失望:玛丽又来月经了,这是在奥古斯丁教堂做完圣诞节弥撒之后回家途中开始的。下一次来月经是1月25日,再下一次是2月底。日记有些地方还有一些更神秘的符号,可能指的是房事,大多数出现在礼拜日的弥撒前后。
其他的记录描绘了夫妻两人的共同生活:玛丽到商店、市场和肉店购物;玛丽特意为黄嘉略做了大米布丁或他最喜欢的油炸果馅饼;家里有烟,还有酒和茶;黄嘉略和朋友去城里的俱乐部。这对夫妻喜欢打牌,特别是和黄嘉略的岳父岳母一起玩皮克牌(Piquet)。他们还经常一起买彩票——这种新活动以巨额奖金来满足人们暴富的欲望,在当时非常热销。当然,也有很多关系紧张的时刻。夫妻俩都经常生病或抱怨,玛丽会突然没有缘由地发脾气,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直到很晚才睡觉,有的时候还会绝食——通常是黄嘉略负责做饭——或者是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突然发火。钱仍然很少,还会发生些小灾小难,随时可能击垮这对在贫困边缘挣扎的夫妇:如丢失了一条面包,丢了二十七苏 (后来又找到了),油(没有交代是灯油还是食用油)撒在了玛丽漂亮的裙子上。这对夫妻一直坚持参加弥撒,但是根据黄嘉略的记载,他们几乎每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前往不同的教堂。如果黄嘉略去了奥古斯丁教堂,玛丽则会去圣絮尔皮斯教堂(St. Sulpice);如果黄嘉略去了圣絮尔皮斯教堂,玛丽则会去圣日耳曼教堂(St. Germain)。这里是否有着我们不能理解的节奏规律?抑或在去做礼拜的时候让别人看到自己与外国的丈夫在一起,玛丽会觉得很难堪或尴尬?
(后来又找到了),油(没有交代是灯油还是食用油)撒在了玛丽漂亮的裙子上。这对夫妻一直坚持参加弥撒,但是根据黄嘉略的记载,他们几乎每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前往不同的教堂。如果黄嘉略去了奥古斯丁教堂,玛丽则会去圣絮尔皮斯教堂(St. Sulpice);如果黄嘉略去了圣絮尔皮斯教堂,玛丽则会去圣日耳曼教堂(St. Germain)。这里是否有着我们不能理解的节奏规律?抑或在去做礼拜的时候让别人看到自己与外国的丈夫在一起,玛丽会觉得很难堪或尴尬?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1714年2月的时候,黄嘉略已经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城市里优雅的法国人。国王图书馆里一位细心的职员记录了黄嘉略婚后在盖奈戈大街定居以来,所添置的衣物、家具、寝具、厨房用品和书写工具,也清楚地罗列了黄嘉略的衬衫、西服、袜子、鞋帽、雨伞、剑和皮带。除了那把剑以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东西。但是在一份名为“黄嘉略开销备忘录”的附加清单中,记载了黄嘉略从领取国家基本救济金到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这里罗列有六条棉布领带、六条西装袖口褶边、两颗扣褶边的银扣;两顶假发,其中一顶价格昂贵,另一顶价格适中;一根流苏拐杖。其中最贵重的一件前襟配有纽扣的齐膝长斗篷,这种衣服被称为“罗屈埃洛尔”(Roquelaure),是以罗屈埃洛尔公爵命名的衣服,新近才流行起来。
突然之间,黄嘉略的生活中出现了新光彩。为此,他热情洋溢,脸修得干干净净,头戴擦过粉的假发,领带和袖口处有整齐的流苏,身着斗篷,手持流苏手杖。1714年2月8日以前,他总是用第三人称简称自己为“黄先生”或用“H”来指代自己。但是在2月份以及3月初的日记中,他已经改称自己为“圣黄公爵阁下”、“福建的红衣主教黄殿下”、“黄元帅阁下”以及“黄大老爷”;而玛丽的穿戴,即使没有黄嘉略那么奢华,也比之前更好了,对她的称谓也随之提高,有时称她为“尊贵的黄夫人殿下”,有时为“公爵夫人”。而对他的岳母雷尼埃夫人,黄嘉略则称她为“大公夫人殿下”。
在这些轻松而浮夸的文字记述中,有一则是黄嘉略在1714年2月17日写下的,他半模仿当时流行小说的语调写道:“我亲爱的读者,你看到了,黄大使先生整日忙得不可开交,还要接见各种各样的人。”当时黄嘉略正在编纂一部法汉字典,馆长比尼昂认为这是最首要的任务,如此一来,法国的学者便可以广泛地使用这些皇家馆藏了。比尼昂相信,要为汉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就有必要编纂一部基础的语言学习指南。这项任务相当艰巨,在此之前,欧洲从未对汉语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对两种文化和语法的比较也尚未展开。因此,为了帮助黄嘉略完成任务,比尼昂为他安排了一位学术地位日渐崛起的年轻助手——刚被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录取的尼古拉斯·弗莱雷(Nicolas Fréret)。弗莱雷比黄嘉略小九岁,但是他与黄嘉略一样,是家中独子,有四个姐姐。这两人很快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在第一次见面后,弗莱雷如此写道:我觉得黄嘉略是一个“有魅力、谦虚的年轻人,他似乎……颇具天赋”。但唯一的问题是——
(黄嘉略)对于欧洲的科学和方法论一无所知。甚至他说的法语也很难懂,他的母语与欧洲语言之间丝毫没有共同点,他学得一知半解。因此,他完全无法理解法语的语法模式,也不知道充斥于书中的那些抽象的语法术语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接下来的1713年到1714年中,这两人的合作非常成功。弗莱雷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工作,解答黄嘉略的各种问题,试图帮助黄嘉略理解法语的核心——语法结构,并卓有成效地将这些语法结构用于汉语语法的分析。在他的帮助下,黄嘉略的法语进步很大,已经可以着手研究主要的问题,并提出假设性答案,然后再由弗莱雷对答案进行核实。黄嘉略也开始教授弗莱雷中国汉字的结构和意义,使弗莱雷摆脱了对汉字流行的看法,认识到中国的汉字与欧洲的象形文字截然不同。黄嘉略还为弗莱雷讲解了汉字的构成,说大字典中收录的七万或者更多的形形色色的汉字实际上基本都由二百一十四个部分构成,中国人称这些组成部分为“偏旁部首”。只要按照既定顺序把这些偏旁部首写出来,人们就可以很轻松地进入这个看似令人困惑的汉字世界。
在默契的相互配合下,这两人完成了汉法字典的暂定词汇清单,将两千个汉字翻译成法语。这些单词是根据实用性来挑选的,主要用于造句或描述常见物品和日常需要。弗莱雷用崇敬的语气记录了黄嘉略的适应能力和韧性:“我被这个中国年轻人的温和、谦逊有礼,特别是坚忍不拔的韧性感动了。他的处境在欧洲人看来是那么的令人绝望。远在四五千里格 的异乡,并不富裕,也无专长,还没有获得任何资助,只有微薄的津贴。津贴全靠工作,但他明白,自己甚至连工作也无法独立完成。其他人也很难搭上手来帮助他,他在工作上的成就永远大不到哪儿去。但令人惊讶的是,他总是处变不惊,富有幽默感,这也让我相信,那些关于中国人性格的各种记录是真实可信的。”在充满了种族偏见的西方文学当中,这番话是那么重要而饱含感情。
的异乡,并不富裕,也无专长,还没有获得任何资助,只有微薄的津贴。津贴全靠工作,但他明白,自己甚至连工作也无法独立完成。其他人也很难搭上手来帮助他,他在工作上的成就永远大不到哪儿去。但令人惊讶的是,他总是处变不惊,富有幽默感,这也让我相信,那些关于中国人性格的各种记录是真实可信的。”在充满了种族偏见的西方文学当中,这番话是那么重要而饱含感情。
一个居住在巴黎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周围法国人的兴趣。在黄嘉略之前,可能只有两个中国人到过法国,一个在1680年代,另一个在18世纪,但是这两人都没有在巴黎居住这么长时间。所以黄嘉略经常受邀外出或者在他的住所接待拜访者,这些拜访者通常是弗莱雷的朋友,或者是居住在附近的学者和天文学家弗朗索瓦-约瑟夫·迪莱尔(Francois-Joseph Delisle)的朋友。毫无疑问,有些人只是出于好奇,但是也有人希望从黄嘉略这里得到一些关于他的家乡中国的信息。后者之中,以年轻的孟德斯鸠后来取得的名声最为显赫。当时,孟德斯鸠刚刚完成了有关法律的研究,他在1713年,他二十四岁那年的夏天或秋天拜访过黄嘉略。
与往常一样,孟德斯鸠的头脑中充满了无数的想法,黄嘉略对其中两个特别有共鸣。第一个想法是写一本从亚洲的视角看法国社会的书,嘲笑法国人的自我优越感,并对欧洲价值观加以道德上的批判。尽管孟德斯鸠最终以《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 1721)的形式展现了这一内容,但是我们知道,黄嘉略是单纯的波斯人的原型之一。孟德斯鸠借波斯人的提问,批判了法国人的自负心态。令孟德斯鸠好奇的是,黄嘉略对法国人的基督教信仰深信不疑,有一次他竟然将自己帅气的帽子留在了教堂里,一个人出去溜达了一圈。当黄嘉略回到教堂的时候,他的帽子已经不翼而飞。根据孟德斯鸠的记载,黄嘉略曾一度相信欧洲社会道德高尚,因而才废除了死刑,而当他见到一些罪犯在巴黎被处决的时候,不禁惊讶万分。
对于孟德斯鸠来说,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法律结构,这是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 1748)中比较政治学部分所分析的基本内容。1940年代末,英国学者罗伯特·沙克尔顿(Robert Shackleton)证实了孟德斯鸠和黄嘉略之间的交往。他在拉布莱城堡的孟德斯鸠故居图书馆的橱柜中,翻出一本名为《地理学》的读书笔记的合订本,有一部分题为“与黄先生谈话中的中国印象”,长达二十页。其中,孟德斯鸠用“谈话”的复数形式说明了他曾多次拜访黄嘉略,而孟德斯鸠在1713年11月收到父亲的死讯后离开了巴黎,所以他拜访黄嘉略的时间应该在此之前。
正如弗莱雷和黄嘉略在学习语法上的兴趣相投一样,孟德斯鸠和黄嘉略之间也存在共同的爱好。孟德斯鸠渴望从黄嘉略那里了解中国的信息,而正如专门为此准备的一样,黄嘉略在1702年离开中国之前,正好长期在中国内地游历。孟德斯鸠系统的提问可能也启发了黄嘉略,给了他分类和整理早期种类繁复的数据的概念。这对他1716年投入设计一部关于中国的两卷本宏伟著作来说,至关重要。
根据孟德斯鸠的记录,1713年他们的交流涉及的广泛内容,是从中国的宗教体系开始的。黄嘉略解释道,在中国有三大互相交融的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并不相信灵魂永生,却认为焚烧祭祀供品产生的烟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逝者的灵魂相结合,所以在祭祀过程中,亡灵“愉快地重生”。佛教相信地狱的存在,并且认为杀生——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是不正确的行为。佛教徒不结婚,佛教中的慈悲之神观音正如圣母马利亚一样,受圣灵感应而怀孕。尽管黄嘉略并没有对佛教做出评价,但他是否在暗示佛教和基督教的某种相似性?孟德斯鸠认为,儒教就像斯宾诺莎主义一样,从“天”的思想中引申出一种“世界精神”(âme du monde)。黄嘉略还谈到了中国两种可怕的死刑——火刑(在黄嘉略生活的时代其实并没有施行)和凌迟(在当时仍然很流行),以及中国人的衣着、坟墓和家庭财产观念。在一次长谈中,黄嘉略谈到了他对中文和语法的看法,孟德斯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其中有多少是来自黄嘉略和弗莱雷的合作研究。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黄嘉略还为孟德斯鸠演唱了一首中文歌,并用中文背诵了《天父》(Our Father)。
在后来的交谈中,黄嘉略和孟德斯鸠不断开拓新的话题领域。他们讨论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科举制的性质和形式,以及中国国家的性质。得知中国在历史上经常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孟德斯鸠感到非常惊讶,并且理解了黄嘉略的观点:早期,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人总是夸耀自己的朝代多么伟大,这是典型的自负自大:如果果真如此伟大的话,1640年代的满洲人为何这么快就征服了明朝?中国审判中的连坐制也让孟德斯鸠大为震惊,因为很多无辜的人会因此受到牵连。黄嘉略也为孟德斯鸠介绍了中文在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用法:在问候的时候用敬语,在介绍自己或自己家庭的时候用自谦语。黄嘉略还清楚地讲述了满人统治对汉人的镇压和侮辱,以及中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和妇女的“三从四德”。这两人之间的交流——至少从孟德斯鸠的记录来看——最终以对中国历史的探讨,以及中国对洪水、日月食的时间的判定方法而告终。尽管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对自己在中国文化、政治方面的造诣非常有信心,但在“地理学”的笔记当中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写道:“我相信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
如果说孟德斯鸠开阔了黄嘉略的眼界,让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社会,那么法国商人带来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刺激。他们邀请黄嘉略参与他们的对华贸易,这四人都是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他们决定打开与中国几座大城市的贸易渠道,因此建议黄嘉略做他们的助手和翻译,为期十八个月。黄嘉略对此非常感兴趣,但他告诉这四人,他要先和图书馆馆长比尼昂协商,根据比尼昂的反应再做决定。比尼昂立马给大臣蓬夏特兰(Pontchartrain)写信,蓬夏特兰极具权势,是路易十四时期主管政务和海洋事务的大臣,对华贸易就归他管辖。1714年2月,考虑到公司的商船就要起航了,所以此事需要尽快讨论。黄嘉略2月24日的随笔日记当中写道,“黄元帅”在两位主管的陪同下,颇有风度地亲自拜访了大臣蓬夏特兰。但是,这种玩笑般的称呼是关于这次航行的最后记录。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商船已经起航,也可能是因为黄嘉略不忍离开法国和妻子,还有可能是他担心自己的津贴一旦被取消就不会恢复——这也是有道理的,毕竟他经历过生活拮据的日子。
朋友弗莱雷也为黄嘉略提出过一些赚钱的方法。当时,阿拉伯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被译成法文,一时洛阳纸贵,译者取得了可观的收入,弗莱雷建议说“翻译中文的小说可以让他名利双收,摆脱深陷其中的生活窘境”。黄嘉略似乎欣然接受了这个想法,两人还一起完成了部分明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初稿。但后来,这一计划又被束之高阁了,因为弗莱雷认为其故事情节“太严肃而缺乏娱乐性”,仅仅靠主角之间的“文学辩论”推动情节的发展,难以吸引当时的法国民众。所以,这两人又将精力集中到之前的字典编纂上来。此前,按照比尼昂的建议,这两人按照汉字发音的字母顺序排列汉字;现在,黄嘉略已经把汉字结构向弗莱雷解释清楚,因此两人重新按照二百一十四个偏旁部首的顺序来编纂。在弗莱雷的建议下,黄嘉略也开始尝试翻译一些中国的散文、诗歌、名家书信和正式文体的代表作。
黄嘉略和玛丽家里两件颇大的家务事,让令人兴奋的学术合作曾几度中断。第一件是黄氏夫妇决定搬家,离开盖奈戈街的狭小住所,搬到更宽敞的公寓中去,以便有地方放置新买的家具,衬托出黄嘉略更加高贵的地位。4月21日,他们在伽奈特大街(Rue des Canettes)找到一处住所,这条大街从古老雅致的圣日耳曼教堂一直通到拥有高大新廊柱的圣絮尔皮斯教堂。为了搬家,黄氏夫妇还买了一张宽敞的新床,有四尺宽,饰绛色帷帐、羽绒床垫、黄花刺绣的枕头,以及水仙花色的塔夫绸床单。此外,黄嘉略的岳母雷耶尼夫人还买了羽毛装饰在床柱的顶上。尽管黄嘉略仍然在生病,有时会咯血,非常虚弱,玛丽也经常大发脾气,不时头痛、腿痛,7月6日他们还是搬家了,并为此花了两周的时间。26日,黄嘉略还请来锁匠为他的房门配置了两把新锁。到8月份的时候,第二件大事儿发生了:玛丽怀孕了。
秋天的生活颇为宁静,只是黄嘉略从来没想到有如此糟糕的天气。8月24日他匆匆在日记中写下,“天气似乎一直都很差”, “今年真是个雨年”。但在偶尔天气不错的时候,黄嘉略会和玛丽以及岳父岳母一起到家附近的卢森堡公园去散步,偶尔也会溜达到巴黎荣军院(Les Invalides)的空地上。黄嘉略还加入了一个四十人的组织,一起大批量购买彩票,他们的新房东——包蒙德(Bomond)夫人还教玛丽将大麦与红糖调和服用,来减轻腹部的疼痛感。此时黄嘉略有很多工作要做,既要自由翻译些作品,还要和弗莱雷编纂字典。
1714年12月26日清晨,他们平淡的新生活以及对新生儿的兴奋期待被毫无征兆地打断了:弗莱雷被秘密逮捕进巴士底狱。弗莱雷的罪名是为法国的詹森教派张目,帮助出版了有关当时宗教争论的非法材料,还恶意攻击当时被奉为正统的《法国历史》(History of France,皮埃尔·丹尼尔[Père Daniel]著),如此的罪名和牢狱之灾使得所有与弗莱雷有往来的人都感到危险。黄嘉略和妻子必定会非常担忧,一旦黄嘉略受到牵连被判罪,就将失去工作和未来。弗莱雷入狱后,黄嘉略又有了一个新的助手,艾蒂安·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被认为是法国学术界冉冉升起的东方学家,但他也是一个狂妄自负、野心勃勃、极富争议的人。黄嘉略和傅尔蒙之间从来也没有达成和弗莱雷那种友善和谐的合作关系。
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下,1715年的春天,黄夫人玛丽在伽奈特大街的住所诞下一名女婴,也许正是在那张让黄嘉略颇为自豪的铺着水仙花色床单的大床上。这个女婴非常健康,当时的一位邻居后来回忆道,“看起来很像中国人,她的脸型和肤色明显和欧洲人不同”。但是黄夫人却因为生产而生病了,产后的高烧很快就耗尽了她的体力,并在几天之后夺去了她的生命。黄嘉略在一年后回忆起这个痛苦的时刻,他写道:“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就好像是上帝已经决定,让我只能再看一眼他为我选定的妻子。而我必须得说,我同上帝一样爱她。”
黄嘉略决定不再续弦,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学术工作和抚养小女儿中。为了纪念逝去的妻子,他的小女儿受洗时取教名为玛丽-克洛德。但他自己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情绪低落,与傅尔蒙的合作也进展缓慢。1715年6月,弗莱雷从巴士底狱中释放出来了,即使他在狱中仍然坚持汉学研究,他和黄嘉略也未能再次合作。弗莱雷有很多其他的研究兴趣,而他似乎也对黄嘉略和傅尔蒙的合作很满意,所以很快就把精力投入各种其他文明的语言和历史研究中去。黄嘉略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傅尔蒙似乎极其嫉妒黄嘉略和弗莱雷之间的合作,并将这两人的研究成果占为己有,以此继续开拓自己的学术生涯。但是,字典的编纂工作还在沿着偏旁部首的顺序缓慢前进,1716年秋天终于编到了“水”字旁,这是黄嘉略列举的二百一十四个偏旁部首中的第八十五个。黄嘉略和傅尔蒙还编写了供教学用的对话,是在标有注释的文学选段之外的补充材料。对话的内容活泼有趣,包括买卖商品、文人之间的谈话,甚至是两位学者露骨地讨论刚搬到邻舍的年轻貌美的女歌手。
1715年,老国王路易十四去世,黄嘉略以法国爱国者的自豪之情称赞路易十四的荣誉。他写道,正是这位已故的老国王,决定打开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从而激励着自己的学术生涯。现在,在摄政王时期,黄嘉略突然明白了自己的任务。他要写一部两卷本的巨著,将中国的一切介绍给法国社会。第一卷主要是语言学的内容,阐明汉语的语法结构,以及汉字书写如何通过不同方式达到上述效果——在西方,这主要是通过词尾、词形和语态的变化来实现的。第二卷主要是向法国读者介绍他们了解中国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关于中华帝国的确切知识”。黄嘉略对此得心应手,主要得益于他在前往欧洲之前在中国内陆广泛的游历。
然而事与愿违。1716年的夏秋之际,黄嘉略的身体一天天地虚弱下去,他似乎又陷入了生活拮据的困境中,他需要钱来支付房租、仆人、食物和小玛丽-克洛德的乳母玛丽·布勒(Marie Boulle)的工钱。他开始酗酒,买酒的钱通常是从当地放高利贷的犹太人那里一点一点借来的。为了增强体力,他还特意借钱买了新鲜的牛奶和鸡蛋。当他再次高烧的时候,正在编写字典的第一千一百四十页。在这个浩大工程中,他煞费苦心学来的语言第一次变得模糊。法语单词被写成了意大利语,意大利语被写成了拉丁语,拉丁语又被写成了法语。他工工整整地又写下了一个字,然后,无奈地放下了笔。
1716年10月1日,黄嘉略在伽奈特大街的住所中去世了,把小玛丽-克洛德留给了法国和她的外祖父母。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同意从1719年1月1日起支付小玛丽的教育费和抚养费。而在此之前,由外祖父母依靠黄嘉略留下的约四百里弗的遗产来抚养她。黄嘉略的葬礼非常体面(花费四十三里弗),人们在那个10月里共为他做了六次安魂弥撒,并安排此后再做六次。黄嘉略曾热切地希望小玛丽-克洛德至少能够活下去,来实现他的梦想,让中国和法国文化相融,增进相互的了解,但是在父亲去世的几个月后,小玛丽-克洛德也夭折了。中西交流的梦想之光,便也一闪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