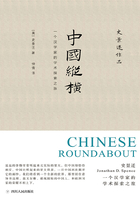
导言
“碰巧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克路士(Gaspar da Cruz)回忆起了1556年至1557年冬天在中国南方度过的日子,“我和几个葡萄牙人坐在馆舍门前河边的一条板凳上,几个青年正驾艇在河上游玩,弹奏各种乐器。我们听到音乐很高兴,就派人去请他们上我们这儿来,说要邀请他们一起玩乐。他们是豪爽的青年,乘艇而来向我们靠近,随后开始调拨乐器,直到我们高兴地发现他们调到没有杂声”。克路士和他的葡萄牙友人非常欣赏这群年轻人的音乐,便请求他们第二天再来演唱,带上几个歌手一块儿,尽管他们答应了,却没有来。不过,也许是看出了克路士的诚意,“有一个早晨,天刚亮,他们带着同样的乐器来为我们唱晨曲,因此没有完全令我们失望”。
从克路士的其他文字当中,我们知道,在等待年轻人来演唱期间,他的生活也并非完全没有音乐。他按照广东人的习俗买了两只夜莺,每天把煮好的饭包在蛋黄里喂鸟。这两只夜莺一雄一雌,被分别关在相邻的笼子里,鸟笼子也被罩起一部分,使得它们“彼此感知却不能相视”。这样一来,克路士欣喜地写道:“雄鸟沉浸在音乐中”,雌鸟与之呼应,啁啾歌鸣,“将寒冬腊月妆点得宛如人间四月天”。
回顾过往,我们大概也曾有过这种闲情雅致,可以从心所欲吧。克路士是多米尼教派的修士,前往广州传教,但成效不大。随后,他返回葡萄牙,一路上走走停停,到达里斯本时恰逢瘟疫蔓延,他加入了救援伤病员的医疗队,自己却于1569年死于这场恐怖的瘟疫。克路士用生命阐释了无私的精神,却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在他死后两周,1570年2月末,《中国志》出版,“详尽记载了中国事物及其特点”。这本二十九章的《中国志》,是西方出版的第一部详细描写中国的足本著作。
对于像我这种在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而言,克路士一直是我的榜样和精神激励。尽管一心传教,恪守教会习俗,还结识了不少葡萄牙冒险家,中文水平也相当有限,但克路士从未放弃他那宽大的胸怀,或丢掉写作过程中对精确与全面的平衡把握。对他来说,月光下的音乐和夜莺的歌声是中国故事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这种异国的生活也可能是残酷艰辛、令人困惑的。明知困难重重,克路士还是试图去抓住那些难以捉摸的因素,来描绘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他在序言中告诉读者,他的意图是“通过本书的叙述,人们可以揣摩那些至今未知之事”。 在克路士的阅历中,其他社会中“遥远的事物常常听起来比实际的要大”,但中国却“恰恰相反,中国比听起来的要大得多”。
在克路士的阅历中,其他社会中“遥远的事物常常听起来比实际的要大”,但中国却“恰恰相反,中国比听起来的要大得多”。
我在汉学研究过程中发现,克路士美中不足的是对于喜爱的事物评价过高,而我必须承认,这本论文集可能也会有过度热情或是轻率的折中。在汉学研究先辈中发现类似的缺陷,对我来说或许是某种安慰。这种安慰同样能在巴耶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身上找到。巴耶尔,1694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小城哥尼斯堡(Konigsberg),父亲是位画家。从中学到大学,巴耶尔通过正规教育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直到十九岁那年,突如其来的渴望促使他开始学习中文。巴耶尔之后在自传中是如此形容的:
1713年,当我还在乡下学习的时候,碰巧发生了一件事——我突然有了学习中文的强烈渴望。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工作着,思考着,甚至是幻想着,要怎样才能够穿进神秘的汉语世界中去。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够在这一领域取得小小的成就,我便会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孙,万王之王。像是一只怀孕的兔子,我把洞穴中的所有东西都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编辑成一本类似字典或是介绍中国语言文学规则的入门读物。![龙伯克(Kund Lundbaek)《汉学家先驱巴耶尔》(T.S.Bayer[1694-1738]: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and Malmo,1986年,第92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C2A41/13907311803050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209205-PdY9eO5Dhc9ueI18oUj7vprZiqsc9Khd-0-24f916df3eb21339e72ea882b6ff07fd)
经过在哥尼斯堡、柏林和圣彼得堡长达十七年的钻研学习,巴耶尔于1730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汉语博览》(Museum Sinicum),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本介绍中国语言的书籍。
在巴耶尔广博而漫长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汉语博览》是一份狂野而奇特的献礼。这部著作算不上成功,法国最负盛名的东方学专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而巴耶尔也在读到这些批评之后不久便去世了。然而,正如克路士一百六十年前对自己的书所做的那样,巴耶尔也试图公正全面地评价中国,尽管他对中国的认识有限。但道路上的困难总是令人生畏,甚至是无法逾越的。最初,巴耶尔完全不懂中文,只有从杂乱失真的材料碎片和粗制滥造的汉字摹本开始研究。身为新成立的圣彼得堡研究会的院士,他小有名气,也有些薪金,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大多数时候,为了解决简单的语言学问题,常常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通过通信来解决。
不仅如此,巴耶尔还继承了欧洲的东方学研究传统,试图寻找一把“钥匙”或是一本百科大全来一下子揭开汉语神秘的面纱:因此,错误的研究起点注定了死亡的结局。但是,正如巴耶尔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说,正是凭借他一贯的(有些玩笑意味)博识,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重担。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希腊人通过尝试攻下了特洛伊,世间一切皆靠尝试呀。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田园诗》(Bucolics)中,那位亚历山大的老妇人也是这样说的”。
在《汉语博览》的长篇序言中,巴耶尔回顾了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西方中国观的变化。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游历,到元朝崩溃、所有商路中断,“这个国家越来越遥远,像是消失在黑夜中的一颗星星”;但是一旦中国“再次揭开它的面纱,我们将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那里居住着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的中国人,和欧洲国家的荣耀不相上下”。
但是在他们的中国研究中,这些勇敢的学者和传教的先驱却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分析汉语本身。这种遗憾——对于巴耶尔来说是那么引人入胜和神秘莫测——激发着巴耶尔去弥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巴耶尔以平静的心态,研读着汉学先驱那些古怪晦涩、浩如烟海的成果;就好像是用前人的话,为他的研究洞穴的内壁不断添砖加瓦,他感到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满怀热情地全力投身其中。巴耶尔的索引,让我们看到了他试图综合起来的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例如,英国学者约翰·韦伯(John Webb),竭尽其学术生涯之所能,来证明汉语是世界上第一种语言,因而是所有语言之母;荷兰学者佛休斯(Isaac Vossius)盛赞中国的艺术和科学是世界之最,声称多么希望“自己是生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法国学者菲利普·马松(Philippe Masson)“证明”了中文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希伯来语,《旧约》中许多棘手的语言问题,都可以从中文当中找到答案——例如,上帝哺育沙漠之中的以色列子民的“吗哪”(Manna),不过是中文当中“馒头”(Man-tou)的变音;而对于瑞典学者奥劳斯·鲁德贝克(Olaus Rudbeck)来说(巴耶尔评价说奥劳斯能以“几乎恐怖的力量和冗长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中文是最接近哥特语的语言。但是在巴耶尔看来,即使他们的理论“模糊肤浅”或是让人“如坠云雾”,也不应该被轻易否决掉,因为在这些热情洋溢的理论背后,是先驱的“睿智和勤勉”。
巴耶尔试图在公正和荒谬感之间保持平衡,但在研究穆勒(Andreas Müller)时遇到了最严峻的考验。这位来自波美拉尼亚的怪人声称他发明了一种简单密匙(clavis sinica),可以让任何人在几天、至多一个月内学会汉语。但是,他不愿将之公开发表,而要找个买主以两千泰勒(德国旧币)的价格出售。但是穆勒没有找到买主,在去世前不久烧掉了所有的研究论文,其中也包括那个有名的“密匙”。在评价穆勒的学术成就时,巴耶尔承认穆勒过于“贪婪”,“捏造”材料来论证自己的结论,他的汉字写得“春蚓秋蛇”,翻译的中文也“过如秋草”,证明了所谓的“密匙”其实“毫无用处”。他还利用乐理知识构造了一套中文声调的理论,“似乎整个国家的对话是一场宴会上的歌曲——四度,八度,高八度”!但是,尽管如此,巴耶尔也不愿意完全否定穆勒的成果,就如同对待他所研究的其他学者的成果一样:因为不论曾遭受多么严厉的批评,穆勒的学术生涯还是展现了“尝试理解中文的执着热情和令人尊敬的创造力”。
在评价自身的研究成果时,巴耶尔用寥寥数语写道:“我给这本书起名为《汉语博览》,只是因为这是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名字,而我又找不到更好的词了。”关于这部著作的价值,巴耶尔认为,“不能由我来细究这两卷本的著作中都写了些什么,也不该由我来评价自己的成败——这应该交给读者来判断”。 即使在1738年,在得知法国学者埃狄纳·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轻蔑粗暴”地否定了他一生的研究成果之后,巴耶尔仍然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他对傅尔蒙教授的尊敬并没有因此“减少”:“我敬佩真正杰出而优秀的研究,即使出自我的对手甚至是敌人。”
即使在1738年,在得知法国学者埃狄纳·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轻蔑粗暴”地否定了他一生的研究成果之后,巴耶尔仍然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他对傅尔蒙教授的尊敬并没有因此“减少”:“我敬佩真正杰出而优秀的研究,即使出自我的对手甚至是敌人。”
现在我们的学术世界弥漫着各种字典、词汇表和参考文献,相较而言,我们也更容易接触中国和中国学者,巴耶尔和克路士的著作可能看起来不过像是满足好奇心的读物罢了。显然,巴耶尔并没有听说过克路士,在遭到傅尔蒙的否定之后也很少有人去读巴耶尔。这两位学者都很快被其他学者超越,后来者有着更广的涉猎范畴和更深刻的洞察力——或者,是拥有更加方便的出版途径。但是,我仍然更喜欢思考这两位学者,阅读他们的沉思,因为不久之后,我们也会被其他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超越。长年的研究和写作最终也会被证明是短暂而不足的。新的文献会出现,旧的文献会被重新评价;新的议题会吸引学者和读者;新的研究方法会淘汰旧的研究方法。正如巴耶尔不停地警示我们的一样,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控制的疯狂,所以做当下能做的事情,尽力研究,接受批评或是褒奖——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我们选择无所作为,不著、不评、不言己,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我们,但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保护,逃避了对真理的追求。如果沉默寡言,我们仍然可以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看护人,甚至可以安详地凝视着所有的一切,但却永远无法参与到最深刻的学术争鸣中去。
我脑海中浮现一幅景象,那发生在很久以前我与父亲的一次雨中漫步:父亲的小狗汤姆斯发现了一个兔子洞,它激动着狂喜着,前爪发疯一般刨着洞,泥土在它的后腿之间飞舞如云。我站在旁边,惊讶地看着这一切。泥土成堆,小狗狂吠,雨点淅沥,却不见兔子的身影。在汤姆斯喧嚣的进军中,兔子早已逃之夭夭,通过东边相邻通道撤离到僻静、安全的地方了。
也许这就是我探寻巴耶尔“洞穴”的凌乱的现代翻版。毫无疑问,我如同克路士一样,做了很多本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研究生涯中,我确实堆积起了不少泥土。我也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论文,这本书当中收录的是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反映了我尽可能精确、公正和透彻地思考中国的努力。 这本书的内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五个部分:中西文化交流、儒家理论和国家权力、中国的社会历史、革命中国以及对恩师的介绍。
这本书的内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五个部分:中西文化交流、儒家理论和国家权力、中国的社会历史、革命中国以及对恩师的介绍。
我把这本集子叫作《中国纵横》(Chinese Roundabout),部分源自对华莱士(Wallace Stevens)的敬意,长久以来,他的著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因为我喜欢“纵横”这个词语,它寓意着曲折而不失目的性,还寓意着(至少在英格兰,这个词类似于美国的“交通环岛”)以某种逻辑来厘清“辐辏并进”之脉络的努力。最为重要的是,这像是孩子们脑海中的“旋转木马”。孩子才是未来的鸿儒巨擘,他们膝盖紧贴着彩绘的木马,手中紧握着热烈的生命,在令人眩晕的风中甩着头,充满了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