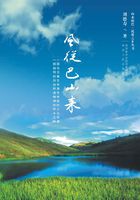
序一
文学与还乡
——读刘德寿《风从巴山来》
住在城里,心里时常虚虚的、慌慌的,也荒荒的,有时就走神,眼睛就忙起来,想为走神的、悬空着的心,找个停靠处,眼睛东瞅西瞅,瞅着的不是轮胎钢筋,就是水泥玻璃,或者就瞅到了钱,商品,各种各样为生存为名利奔走的鞋子、车子、帽子,有时竟不小心瞅着了车祸或盗印着世道人心的假币。目光,就这样硬生生被碰回来了,目光受不了太多的僵硬、势利和漠然。
是的,人的目光虽然是光的一种,但目光不同于金属之光和石头之光,目光是从心泉里发出的,目光是水做的,水生的目光天然地喜欢水,喜欢柔软,喜欢空灵,喜欢清远,喜欢温厚,喜欢青翠。人的目光遇到这些水性的事物,才愿意停靠,目光停靠了,心也就停靠了。心有了停靠处,就不虚了,不慌了,不荒了,就回到家了。所以,有人说,此心安处是我乡。
但是,我的眼睛很难在城市找到停靠处,心也就时常悬着,我的眼睛觉得对不起心,既未找到养眼之物,也未找到养心之境。眼睛只好钻进古书,去《诗经》那里,去老庄那里,去陶渊明那里,去唐诗宋词那里,寻找明月清风白雪,寻找小桥流水人家,寻找柳暗花明春风古渡芳草碧连天。但是,寄存在文字里的美好甚至美妙的古典意境,可以滋养和慰藉心魂,却无法包揽我们的全部人生。人生还需要鲜活,还需要当下,还需要参与。
于是,我时常回到乡下老家,走进山野深处,在横横竖竖的阡陌上来回行走,横横竖竖地把自己写进一首残存的田园诗里。可是,这横横竖竖的阡陌,今天清晨还能被你来来去去走成一个“正”字或“田”字,明天黄昏,或许那一横就没了,唯独一竖,或许那一竖就没了,唯剩一横,直直地硬硬地指向城市的方向、商业的方向和似乎很现代却也很迷茫的方向。唯独一竖,或唯剩一横,是难以写成“正”字或“田”字了。而我是多么喜欢那个安静端庄镜照天地的“正”字和那个方正温润、生长四季的“田”字啊。
是的,我们的老家故土,无论你对她怀着怎样深沉的情感,在今天,她早已仅仅是一首残存的田园诗了,或者干脆成了一个农产品生产基地了(而非诗意栖息地),无论你怀着怎样的对于田园诗意、对于农耕文明、对于故土情境的感念和缅怀,你也无法在被现代机械文明、商业逻辑和电子文化改写了的现代的大地上,在已经破损、碎片化、商业化、格式化的大地上,重现那完好的自然美景和古典诗意。因此,你的眼睛找到的,也多是临时的停靠处,而非永恒的栖息地,你那悬空的心,偶尔有了逗留处,却没有了恒久的栖息地。
这就是我的心或我们的心,为什么时常虚虚的、慌慌的,也荒荒的一部分原因。
虚虚的,慌慌的,荒荒的,这也是世界性的现代焦虑和疾病。这既是一个生存性问题,也是精神性问题。所以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很深刻也很忧郁地指出:被技术、工业、商业和消费主义文化彻底改写了也瓦解了的大地上,在堆满人造物和文化垃圾的现代世界,已呈现荒原化景象,大地已失去了大地自身,它已丧失了古典的安详和天然的诗意,已无法为惊慌的现代人类安魂和慰心,现代人类是失去原乡(故乡)的无根之人,是流浪者,是漂泊者。因此,哲学、文学和诗的责任,就是寻找失去的原乡,触摸神性和诗意消失的踪迹,为人心寻找回乡的路。也就是说,哲学、文学、诗做着一个共同的梦:还乡。
其实,真正的诗人、写作者,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还乡者。即便是被现代人追忆和神往的盛唐,生活在其中的当时的诗人们却并不以为梦想之舟已经在此靠岸,他们也在做着还乡梦,杜甫诗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是缅想着更古早的淳朴年月;李商隐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他是在无限怅惘的黄昏落照里,缅怀那深情纯洁的过往;而更早的孔子,一生都做着克己复礼的还乡梦,一次次梦见他崇仰的圣君周公,以至于晚年梦少了,他竟悲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是在回忆中发现的情绪。俄国诗人普希金说:那逝去的一切,将变成美好的记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索性就把小说写成了对生命的回忆:《追忆似水年华》。
我国历史久远而深厚,相较于我们短促的此生,过往的岁月几乎是永恒般的漫长,为一代代人们提供了足够丰厚的怀古、忆想、还乡的背景和资源,所以,我国以及东方古国的还乡梦大多都是退向历史、返回过去的;美国历史太短,仅二百多年,比一个高寿老人的一辈子略长一点,没什么可怀古、可忆想的,所以美国人的还乡梦就大不同于我们,他们的还乡就是到未来之乡去,到太空去,到银河深处去,到外星去,因此美国的未来神话、宇宙探索、太空文学就特别发达,他们是乘坐光速飞船做着一厢情愿的还乡梦。
不管以何种方式做着还乡梦,不管人们要还的乡是自然之乡、故土之乡,还是未来之乡、宇宙之乡,我以为人们追忆和渴慕的都是一种情义之乡、道德之乡、美善之乡,是一个能够化解焦虑、舒展身心、安放生命、慰藉心魂的生命的故乡和情感的故乡,是一个葱茏柔软温情的故乡。而我国作为一个悠久的农耕古国,五千年深的土壤里,积淀着太多太深的与乡土、山水、草木、生灵的生命血缘和伦理亲情,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基因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都铭刻着对故土田园老屋炊烟的牵挂和思念,都铭刻着对山水草木生灵的记忆和依恋,都铭刻着永难忘怀的乡情、乡风、乡恋、乡愁。
而在城市化战车步步紧逼,水泥大肆铺张和覆盖,大自然日渐被人工化、碎片化和资本化,几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纷纷沦陷的年头,人们的乡愁也就与日俱增,还乡梦就成了几乎所有人经常要做的梦。作为人类精神触觉的文学,作为多梦的写作者,我们的乡愁和还乡梦,在这个时代就显得尤为强烈、深切和浓厚。
作家刘德寿先生就是一位执着的梦游者和记梦者,他做的最多的梦是山水之梦、故园之梦、还乡之梦,这也是他做的最好的梦。与德寿认识、交往多年,读过他的不少文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些写班城沧桑、镇巴山水、故园情思的文章,他把深情的回忆和细密的眷顾,都寄托在那些陡峭而温暖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为了寻回梦中的原乡,他《穿越最后的净土》,抵达《那片古老的林子》,伫立《如心桥》,表达对《一条河的思念》;而那只刚刚从庄周梦境里飞出的《飞翔的蝴蝶》,引领他飞越狭小的生存笼子,驶向像梦一样美妙的与神性比邻的永恒之乡。但是,德寿虽怀着诗人的浪漫之梦,他更知道自己置身于实实在在的山水故土,置身于诗意和情义之间,置身于古典和现代之间,置身于缅想和担当之间,虽然,诗意可喜,古典可敬,缅想可爱,但是,山水需要情义之人,现代需要还乡之舟,故土需要担当之肩,所以,在德寿情思丰厚、血脉交织的文字里,既飘逸着他的浪漫诗情,也流淌着他的现实情怀。《南关·难关》《登苗乡大道》《还去贺家山》《寻访至宝塔》《拴马岭拾遗》《故乡的炊烟》《古坟湾》《故乡,一些远去的鸟儿》,仅读读这些题目,读读这些藏着无尽岁月的地名,都能唤起我们内心里与作者相似的连绵不绝的乡情和乡愁。
我此时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拿着这本集子做导游手册,请德寿做向导,去那些高山远水,去那些云村雾寨,逐个探访,看望我们的故乡,问候我们的乡亲,寻找并连接起我们的血脉之根和心灵故乡……
2015年7月15日 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