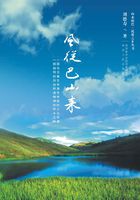
菜花·菜籽·菜油
是谁,将这十万颗鸡蛋凌厉地捣碎;又是谁,将这十万颗鸡蛋黄,齐普普地洒在了我故乡辽阔而丰饶的田野上,让那山川野岭,沟壑涧畔,瞬间变成了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浪般的涌来……
哦,那是油菜花海,是故乡春天里必不可少的油菜花海,那金黄金黄的油菜花海,火爆爆的油菜花海,招蜂惹蝶的油菜花海啊!
眨眼工夫,我这五十年的青春和生命就这么白白地浪费。五十年的风雨,五十年的功过,五十年的岁月里,我没有留下什么,没有携带什么,没有牵挂什么。当然,这是除了亲情,除了尊严,除了个性。除此,我留下的,可能只有这“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油菜花海了。
印象中,童年的油菜花海不是太大的规模。有时候,在干瘦干瘦的黄土地里和边边角角的自留地里,祖母也常带我们赏花,但那时候,我实在感觉不出这花海的本质和其开放的目的和意义。
后来,在我们懂事的时候,祖母依然会在每年的阳春三月带我们赏花。可那时候,我们已初涉人世。于是,人性的本能总会让我们自觉和不自觉地犯下一些低级性的错误。比如好奇、惹事、贪玩、捣蛋等等。这其中,悄悄地在自留地里或邻居家的油菜花地折菜条,是我们通常惯犯的错误。每每如此,祖母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和教诲,也不断地给邻居们赔情道歉。但祖母却从未因此而责罚过我们。虽然,这是祖母一生的淑范和美德。
问题是,不管那时或现在,即就是油菜花开堆满山冈的阳春时节,在几十年里,我们见过的油菜花儿,赏过的油菜花海,甚至在油菜花海扯猪草的那些年月,在油菜花海谈情说爱的那些季节,在油菜花海无所事事的那些落难的日子里,我们拂过的花朵,惹过的花瓣,折过的花骨,闻过的花香,何止海浪和千万。但那一望无际的花海,那蜜蜂嗡嗡的花海,那一波一浪的花海啊,它总是别无选择地、出于本分地、一年又一年地开放在故乡的原野上。
哦,那是故乡美丽的天堂,是故乡父老年年岁岁燃烧的希望……
面对浓浓而多情的油菜花海,我们的父老能有几许的希望,能有几重的盼头,能有多大的丰收把握,这完全取决于油菜花儿的密度和油菜花枝的骨骼。至于油菜花开的美学,油菜花开的意义,油菜花开在天地之间的生命奇迹,似乎永远与农人无关。而花开美不美,花开艳不艳,花开甜不甜,那不是农人切身利益的主流和所要关怀的终极思考。事实上,乡亲们对于油菜花儿的开放从没有过认真地思考,也没有过冷静地关注。他们认为,油菜花开太平常、太普通,太平凡不过了,油菜花开是自然现象,油菜要结籽,就必须要开花,开花是油菜天经地义的职责。至于花开几许,花开浓淡,油菜花开的过程,那不是农人非要问鼎的核心,农人的生存哲学很现实,他们只关注结果,只关注丰收的喜悦。
不可否认,我的血脉始终流淌着古老的农民基因。在祖辈父辈的劳动和无穷的生命体验中,我们看惯了春花秋月,赏惯了各种山花烂漫的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海的虚实和浓淡岁月。庄子在《应帝王》篇中借无名人之口所言:“汝游新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这是三重世界的共感与虚化:主体之心的淡化,自然元素性的混化,器物的再次自然化与共感。中国文化以其自然为中介的调节,顺应了虚化的原则。
面对中国文化之活化的自然性和虚淡的默化精神,我一直回味着油菜花开的自然与自由,回味着油菜花开的古意与梦境。尽量让油菜花开的自然化与我的自由书写性相结合,并从自然出发,重写中国文化自身的现代性,让油菜花开来唤醒自然的潜能,让美自然化,让油菜花海进入新的自然化的美学领域。
问题是,我的父老乡亲,我的童年和少年,那实在是不懂美学,也没有美学思维;不懂自然,又生活和经历过自然当中那些黄连树下弹琴,苦中有乐的艰苦历程。

那时候,不论是油菜花开,或所有的花开都是花开花落、自生自灭的大自然现象和杰作。不同的是,油菜花儿是农人们自种的家花。但它之所以不能引人注目,也提不起父老乡亲的兴趣和我那时候的怜爱与关怀,全是因了油菜花儿的混沌与淡漠。现在看来,它不清香,也不暗香,亦不冷香,还真是油菜花儿的个性使然。但它却特别地勾引着蜂蝶,以至于我们常常地被蜇得鼻青脸肿,防不胜防。这情况当然是我们不谙世事,就像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而我们却偷吃了菜条,又拈花惹草的结果。而那些山花,也包括春风一家的桃花李花和杏花,尤其那同样招蜂惹蝶的甜甜的野刺梅,它们香得出奇,香得醉人,香得惊心,香得勾魂;但它们总是昙花一现,青春短暂而已。而我故乡的油菜花啊,他们不亢不卑不香,虽然梅开二度甚至三度,让它的花期格外地慢长。
对此,这花心花蕊花荣花貌,我无法理喻。直到懂事的时候,我才听父老乡亲们说:油菜花儿不香,是因为它是家花;刺梅花儿不长,是因为它们是野花;这就是说,家花没有野花香,但野花却没有家花长啊!
对于油菜花儿,我不羡慕、不嫉妒,但我也不鄙弃、不抵触。许多人看重的是油菜花海的金黄与壮丽。赏的是花,却浮浅了油菜花开的灵魂和品位,更浮浅了油菜花开的自然属性和美学精神。而我看重的是结果,看重的是成熟,看重的是油菜花海最终的奉献和希望。更看重油菜花开的孕育和其生命的忍力耐力和坚强……
于是,我想起尼采的经典命题:“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与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这个遥远的话题,总让我想起晚年的老祖母,在一些阴雨连绵的暮春天气,在油菜籽儿即将收割的四五月前后,或在阴雨连绵正值油菜播种的深秋时节,祖母的周身总有一些隐隐的疼痛,尤其祖母的那双手,仿佛被岁月的沧桑烘干的古木,虬枝错节,伤痕累累,青筋凸突。那双手啊,还真像即将收割后的油菜翻炸裂口,不忍目睹。我知道,那是祖母终身劳作的结果,尤其秋天,祖母把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小得不能再小的油菜籽儿播种在老屋的自留地里,泼上几瓢圈肥,覆上几锄泥土,就任其吐蕾、发芽、生长。说来也怪,寒冷的冬天,白雪覆盖,冰霜凛冽,这稚嫩的新芽,脆弱的生命却非常地顽强,它不仅耐得住寒冷,遇上瑞雪,它还更加蓬蓬勃勃地壮硕和生长,并在白雪的覆盖下,静悄悄地去做绿色的梦、温馨的梦、丰收而甜美的梦啊!
这就是故乡的油菜,一枚精致而典雅的油菜,生命力极其坚强而又青春旺盛的油菜啊。祖母说:油菜花儿的凋谢,相比于其他花种的衰败要来得慢一些。它之所以慢长,甚至几度开放,是因为孕育的过程重要,花越旺,花期越长,“籽粒越饱满,品种越优良,油量越丰沛。”当然,祖母没有说出这么富有诗意而浪漫的语言。祖母的原话是,油菜花儿开得越好,油菜籽儿就越繁茂,油量也就越多了。可见,祖母携我们在油菜地里劳作,她不是为了赏花,而是为了生计,为了生存的理由,为了儿孙的成长着想。
这就是祖母和故乡父老的生存哲学。
于是,一粒菜籽,两粒菜籽,十粒菜籽,百粒、千粒、万粒菜籽,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菜籽向我们涌来。这时候,我掬起一捧菜籽,就有可能捧起了一个军队;而我扛起一袋菜籽,就有可能扛起了一个民族。这种结果,这种胸怀,这种境界,完全是出于对于菜籽的典雅而精悍的崇拜和图腾。问题是,你千万别嫌弃了菜籽的小巧和玲珑,这小小的籽粒,它完全是一个宇宙的缩影。这是因为,那些相吸相斥相容,而又相安无事的菜籽,就像宇宙的星球,在遥远的银河岸边和遥远的宇宙深处,星星们就如同菜籽,在大宇宙的和谐统一下,把阳光、风雨、氧气供给了自然,供给了人间。而我故乡的菜籽,它们用细胞式的组合,用小人国的身体,用其圆润精湛的姿态,生死轮回,亘古不变,完成了由菜籽到发芽、开花、结籽、出油的生命历程……
我第一次打油,是在故乡狭壑深处的一个叫作崔家扁的穷山沟里。那地方,山势拥挤,河流蜿蜒,狭河幽绝。大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揪心境界。但是,你若稍不注意,要是流落在这样的狭河里,你会无可奈何地生畏、失落,甚至绝望。
但就是这样的河湾,这样的大山沟里,故乡唯一的土法上码的榨油机作坊,就坐落在一个悬崖峭壁的山畔畔上。
畔畔上,有一排长三间两头转的青瓦房,瓦房的侧边,靠近悬崖的山边边上,是一排简易的木栏栅房。在这里,我第一次领略和欣赏了榨油现场那排山倒海的生命序曲,那像喝了《红高粱》酒,敢走青杀口一样的榨油机厂那波澜壮阔的雄浑和澎湃。
至今想起来,那场面简直是在虎口夺食,是在生死场上,我的农二哥们用生命的较量,甚至是在用血和泪的控诉,换取我生命中和故乡父老在那个年代难得饱和的油量……
菜籽被少量的清水浸泡,然后捣碎,再用稻草包裹。通常有一尺见方或脸盆一样的圆盘。二哥们将这些圆饼镶在铁箍里,铁箍装在一个高大的木制井架上,圆饼的高度在人的腰部,而井架却高大无比,粗壮的木头,仿佛远古的战神,战神的使命,就是托起那千斤重担的木杵,木杵被两股壮实的钢绳揽住,紧紧地拴在那高大的脚手架上。这时候,一声号子吼起,四名力大汉子粗的中年男人,他们光着膀子,赤着脚板,赤着那同样似菜籽壳一样翻炸裂口的脚板,伴随着号子的节奏和起落,四条汉子同时吼起了号子:“嗨咗嗨咗、嗨咗嗨咗……”和着号子,他们蹬起八字步,舞动那千斤重担的木杵,一齐枉命般的撞向那滚圆的铁箍,在碰撞的瞬间,汉子们却利索地同时撒手,眼明脚快地散开,利索地退向两边。这时候,一声巨响,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号子响起,不断地巨响和着巨响,那笨重的脚手架上,力与力的摩擦,人与物的较量,不断地巨吼和碰撞……
整个过程,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惊心动魄。一阵阵心魂,早已随着汉子们雷厉风行的奔腾和排山倒海的碰撞,软了,软了……
端午节前夕,祖母总要把家里唯一的几十斤菜籽让我们弟兄姊妹背去打油。那时候,我们全家一年的收获也就百十余斤油菜。至于稻谷小麦之类的主粮,若要是平均下来,靠挣工分吃饭的大锅饭时代,家里的收入比例就更少了。因为,除了剩余部分,大多数的口粮都上交了国家,是所为的公购粮之类的摊派任务。这就常常让我们青黄不接甚至家贫如洗。而唯一的一头年猪,也要上交国家半条。我们一家上有老、下有小,祖孙三代十多口人,每年的口粮和油量几乎是微乎其微了。
那一次,大概是我十三岁那年的七月十二日中午,我和村里还有邻居的放牛娃们第一次出远门,去完成祖母牢牢交办和千叮咛万嘱咐的艰巨任务。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是我们改善生活的又一个传统节日。在南方,端午节吃粽子是乡亲们的共同习俗。而在我们的陕南大巴山区,端午节的主打菜谱就是我们用菜油炸出的“面疙瘩”。后来,我才知道,这“面疙瘩”实际上就是故乡后来逐渐兴起的“豆酱油条”的老祖父。
犹记得,那是故乡的榨油机厂最为鲜活热闹和最为繁忙的一天。远近山民蜂拥而至。虽然,邻近的乡亲们早已在农闲时节备好了菜油,但更多的山民们,却是把或多或少的菜籽提前寄存在榨油机厂,再由油厂主人在闲时和早晚天气自行安排榨油。于是,油厂的周围,房前街檐,那些背篓,那些蛇皮口袋,那些油瓶,还有盛油的竹筒,也有条件较好的塑料桶,还有复转军人从部队带回的军用水壶。那些东西随随便便地堆放和寄存,却从来少有混乱和丢失。不像现在,富裕时代,人们反而增强了戒备心理。物质匮乏的贫穷时代,人们相互体贴和信赖,谁忍心去占别人的便宜呢?现在,一些富人真是越有越熊。莫说体贴、信赖,倒是嫌贫爱富的社会风气,已把我们这一代人滑向了更为贫穷的物质和精神领域……
随着木杵的起落,铁箍不断地加榫,油饼不断地紧缩,不断地变薄,稻草完全融合进油饼里。然后,一声巨响,又一声巨响,接二连三的巨响,木榫越加越多,油饼越来越薄。这时候,几条汉子汗流浃背,凶猛异常。但是,我也看到,随着那四条光膀子男人的汗滴,我的油饼,那稻草包裹的油饼,在力的作用下,也开始了汗流浃背,一滴、两滴、三滴。一声巨响,两声巨响,三声巨响。“咳咗、咳咗”,点点、滴滴。这时候,油饼越来越薄,巨响越来越快,随着最后的一声巨响,接着一片喘息,几条汉子仰躺在地,木杵停下来,油饼静下来,点滴细若雨丝,最终停止了泣滴……
这就是一粒菜籽的命运,奉献了花海,奉献了美学,奉献了生命,奉献了全部,最终化为死一样的沉静。沉寂的过程,是千锤百炼的撞击,是赤裸裸的奉献。是身体和生命的全部。
我的菜籽,榨出了金黄金黄的菜油。干枯的油饼散落一地。根据事先承诺,我将祖父用旱烟换取的三块五毛钱角票,油腻腻地掏给了主人。这时候,天已完全黑下来,整个河湾像一口锅扣在了天幕上。对此,在主人的盛情叮咛下,我们捆上了柏皮火把,在邻居幺叔的带领下,没入漆黑的夜晚,在深深的长河中,过迷水洞,上李家坝,沿着羊肠小道的严家坪斜坡,爬上高高的放场坪,这时候,我们才最终轻松下来,看到了一些河湾的灯火,也感到了在普子垭豁等候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油炸面疙瘩,油炸土豆丝,油炸鲜豆腐,还有故乡的油条和金黄色的洋芋夹。同是一种颜色,同是一种清香,同是一种酥酥的感觉,同是一种蛋黄的惹眼,同是一种地道纯正的美味。但它们的诱惑却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是,这些地地道道的农家乐,在那些年月里,我们只有在屈原夫子的祭日里,才能够无拘无束地饱餐和品尝……
四十年后的今天,故乡的榨油机厂已不复存在,老屋也不复存在。而更为可悲的是,我的亲人的族群里,祖父走了后,祖母跟着就走了,母亲不久也走了,之后长嫂又跟着母亲无情地走了,尤其是我终生难忘而又苦难凄凉的幺妹也走了……每每想起逝去的亲人,我的心、我的魂就像是无数条汉子在不断地撞击,不断地撕裂,总是在滴血的疼痛。
幺妹啊,亲人们,你们现在在哪里?
四十年来,我一直这样的呼唤,但渐渐地,幺妹不断地远去,亲人们也不断地走了,又不断地远去。但他们是不是忍心,是不是结伴或孤独地远行,我不得而知。但他们却不能像油菜花那样,待到来年,带到春风又绿大巴山的时候,逝去的油菜花儿又会回到我们的身边。可是人呢?我的亲人们呢?他们却不如一朵油菜花的起死回生,他们说走就走了,而且是一去永不回头……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老家,生活刚有好转,用油也较为方便。不像祖母在世的时候,总是顾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实在没法,祖母就用猪皮抹抹锅底,用漆油充当油料。漆油是山里的漆树结的一种花籽而熬制的油料,炒菜前,待铁锅烧红的时候,祖母便将豆腐块一样的漆油乳白色的漆油在锅底几抹,油花便晕化开来。但炒出的菜,要是在冬天,会很快凝成一坨,遇上不适应的人群,如果过量地食用漆油,就会浑身发痒,并很快出现一些红肿的斑块,那是漆树过敏而导致的结果。但那些年里,漆油焖土鸡倒是一道香喷喷的美食,记忆中,我生平曾有过一两次的享受。
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情况,我深深难忘。就是每逢年节,或清明,或端午,我们如果能够炖上一顿腊肉的话,那浮在汤菜表面的油花或冬天里结成的油块,纵然是水上浮油花,有油也有限吧,但汤上的浮油一定会被祖母轻轻地刮起,然后用于我们一段时期的油料来源。至今想起来,祖母操持这个家务实在不易,但她总在想方设法,精打细算,重复地计算着日子的久远和日子的艰难。而反观现在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我们真应该好好反思。
对此,我故乡的菜花,故乡的菜籽,故乡的菜油,那是绿色环保的净土,是故乡朴素而简单的生存哲学,是人们在关注花海摇醉花海的闲暇之余,故乡儿女对这片净土难能可贵的平安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