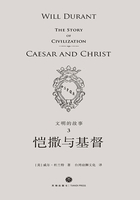
第一章 埃特鲁斯坎人序曲(公元前800—前508)
意大利
山谷中点缀着寂静的小村庄,山坡上展现着广阔的牧场,群山环抱有如高举的酒杯,处处湖泊有如杯中的佳酿,绿色的田野、黄色的麦地向碧海之滨伸展。村落、小镇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倦怠慵懒,然后又蓦然复苏,生气活泼,热情奔放。即使较大的城市之中,虽然尘土飞扬,但每一件事物,从小平房到大教堂,看起来都是那样美——这就是2000年前的意大利。因此,即使那落笔平实、不嗜雕饰的老普林尼(elder Pliny)提起他的祖国,都要说:“普天之下,走遍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如此的美。”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歌颂道:“此处四时皆春,即使炎夏也没有暑气。每年牛羊繁殖两次,树木结果实两回。”在帕埃斯图姆,玫瑰每年两度盛开;在意大利北部,有许多像曼图亚一样的肥沃平原,在那些地区,“有许多生满绿草的溪流,正是天鹅繁殖之地”。沿着这个大半岛,亚平宁山脉好像一条脊骨,为半岛西部遮蔽东北风。地面上分布着无数河流,滚滚地流入那些迷人的海湾。在北方,有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其他三面皆有水环绕,有很多悬崖峭壁。这块陆地,正是勤奋的人民易于得到报酬的地方,而其伸入地中海上的战略地位,又注定了他们统治古代世界。
这些山地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死亡,因为不时的地震与火山爆发,使多个世纪的辛劳变成了灰烬。但是,此处的死亡通常却是生的礼物,其熔岩混合着有机体,使百代后都享受其丰沃的土地。半岛上有一部分地形太过陡峭,还有一部分满是瘴气沼泽,均不宜耕种,而其他地方则十分肥沃,从而使希腊著名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对古代意大利食物的丰富和价廉大为惊叹。他暗示,意大利农作物收获的量与质,可从其人民的活力与勇气判断出来。剧作家阿尔菲耶里(Alfieri)认为,在人与庄稼的关系方面,意大利比任何地方都好。甚至在今天,那些魅力十足的意大利农民的热情——他们结实的肌肉,迅速转变的喜怒,以及他们燃烧似的眼睛,还会使胆小的学生受惊。在马略、恺撒及文艺复兴时代,曾使意大利伟大,也曾使其自行破裂的骄傲与愤怒,迄今还保留在意大利人的血液中,只等待着一个大好理由或争辩而爆发。这里的每一个男人都刚健而英俊,每一个女人都美丽、健壮而勇敢。“意大利母亲”(The mothers of Italy)3000年来所孕育的天才朝代,有什么国度能与其媲美?没有其他国家能像意大利一样,长时间地作为历史的中心——最初是政治,其次是宗教,再其次是艺术。自政治家加图(Cato)到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历时1700年,罗马一直是西方的中心。
亚里士多德说:“据最善于判断那个国家的人指称,当意大利人做了欧埃诺托里亚(Oenotria)的国王后,那里的人民就不再称欧埃诺托里亚人,而自称意大利人了。”欧埃诺托里亚位于意大利半岛靴部的足趾处,那里葡萄遍地,故有欧埃诺托里亚之名,意即“葡萄酒之地”。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说:“意大利人是西西尔人(Sicels)之王,他们在占领欧埃诺托里亚后,即征服了西西尔,而称该岛为西西里(Sicily)。”正如罗马人称所有希伦人(Hellens,即希腊人)为希腊人一样,希腊人最初只有少数人从阿提卡(Attica)北部移民那不勒斯(Naples),称当地人为意大利人。以后渐渐地,波河(Po)以南的所有半岛人民,都被希腊人称为意大利人了。
毫无疑问,意大利的许多故事已经销迹于地下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告诉我们,至少在公元前3万年,意大利那些平原就已有居民了。在公元前1万年至前6000年之间,又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一种古代传统上称为利古里(Liguri)及西西利(Siceli)的人种,长长的头型,形似粗陶器,穿着线状的服饰,用磨光的石头做工具和武器,来驯养家畜、打猎、捕鱼及埋葬死者。有些人居住在洞穴中,其他的人则用篱笆和涂料构筑圆形茅屋居住。这些圆形小屋的构造不断发展,以至于有建筑在帕拉蒂尼山(Palatine)上的圆形“罗慕路斯之宫”(House of Romulus,罗慕路斯为古罗马的建国者),建在广场(Forum)中的维斯塔神庙(Temple of Vesta)及哈德良陵墓(Mausoleum of Hadrian)——今日的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 Angelo)。
约公元前2000年,来自中欧的一些部落侵入——据推测这不是第一次——意大利北部。他们把其建筑风格带了进来,把村庄建筑在水中的木桩之上,以防野兽或人的攻击。他们主要定居在加尔达湖(Garda)、科莫湖(Como)、马焦雷湖(Maggiore)及其他美丽的湖上。时至今日,这些迷人的湖仍然吸引了许多外国观光客。后来,他们逐渐向南迁移,由于南方湖少,才把房屋建筑在陆地上,但仍以木桩为屋基。他们在其居住地四周筑垒掘壕,这个习惯传下来,便形成罗马军营与中世纪城堡的特色。他们放牧马牛,耕种土地,织造衣物,烧制陶器。意大利在新石器时代之末(约公元前2500年),以青铜铸造了上百种的工具和武器,包括梳子、发夹、剃刀、钳子以及其他创始年代不明的器具。他们把所有废物堆积在村子四周,后人因其具有肥沃的潜能,遂称他们的文化为“terramare”,意思是泥灰土。据我们所知,他们就是意大利人的直系祖先。
在波河流域的这些后裔,约公元前1000年向日耳曼人学会了冶铁,制造改良的器具,并以博洛尼亚(Bologna)附近的维拉诺瓦(Villanova)为中心,以其铁器为武装,推广他们的维拉诺瓦文化(Villanovan culture)。我们或可相信,其后的翁布里亚人(Umbrian)、萨宾人(Sabine)和拉丁人(Latin)的血统、语言及主要艺术,皆由此而来。后来,约公元前8世纪,又有一个新的移民潮到来,他们征服了维拉诺瓦人,在台伯河(Tiber)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奇特文明。
埃特鲁斯坎人的生活
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也是历史上的难解之谜。他们统治罗马百余年,遗留给罗马的影响甚为深远,不了解他们就很难了解罗马。然而,罗马的文学却闭口不谈他们,好像一个高贵的夫人极想在大家面前忘记其青春时代的浪漫一样。正如意大利的学者所提供的,他们的文化是以埃特鲁斯坎人的遗迹为基础;而在诗歌、戏剧及历史方面,也有许多“已逸文学”(lost literature)的征候。但是,其语言迄今仍只有少数几个字能够认出,今天的学者们对于埃特鲁斯坎人的神秘,比商博良(Champollion)以前对法老时代的埃及所知还少。
因此,埃特鲁斯坎人究竟是什么人、何时以及从何处而来,迄今仍是争论的话题。也许旧的传统已经被人太轻易地抛弃了。而那些卖弄学问的人,喜欢否定非正史流传下来的公认事实。希腊史学家和罗马史学家,绝大多数人都假定埃特鲁斯坎人来自小亚细亚。他们的宗教、服饰及艺术,有许多部分暗示着一种来自亚洲的特色;但也有许多部分,则是出自意大利本土。埃特鲁里亚(Etruria)的文明很可能是维拉诺瓦文化的一个支流,在商业上曾受希腊和近东的影响。然而一如大家所相信的,埃特鲁斯坎人本身,则是来自小亚细亚——可能是吕底亚(Lydia)——的入侵者。不管怎样,他们超强的杀戮性,使他们成了托斯卡纳(Tuscany,罗马北方的地区)的统治阶级。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何处登陆,只知道他们发现、征服及发展了许多城市——不再是以前那种用泥和草筑成的村庄,而是有围墙的小镇,按几何图形划定的街道。他们的房屋也不再是用泥土,而是用烧硬的砖或石头筑成。他们的12个社区,组成一个松弛的埃特鲁斯坎联邦(Etruscan Federation),由如下几个城市支配:塔奎尼乌斯(Tarquinii,今科尼多,Corneto)、阿雷提乌姆(Arretium,今阿雷佐,Arezzo)、帕鲁西亚(Perusia,今佩鲁贾,Perugia)及维爱(Veii,今伊索拉,Isola)。 然而由于山地及森林阻隔,彼此之间交通运输困难。各个城市的人民像希腊人一样妒忌好战,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独立城邦,很少团结对外。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安全,每逢其他城邦遭受攻击时,往往袖手旁观。于是,这些城邦一个接一个地都被罗马征服了。但是,这些同盟城市在公元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形成了意大利半岛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包括一支组织精良的陆军、一支著名的骑兵及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至于有一个时期统治了迄今仍被称为第勒尼安海(即埃特鲁斯坎,Tyrrhenian Sea)
然而由于山地及森林阻隔,彼此之间交通运输困难。各个城市的人民像希腊人一样妒忌好战,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独立城邦,很少团结对外。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安全,每逢其他城邦遭受攻击时,往往袖手旁观。于是,这些城邦一个接一个地都被罗马征服了。但是,这些同盟城市在公元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形成了意大利半岛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包括一支组织精良的陆军、一支著名的骑兵及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至于有一个时期统治了迄今仍被称为第勒尼安海(即埃特鲁斯坎,Tyrrhenian Sea) 的全部水域。
的全部水域。
埃特鲁斯坎各城邦的政府,也像罗马一样,最初是君主政体,以后变成了一些“头等家族”(first families)组成的寡头政体,渐渐地又给予有产公民组成的议会以每年选举官员(magistrates)之权。就我们所能理解的墓地绘画和浮雕来看,那完全是一个封建社会,土地属贵族所有,维拉诺瓦农奴及战争所俘的奴隶从事耕种,所有剩余产品皆供贵族地主奢华享受。他们通过训练,在森林与沼泽中开垦了托斯卡纳,并发展了一套农村灌溉与都市暗沟排水系统,这在同时代的希腊是没有的。埃特鲁斯坎的工程师们开山凿石,建筑排水隧道,以排泄过多的湖水,并建筑有排水沟的大道。早在公元前7世纪,埃特鲁斯坎人的实业是开采西海岸的铜及厄尔巴岛(Elba)的铁,铁矿石运到波普洛尼亚(Populonia)熔解,再将生铁在意大利全岛出售。埃特鲁斯坎商人进出于第勒尼安海上,从事贸易,从北欧下至莱茵河及罗讷河地区,越过阿尔卑斯山,带回琥珀、锡、铅及铁,并在地中海的每一个重要城市出售其产品。约公元前500年,埃特鲁斯坎各城市各自发行货币。
埃特鲁斯坎人在其坟墓中刻绘自己的像:粗矮结实、大头,差不多完全是阿纳托利亚人(Anatolian)的容貌,肤色是红的,特别是妇女的肤色。但是,他们擦胭脂的历史则与文明一样古老。女人以美丽著名,有些男人的面貌也很斯文高雅。其文化已发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因为在他们的坟墓中,曾经发现过补假牙架子的样本。他们的牙科医术也像医学及外科手术一样,自埃及和希腊输入。男女都留长发,男人很喜欢蓄须。他们的衣服仿效伊奥尼亚人的式样,内衣像古代希腊人的袍子,其外袍后来就变成罗马人的礼服。男女皆爱好装饰物,因此他们的墓中有很多珠宝。
如果我们从坟墓中画像所表现的快乐来判断,埃特鲁斯坎人的生活也和克里特岛人一样,以战斗而坚强,以豪华而柔和,以节庆赛会而快活。男子参与战斗,干劲十足,并从事各种男性运动。他们打猎,在竞技场斗牛,沿着危险的赛程驾驭战车,有时候是四马并驾的车子。他们投掷铁饼和标枪、撑竿跳高、竞走、摔跤、拳击以及格斗。这些比赛都很残酷无情,因为埃特鲁斯坎人也像罗马人一样,认为使文化进步到离兽性太远,是极为危险的。不够英雄气概的人则挥舞哑铃、掷骰子、吹笛子或跳舞。坟墓中的画也描绘着饮酒狂欢的情景。有时候也举行只有男人参加的酒会,也有醉后交谈的各种姿态。然而,时常总是男女同在,穿着富丽的服饰,成双成对地靠在漂亮的长椅上,或吃或饮,旁边由奴隶伺候着,有舞蹈和音乐助兴。男女偶尔也以色情的拥抱来点缀席间。
在这种场合出现的女子,可能是高等妓女,相当于古希腊的艺伎(hetaira)。如果罗马人的传说可信,埃特鲁斯坎的少女也像希腊属亚洲及日本武士时代的少女一样,获准以卖淫获得她的嫁妆。在普劳图斯(Plautus,古罗马喜剧作家)剧中的一个人,控告一个少女“以托斯卡纳人的方式出卖皮肉而获致婚姻”。可是,在埃特鲁斯坎人中妇人的地位很高。绘画上所表现出来的,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女人都很突出。其亲属关系可从母亲考察出来,使人再度想起亚洲血统。教育并不限于男性,因为塔奎尼乌斯首任国王的夫人塔纳奎(Tanaquil)除精通政治权谋外,也精通数学和医学。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曾认为埃特鲁斯坎人属于公妻社会,但是,没有遗迹留传下来,以证实这个柏拉图式的乌托邦。那些图画有许多都是描写夫妇和谐与家庭生活的场景,孩子们在左右做着顽皮的游戏,快活天真。
其宗教对消极的道德,极尽讽刺之能事。埃特鲁斯坎人的万神庙,以其充分的装备来吓阻日益增长的自我主义,而使家庭的责任易于履行。最大的神是掌管雷电的丁尼亚(Tinia),在其左右,有“十二大神”,好像一个委员会,无情地执行丁尼亚的命令。这些神太伟大了,谈及他们的名字是犯渎神罪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必提他们的名字)。特别可怕的是地狱的男女主神曼图斯(Mantus)和曼尼亚(Mania),各有一群有翅膀的恶魔为其执法。最不易满足的是命运女神拉莎(Lasa or Mean),手里舞着蛇或剑,用铁笔和墨书写,用铁锥和钉子固定,以执行她的毫不通融的命令。比较愉快的是拉瑞斯(Lares)和珀那忒斯(Penates)——置放在炉边的两种小神像,象征在家和出外的神灵。
以研究羊肝或飞鸟断定未来的卜巫术,可能是巴比伦人传给埃特鲁斯坎人的。但是,依照他们自己的传说,此事是一个圣童启示他们的。这个圣童是丁尼亚的孙子,他从一个刚翻过的畦沟里出生,就以圣哲的智慧开始说话。埃特鲁斯坎人的最高祭礼,是以一只羊、一头牛或一个人作为牺牲。作为牺牲的人,或被斩杀,或在大葬礼中被活埋。有些时候将战俘屠杀,作为神前的一次赎罪。因此,在阿拉利亚(Alalia)俘获的腓尼基人,便在卡西里(Caere)的会堂被石头打死。公元前358年所俘虏的约300名罗马人,则在塔奎尼乌斯成为献祭品。埃特鲁斯坎人显然相信,他们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可以从地狱中解救一个灵魂。
埃特鲁斯坎神学的最得意之处,在于对地狱的信仰。我们在其坟墓画像中所见的死者的灵魂,被守护神带往地府法庭,在那里进行最后审判,给他一个为生前行为辩护的机会。如果辩护失败,他就被判有罪,要受种种折磨,其痕迹留在维吉尔的作品中、早期基督教的地狱观念中,且借但丁的《地狱篇》流传了2000余年。好人不会受到那些惩罚,被罚者的痛苦也可因其活着的朋友的祈祷或牺牲而得以减轻。已被拯救的灵魂,从地狱升到天堂,在那里享受着墓中图画所描写的欢乐与豪华的神仙生活。
对于死者,埃特鲁斯坎人通常都予以埋葬。那些有钱人家的死者,则被安置在赤陶做成或石头雕成的棺材里,棺盖上刻绘着一部分像死者、一部分像古希腊阿波罗神的微笑人像。这方面,是埃特鲁斯坎传统对中世纪艺术的又一贡献。有时也将死者火葬,然后将骨灰置于瓮中,骨灰瓮上也绘有死者的画像。在许多例子中,骨灰瓮和坟墓都模仿一幢房屋。有时,坟墓是自岩石中凿开的,分成几个房间,放置一些家具、餐具、花瓶、衣服、武器、镜子、化妆品及宝石等,作为其死后生活之用。在卡西里的一座坟墓中,一个战士的骨骼,躺在一张保存得极为完整的铜床上,床的旁边还摆放着武器和战车。在其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有女人的装饰品和珠宝,那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妻子。那堆曾是她可爱身体的灰尘,仍旧裹在她所穿的婚袍之中。
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
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差不多就是我们所知的埃特鲁斯坎人历史的全部。我们可从其艺术中,探索其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宗教与阶级的权力,以及其与小亚细亚、埃及、希腊、罗马之间经济与文化接触的消长情况。这是一种受宗教习惯束缚而由其熟练的技术加以解放的艺术,它反映出一种野蛮和蒙昧的文明,却表现得很有特色和力量。伊奥尼亚、塞浦路斯及埃及等东方人的影响,支配了埃特鲁斯坎人艺术的初期形式和风格,而希腊的特征则支配着其后期的雕刻和陶器。在建筑和绘画、铜像及金属制品方面,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不但有其自身特色,而且不同凡响。
他们的残存建筑物,只是一些碎片或坟墓。埃特鲁里亚城的城墙依然存在——由没有黏合的石块砌成的厚墙,石块接合得很好,也很坚固。埃特鲁斯坎富人的住所,阐释了意大利房屋的典型设计:一个令人无法接近的外围墙,一个内部中庭或接待室,中庭屋顶有一部分是露天的,让雨水落在下面的水槽中。中庭四周是一些小室,对面通常是有支柱的门廊。罗马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曾描述过埃特鲁斯坎人的寺庙,他们的坟墓有时也采用寺庙的形式。大体说来,他们是仿效希腊模式,但托斯卡纳式修改了多利安式,柱子上没有凹槽和柱基,内堂设计的长宽比例为6∶5,而不是较为雅致的雅典派6∶3的关系。一个砖砌的内堂、一个石砌的列柱廊、木制的楣梁与山形墙、陶瓦上的浮雕和装饰,整个内堂置于一个奠基上或台地上,内部和外部都画得很辉煌——这就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寺庙。至于非宗教性的大建筑——如城门与城墙,沟渠与排水设施——据我们所知,拱门与圆顶是埃特鲁斯坎人介绍给意大利的。显然,这些庄严的建筑形式是从吕底亚带来的,而吕底亚则学自巴比伦。 但是,他们并没有仿照这个漂亮的方法,即覆盖广大空间而没有竖柱其间,以及使用沉重的楣梁。因为他们大部分还是运用希腊人的旧方法进入凹槽之内,而留给罗马去完成拱形建筑革命。
但是,他们并没有仿照这个漂亮的方法,即覆盖广大空间而没有竖柱其间,以及使用沉重的楣梁。因为他们大部分还是运用希腊人的旧方法进入凹槽之内,而留给罗马去完成拱形建筑革命。
埃特鲁斯坎人最著名的产品,是他们的陶器。每个博物馆都有很多这种陶器,使置身于陶器厅的疲惫的航海者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最完美的制作,不知为何未收集那些存品。埃特鲁斯坎人的花瓶,除了明显模仿希腊式的,大都设计平庸、技艺粗糙,其装饰看上去非常野蛮。没有任何民族的艺术产生过那么多人体的扭曲、可怕的面具、奇怪的野兽、凶恶的魔鬼及恐怖的神祇。但是,其公元前6世纪的黑陶(bucchero nero),则具有一种意大利式的活力,也许是代表着维拉诺瓦风格的发展。在乌尔奇(Vulci)和塔奎尼乌斯两处,曾经发现过精美的花瓶——从雅典输入或模仿安提卡式的黑色图样。弗朗索瓦花瓶(François Vase)是一种大油罐,是那个名叫弗朗索瓦的法国人在丘西(Chiusi)地区发现的,显然是希腊著名技师克里夏斯(Clitias)和埃哥第麦斯(Ergotimus)的作品。稍后发现的一些瓮,黑底绘上红色图样,倒很别致,但显然也是希腊制造的。这种产品的丰富,使人联想起阿提卡陶器夺取了埃特鲁里亚市场,迫使本地工人只限于从事工业产品生产。总而言之,强盗们抢劫埃特鲁里亚坟墓而留下那么多陶器时,他们就被宽恕了。
我们谈到埃特鲁斯坎人的青铜器时,就不能那么不客气了。埃特鲁斯坎人的青铜矿工,是他们手艺最上乘的人。其青铜器的产量差不多可与其陶器匹敌。据说,单是一个城市之内,就有过2000尊铜像。他们留给我们的遗物,差不多全是罗马统治期间的作品。在这些浮雕品之中,有两件突出的杰作:《演说者》(Orator)存于佛罗伦萨考古陈列馆,这件作品有罗马人的高贵气质与青铜的谨严;1553年在阿雷佐发现的《凯米拉》(Chimera,怪物名)也保存在佛罗伦萨,但有一部分是经过切利尼(Cellini)修复的。这是一尊令人厌恶的铜像,可能是被柏勒洛丰(Bellerophon,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英雄)所杀的怪物(“凯米拉”)——狮头狮身,尾巴是一条蛇,背上长出一个羊头。然而其暴力与结局则使我们一致认为,这只是生物学上的幻想物而已。埃特鲁里亚的青铜产品,如小像、剑、头盔、胸甲、矛、盾、餐具、水壶、硬币、锁、链、扇、镜、床、灯、烛台,甚至还有战车,数以百万计,常输出到遥远的地方。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保存的一辆埃特鲁里亚战车,很受游客的欢迎:车身和轮子是木制的,套子及轮箍是铜的,前部很高,且有相当优美的人物浮雕。许多青铜制品都有精致的雕刻。表面以蜡涂着,用铁笔将图样蚀刻进去,将整个作品浸入酸液,无蜡的线条被酸液腐蚀,然后将蜡熔去。在金、银、骨、象牙的雕刻方面,埃特鲁里亚的艺术家是埃及与希腊人的继承者及同辈。
在埃特鲁里亚社会,石头雕刻并不流行。大理石很少,显然他们还不知道卡拉拉(Carrara)有采石场。优质黏土是有的,很快就被用来制成许多陶器浮雕、小像及石墓或建筑的装饰物。约公元前6世纪末,一个不知名的埃特鲁里亚艺术家在维爱建立了一所雕刻学校,刻出了埃特鲁里亚艺术的杰作《维爱的阿波罗》(Apollo of Veii),那是1916年在这里发现的,直至最近还竖在罗马的朱利亚别墅(Villa Giulia)中。这个可爱的雕像,是仿照当时的伊奥尼亚与阿提卡的《阿波罗》像做成的,这像显示出差不多是蒙娜丽莎的脸型,带着微妙的笑容,弯而斜的两眼,以及健康、美丽和充满勃勃生气的身体,意大利人称之为《行走的阿波罗》(il Apollo che cammina)。在这尊雕像以及许多石棺上所雕刻的人物中,其头发与披巾的亚洲形式已被埃特鲁里亚雕刻家做得惟妙惟肖了。在《演说者》那尊雕像中,他们及其罗马传人则已替写实的肖像画建立了一个传统。
埃特鲁斯坎人的绘画,与希腊、意大利的绘画融和,将另一种艺术传给了罗马。老普林尼描写阿尔代亚(Ardea)的壁画为“比罗马本身还古老”;而对其他壁画,则称为“更老的古物”,且是“最美的”。其艺术利用陶器及家庭与坟墓的内部作为它的外表,只有墓中的壁画与瓶画遗留了下来。由于留下的数量很多,使我们可从那些遗物中追溯埃特鲁里亚绘画的每一阶段,从东方的与埃及的开始,经过希腊的与亚历山大城的,最后到罗马与庞贝的风格。在很多坟墓中,我们发现第一批意大利标本的窗户、入口处、柱子、门廊及画在内墙的其他仿造的建筑形式,每一种风格都是庞贝的。这些壁画的颜色,一般都已消退,但有几幅则使人大为惊异,经过2000多年的时光,其颜色还是光彩夺人,其技艺则很平凡。早期的绘画没有配景,没有远近透视,没有用光暗变化表现充盈与深度;人物都是埃及人的苗条身材,好像在凸面镜中平视一样;不论足尖方向如何,面孔总是侧面的。在稍后期的标本中,配景法与透视法已经出现,身体的比例都呈现得很逼真、很有技巧。但是,无论哪一时期的画,都表现出狂欢快乐,近乎顽皮,使人想到其坟墓做得那么好,真不知埃特鲁斯坎人的生活有多么的愉快。
这些人生活在战斗中,因战斗而愉快;在竞技场中,骑马进行长矛比武;他们猎捕野猪或狮子,那些拥有观众的勇士全力以赴;他们在运动场赛拳或摔跤,而观众们的议论反比参赛者更激烈;他们骑马或驾战车绕着小山而行;有时也平静地去捕鱼。在一幅令人愉快的画面中,一对夫妻在静静的小溪中悠闲地划着船,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明智之举。在西西里的一个坟墓中,画着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靠在一张长椅上;男子戴着桂花冠,举起一杯酒,向女子发誓永远对她忠诚不变;她虽然明知他说谎,还是笑了。在其他墓室中,埃特鲁里亚画家画出了他们的理想天堂:永不休止的狂欢酒会,无忧无虑的小姑娘,随着双管笛和七弦琴热烈狂舞。笛子、七弦琴、喇叭及古笙,显然是每个宴会、婚礼及葬礼所不可或缺的。爱好音乐和跳舞,是埃特鲁里亚文明优美的一面。在科尔内托的里奥内斯(Lioness)地区,有一个坟墓,所画的人物都赤身裸体,狂欢暴饮,疯狂旋转。
埃特鲁斯坎人向南北同时扩张,其势力伸展到北方的阿尔卑斯山麓和南方的一个叫坎帕尼亚(Campania)的希腊城市。于是,他们就与新兴的罗马隔着台伯河对峙。他们在维罗那、帕多瓦、曼图亚、帕尔马、摩德纳、博洛尼亚及亚平宁山脉外的里米尼、拉韦纳及亚得里亚等处建立了殖民地。亚得里亚是埃特鲁斯坎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前哨,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即因此地而得名。埃特鲁斯坎人在费德纳、柏拉尼斯特及卡普亚,可能还有小托斯卡纳等处殖民,这样就把罗马包围起来了。最后,公元前618年(这个年代,虽然传统说得那么肯定,却不很可靠),埃特鲁斯坎人的一支先锋部队占领了罗马城。之后的100年里,罗马始终受着埃特鲁斯坎人的权力统治,并依其文化而组织国家形式。
诸王统治下的罗马
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维拉诺瓦移民渡过台伯河,定居于拉丁姆(Latium)平原。他们是否征服或消灭了此处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种,或与他们通婚,无从知晓。在台伯河与那不勒斯之间这个历史区域的各个村落,逐渐合并成为一些城邦国家,彼此互相嫉妒,不愿团结,只有在每年的几个宗教节日或偶然对外战争时,他们才会联合起来。其中最强的城邦是位于阿尔邦山(Mt.Alban)山麓的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这里可能就是教皇避暑的冈道尔夫堡(Castel Gandolfo)。大概在公元前8世纪,一队拉丁姆移民——由于对征服的贪婪或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而需要土地——向西北移动了20英里左右,在这里创建了最著名的人类居所——阿尔巴隆加城邦。
不妨大胆地臆断,这可以说就是罗马全部历史的起源。但是,罗马人的传统说法却不如此简单。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烧毁了罗马城,大多数的历史记录可以说都被付之一炬。继此之后,富于爱国心的想象就自由地描绘出罗马的诞生。而我们所称的公元前753年4月22日这一天,就被称为A.U.C.(anno urbis conditae),即罗马开始建城之日。成百上千个故事和诗歌告诉我们,阿佛洛狄忒的子孙埃涅阿斯(Aeneas)如何从燃烧的特洛伊城逃出,忍受了许多当地人的虐害之后,终于带着普里阿摩斯城的神祇或肖像来到意大利。埃涅阿斯娶了拉丁姆国王之女拉维尼亚(Lavinia)为妻,其第八代子孙努米托(Numitor),据说就在拉丁姆首都阿尔巴隆加登上王位。一个篡位者阿穆留斯(Amulius)赶走了努米托,为了断绝埃涅阿斯的后代,又把努米托的儿子杀死,并强迫其唯一的女儿瑞亚(Rhea)到维斯塔神庙(Vesta)去做女祭司,并要她誓不嫁人。但是,瑞亚在一条小溪旁边躺下,“敞开胸部乘凉”。她相信神和人都不会侵犯她,就睡着了。战神(Mars)为她的美丽所惑,使她生了一对孪生子。阿穆留斯下令溺死这两个婴儿。他们被置放在一只木筏上,却被波浪吹上岸去,由一只母狼哺乳——另有一个怀疑的说法,喂乳者系一个牧羊人的妻子阿卡·洛伦蒂(Acca Larentia),其绰号卢帕(Lupa)与母狼同音,她因为喜欢这两个小孩,而又不知道此属犯法,所以把他们带大。这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叫罗慕路斯(Romulus),另一个叫雷穆斯(Remus),他们长大之后,就杀了阿穆留斯,使努米托复位,他们自己则坚决地到罗马小山上另建一个王国。
考古学家并没有提供证据以证实这些故事,但它可能包含着一个真实的核心。也许拉丁姆派遣一部分殖民去发展罗马,作为抵抗埃特鲁斯坎人扩张的战略外壕。城址距海20英里,对海上贸易并不十分适宜,但在那个海盗劫掠的时代,倒也是适当的。至于内部商业,罗马位于南北水陆交通的要道,十分便利。那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所在,多雨、洪水泛滥,又处于被平原包围的沼泽中,甚至城中的低洼地区,春天都是疟疾的温床,所以全城的七座山冈都盛行疟疾。据传统说法,首先建筑的山冈是帕拉蒂尼,可能是因为该处山下有一个小岛,便于作为台伯河的徒涉场及架桥。其邻近各山冈的斜坡上也暂住了人,而且不断增加,直至人口泛滥,以至于渡过台伯河就到了梵蒂冈及雅尼库伦(Janiculum)山冈之上 。“七山”居民有三种部落——拉丁姆人、萨宾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他们首先组成一个联邦(Septimontium),逐渐合并而成为罗马。
。“七山”居民有三种部落——拉丁姆人、萨宾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他们首先组成一个联邦(Septimontium),逐渐合并而成为罗马。
古代传说的故事还告诉我们,罗慕路斯如何使那些移民娶妻。他安排一些运动项目,邀请除萨宾人的其他部落参加。赛马时,罗马人夺取了萨宾人的妇女,并将其男子赶走。萨宾丘里迭斯部落(Curites)的国王塔提奥斯(Tatius)立即宣战,并进军罗马。据守卡皮托利诺要塞的是罗曼(Roman),他的女儿泰匹亚(Tarpeia)打开城门迎接进攻者入城。他们给她的报酬,是用盾牌将她打死。过了几代之后,以她的名字命名“泰匹亚岩石”(Tarpeian Rock),那是一个刑场,凡是判了死刑的人,就从这里抛下去摔死。萨宾的妇女并不抱怨被掳,当国王塔提奥斯的军队逼近帕拉蒂尼时,她们请求休战,因为如果丘里迭斯人战胜,她们便要失去丈夫;丘里迭斯人如果战败,她们就要失去父兄。罗慕路斯又说服塔提奥斯与自己共主王国,且使丘里迭斯人与拉丁姆人合并,成为共同的国民。自此以后,罗马的自由人就称为丘里迭斯人。在这“罗曼蒂克”的故事中,或者也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在内——否则就是基于爱国心,而掩饰了萨宾人征服罗马的事实。
经过长时间的统治之后,罗慕路斯被一阵旋风送上天去,此后他就被崇拜为奎里努斯(Quirinus,罗马人所爱的神祇之一)。塔提奥斯死后,那些重要家族的族长们选择一个名叫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的萨宾人为国王。自罗马城创建至埃特鲁斯坎人统治之间,罗马政府的权力可能掌握在那些长老或元老之手,而国王的职责,则像同时代的雅典执政官,主要负责的都是最高祭司的职责。罗马的传说把努马描绘为萨宾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身兼哲学家与圣人。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写道:
他努力教导人民敬畏神祇,视之可对……野蛮民族发生最为强大的影响。但如果不宣称具有超自然的智慧,那么他的努力将无法感动人民,他便佯称夜间曾与女神埃吉里亚(Egeria)晤谈,并遵照她的劝告,制定天堂最能接纳的宗教仪式,同时为每一个重要神祇委派一个特别祭司。
通过在罗马各部落建立一个统一的崇拜,努马加强了他的王国的统一与安定。西塞罗认为,努马使好战的罗马人将兴趣转向宗教,给他的人民带来了40年的和平。
他的继任者图卢斯·荷提里乌斯(Tullus Hostilius)使罗马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确信,国家的活力由于久无战斗,而逐渐地衰弱。他环顾四邻,觅取战争借口。”他选择罗马的母城阿尔巴隆加为敌国,加以攻击,并将其彻底消灭。当阿尔巴隆加国王违背同盟承诺时,图卢斯将他捆在两车之间,并使两车向相反方向驶去,而把他撕成碎片。图卢斯的继任者安库斯·马西乌斯(Ancus Martius)也赞同他的尚武哲学。据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罗马史学家)说,图卢斯的战争哲学,安库斯完全了解:
人们希望借不做错事而保持和平,那是不够的……但是,一个人愈想和平,他就愈容易遭受攻击。他看出,对于安静的渴望,并不是一种防护力,除非配备用于战争的装备;他又认识到,在四方扰攘中,只耽乐于自由,而不热心战争的人,很快就会被毁灭。
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
传说接着告诉我们,约公元前655年,科林斯富商狄马拉塔斯(Demaratus)被驱逐出境,来到塔奎尼乌斯居住,娶了一个埃特鲁里亚女人为妻。他的儿子卢西乌斯·塔奎尼乌斯(Lucius Tarquinius)迁居罗马,并在那里取得很高的地位,当安库斯死时,或是他自己夺取了王位,或者——更可能的是——与城内的所有埃特鲁里亚家族联盟,而被选举为王。李维说:“他是第一个通过拉票为王的人,他发表许多演说,取得平民(pleb)的支持。”平民是指那些无法追溯其原始祖先的市民。君主政治的权力,在这位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的治理下日见增大,进而凌驾于贵族政治之上,而罗马的政治、工程、宗教和艺术,因而大受埃特鲁斯坎人的影响。塔奎尼乌斯王成功地击败了萨宾人,并征服了整个拉丁姆平原。据说,这位国王利用罗马的资源,去装饰塔奎尼乌斯城及埃特鲁里亚的其他城市,同时也把埃特鲁里亚及希腊的艺术带回他的首都,并兴建了好多庄严的寺庙,以美化罗马。显然,他代表着商业与商人势力的增强,压倒了地主的贵族政治。
这位第一个塔奎尼乌斯王,在统治38年之后,被一个贵族刺死,此人的目的是想把王权再度限制在一个宗教角色之上。但是,塔奎尼乌斯的遗孀塔纳奎控制住了形势,并把王位过渡给她的儿子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据西塞罗说,图里乌斯是第一个“不经人民选择而保持王权的国王”。这里所谓的“人民”(people),是指有领导地位的众家族。他统治得很好,并在罗马四周筑起城墙,开掘外壕。但是,大地主们憎恨他的统治,并密谋推翻他。结果,他便与平民中的富有者结为同盟,并改编军队及选举人,以加强其地位。他实行人口与资产普查,依照市民的财富而不是依照其出身来区分阶级。于是,虽然旧的贵族阶级没有变动,他却提起一个骑士(equites)阶级,作为一个平衡力——所谓骑士,就是能自备马匹与披甲而服役于骑兵队的人。 这次普查报告显示,能够负担武装的约有8万人。如果每位士兵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每四个家庭有一个奴隶,据此估计,约公元前560年,罗马人口及其郊区臣民的总人数约有26万。图里乌斯把人们分为35个新部落,依照居住地区,而不是血统和阶级。因此,也像之后的阿提卡的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雅典执政官)一样,他将贵族阶级的政治凝聚力与选举力削弱了——贵族阶级是依出身而列为最高阶级的。他自己的侄儿攻击他的统治不合法,他就举行一次平民投票,据李维说,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他的侄儿不服,暗杀了图里乌斯,自称为王。他与塔奎尼乌斯同名,故为另一个塔奎尼乌斯。
这次普查报告显示,能够负担武装的约有8万人。如果每位士兵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每四个家庭有一个奴隶,据此估计,约公元前560年,罗马人口及其郊区臣民的总人数约有26万。图里乌斯把人们分为35个新部落,依照居住地区,而不是血统和阶级。因此,也像之后的阿提卡的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雅典执政官)一样,他将贵族阶级的政治凝聚力与选举力削弱了——贵族阶级是依出身而列为最高阶级的。他自己的侄儿攻击他的统治不合法,他就举行一次平民投票,据李维说,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他的侄儿不服,暗杀了图里乌斯,自称为王。他与塔奎尼乌斯同名,故为另一个塔奎尼乌斯。
在这个绰号为“骄傲者”的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 Superbus)的统治之下,君主变成了绝对权力者,埃特鲁斯坎人的影响力高于一切。贵族们一向认为国王只是元老院的执行人及全国宗教的祭司长而已,他们绝不能长久忍受无限制的王权。因此,他们曾经杀死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第一个塔奎尼乌斯王),对图里乌斯的被杀,他们却袖手旁观。但新塔奎尼乌斯王却比第一位塔奎尼乌斯王更坏。他身边有一个卫队,迫使自由人服数月的劳役以贬抑其地位,在广场上把公民钉死在十字架上,处死了许多上层阶级的领袖。他极度暴虐,招致全国有影响力的人的一致痛恨。 他想借战争以博取威望,于是进攻鲁图里人(Rutuli)及沃尔西人(Volscian)。公元前508年,正当他率军出征时,元老院集会把他废除,这是罗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他想借战争以博取威望,于是进攻鲁图里人(Rutuli)及沃尔西人(Volscian)。公元前508年,正当他率军出征时,元老院集会把他废除,这是罗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共和国的诞生
有关此事,传说变成了文学,政治散文融化而为情诗。据李维说,一天晚上,在阿尔代亚地方的国王营帐中,国王塞克斯都·塔奎(Sextus Tarquin)正与一个亲戚科拉提努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辩论着他们的妻子中哪一个德行更好。科拉提努斯提议,他们应立即乘马回罗马去,使他们的妻子在深夜惊喜一番。回到罗马宫中,他们发现塞克斯都的妻子正和密友们欢宴,而科拉提努斯的妻子卢克里莎(Lucretia)则正为她的丈夫织羊毛衣。塞克斯都大受刺激,很想探试卢克里莎的忠贞,并享受她的爱。几天后,他秘密回到卢克里莎家中,用欺骗和暴力制服了她。卢克里莎派人请回她的父亲和丈夫,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便自杀。为了这件事,科拉提努斯的朋友布鲁图(Lucius Junius Brutus,与暗杀恺撒的那位布鲁图不是同一个人)向所有反对塔奎的人要求,把塔奎尼乌斯王室逐出罗马。他自己本是国王的侄儿;但是,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被塔奎处死了,他为了保全性命以待复仇,便假装精神错乱,因此得了这个布鲁图的别名(意为“傻子”)。现在,他和科拉提努斯一同骑马前往元老院,把卢克里莎的事情告诉元老们,并促请驱逐所有的王室成员。与此同时,国王也已离开军队,匆匆地赶回罗马;布鲁图得到这个消息,骑马前往军中,又把卢克里莎的事情说了一遍,遂获得军人的支持。塔奎王逃奔北方,请求埃特鲁里亚为他恢复王位。
国民与军人召开第一次大会,他们不再选举一个终身国王,而选出两位执政(consul) ,统治期为一年,两人的权力完全相等。依据传说,第一届两位执政就是布鲁图和科拉提努斯,但科拉提努斯辞职,代替他的是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Publius Valerius),他之所以博得“人民之友”(publicola)的称号,是因为他曾促使议会通过几个法案,迄今仍为罗马的基本法:(1)对于任何试图自立为王的人,可以杀之而不受审判;(2)任何人不经人民同意而企图擅自担任公职者,应处死刑;(3)任何市民被官员判处死刑或鞭笞罪者,均有权向议会上诉。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还曾创下一个惯例,当执政进入议会时,必须将其随从所持的斧头从束棒取掉,并予放下,以表示服从人民主权,以及平时宣判死刑的唯一权力属于人民。
,统治期为一年,两人的权力完全相等。依据传说,第一届两位执政就是布鲁图和科拉提努斯,但科拉提努斯辞职,代替他的是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Publius Valerius),他之所以博得“人民之友”(publicola)的称号,是因为他曾促使议会通过几个法案,迄今仍为罗马的基本法:(1)对于任何试图自立为王的人,可以杀之而不受审判;(2)任何人不经人民同意而企图擅自担任公职者,应处死刑;(3)任何市民被官员判处死刑或鞭笞罪者,均有权向议会上诉。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还曾创下一个惯例,当执政进入议会时,必须将其随从所持的斧头从束棒取掉,并予放下,以表示服从人民主权,以及平时宣判死刑的唯一权力属于人民。
这次革命导致了两大结果,罗马从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并以贵族政治代替君主政治,贵族们统治罗马直至恺撒为止。但是,贫穷市民的政治地位并无改善;相反,之前由国王图里乌斯给予他们的土地,现在都要交出,而且还失去了适度的保护法案(凭那些法案,贫民在君主的庇护之下,可不受贵族的支配)。胜利者们称这次革命为自由的胜利,然而强者口号中的自由,时时意味着强者剥削弱者的限制被解除了。
塔奎尼乌斯家族被逐出罗马,再加上公元前524年在库迈(Cumae)地区,埃特鲁斯坎人被希腊殖民军队打败,埃特鲁斯坎人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导权受到威胁而濒临结束。基于上述理由,克卢奇安的行政长官波尔塞纳(Lars Porsena)答应了塔奎的请求,从埃特鲁里亚联邦各城市中召集一支军队,向罗马推进。同时,在罗马方面也有人企图使塔奎复位。布鲁图的二子也在被捕的谋变人物之中。这位性如烈火的第一届执政,以禁欲主义者的沉默,目睹着他的孩子受鞭笞及斩首之刑,替日后的罗马提供了一个榜样——这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罗马人在波尔塞纳的军队到达之前拆毁了台伯河的所有桥梁。那位霍拉提乌斯(Horatius Codes)就是在这次防御桥头堡之战中,使自己在拉丁文及英文诗歌中永垂不朽的。尽管有些故事试图以光荣掩饰战败的其他传说,罗马终于还是向波尔塞纳投降了,且割让了一部分领土,那是被罗马诸王先后掠夺过的一些拉丁姆市镇。波尔塞纳为表示感谢,并不要求恢复塔奎的王位。这时候,埃特鲁里亚的贵族们也把他们的君主放逐了。罗马衰弱了一代之久,然而其革命仍然存在。
埃特鲁斯坎人的政权虽已被推翻,然而埃特鲁斯坎人影响的特征与遗迹,仍存于罗马文明之中,直至埃特鲁里亚灭亡为止。在拉丁语中,显然很少受到埃特鲁里亚的影响;然而,罗马数字可能都是埃特鲁里亚的,而“罗马”这个名字,也可能出自埃特鲁里亚语的拉蒙河(Rumon)。罗马人相信,他们征服者的凯旋仪式,政务官员的紫边袍子与象牙宝座(形似战车),以及在执政之前由12名手下携带的象征执政打、杀权力的束棒和斧头,都是仿自埃特鲁斯坎人的。 在罗马建立其舰队之前数世纪,其银币即用船首作为花纹——埃特鲁斯坎人的硬币则久已使用这种花纹,以象征其商业活动与海军力量。自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罗马贵族中有一种习惯,他们派遣其子弟前往埃特鲁里亚的各城市去接受高等教育;他们要学习几何学、测量学和建筑学等。罗马的衣服式样同样仿照埃特鲁斯坎人,抑或两者系出同源。
在罗马建立其舰队之前数世纪,其银币即用船首作为花纹——埃特鲁斯坎人的硬币则久已使用这种花纹,以象征其商业活动与海军力量。自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罗马贵族中有一种习惯,他们派遣其子弟前往埃特鲁里亚的各城市去接受高等教育;他们要学习几何学、测量学和建筑学等。罗马的衣服式样同样仿照埃特鲁斯坎人,抑或两者系出同源。
罗马的第一批伶人,以及他们被称为演员(histriones)的人,皆来自埃特鲁里亚。如果李维的话可信,罗马的第一个大竞技场的建筑,以及由埃特鲁里亚输入比赛马匹及拳击师到罗马比赛,就是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所为。埃特鲁斯坎人带给罗马残酷的格斗竞赛,但也带给罗马妇女比在希腊所能发现的更高地位。埃特鲁里亚的工程师们替罗马建筑城垣和排水设备,并把一个沼泽地区神奇地变为有保护和文明的都城。罗马的宗教仪式,如占卜官、肠卜祭司、预言者等,绝大部分都是效法埃特鲁斯坎人的。迟至尤里安(Julian)皇帝时(公元前363年),埃特鲁斯坎人的占卜官仍为罗马各部门中一个正规编制。罗慕路斯是以埃特鲁斯坎人的礼仪习惯来划定罗马疆界的;有抢夺象征的罗马婚礼及正式的葬礼,也可能出自同一来源。罗马音乐的音阶法及乐器,也来自埃特鲁里亚。罗马的画家,绝大部分都是埃特鲁斯坎人——画家们工作的那一条街叫作维库斯·图斯库斯(Vicus Tuscus)。可是,画家本身也可能是坎帕尼亚的希腊人,经由拉丁姆渗透进来的。罗马的雕像深受为家庭画廊而制作的死亡面具的影响,而这种面具又是来自埃特鲁里亚的习惯。埃特鲁里亚雕刻家以青铜像、陶瓷像及浮雕来装饰罗马的寺院及王宫。埃特鲁里亚建筑师传给罗马一种托斯卡纳建筑式,迄今仍可在圣彼得教堂的柱廊中见到。罗马的几位埃特鲁里亚国王,似乎是首先建造罗马大建筑的人,他们把用土屋或木屋拼集起来的一些村落,改造为由木、砖、石造的城市。直到恺撒时代,罗马人未尝见过比埃特鲁斯坎人统治期间更多的建筑。
我们绝不应过度夸大这种情形。尽管罗马曾向其邻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但在其生活的所有基本特征中,显然还是罗马自己的。在埃特鲁里亚历史中,并没有使人联想起罗马特性的东西。罗马凭借其严格的自律、残酷和勇气、爱国心与禁欲的行为,耐心地征服并统治着地中海沿岸国家。现在,罗马已经自由了,舞台已经准备就绪,兴亡大戏即将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