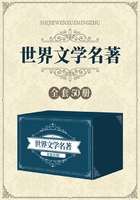
第246章 牧场
本书的其余关节,就要表达完毕。且说乔治·谢尔比,他一则像别的年轻人一样,对两人的传奇般的遭遇感兴趣,一则常怀仁慈博爱之心,于是,不惮烦劳,把伊丽莎的卖身契寄给了凯茜。上面所著日期和姓名,都同她自己所记得的情况完全吻合。这就使她觉得确凿无疑,认定卖身契上的姑娘就是自己女儿,而现在,有待她做的,便是寻访逃亡者行踪的蛛丝马迹了。
如此一来,命运的出人意料的巧合,便把她和都德夫人维系在一起。她们当即日夜兼程赶赴加拿大,开始了查访无数摆脱奴隶制度的逃亡者所栖身过的各个收容站。在阿默赫斯堡,她们找到了乔治·哈利斯和伊丽莎初抵加拿大时藏身于其处的那个传教士,通过他才追踪乔治一家来到了蒙特利尔市。
这时,乔治和伊丽莎获得自由满五年了。在一个知名的机械师的工厂里,乔治谋到了一份固定职业,挣的工资足以养活全家。同时,家里又添了一个女儿。
小哈利,现在已是个英俊聪明少年,在一所有名的学校念书,学业知识迅速长进。阿默赫斯堡收容站的牧师,乔治刚刚登陆时在他处栖身的那个令人尊敬的牧师,对都德夫人和凯茜所讲述的情况,兴趣盎然,于是在前者请求下,答应陪同她们去蒙特利尔寻访亲人。一切费用由都德夫人开销。
于是,故事场景转换到了蒙特利尔市郊的一座整洁的小公寓里,其时正是黄昏时分。壁炉里,火苗噼噼啪啪欢乐地燃烧着;铺着雪白桌布的茶桌已经摆好,做好了吃晚饭的准备。房间一角,有一张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是一张放有纸笔的宽大写字台,上方的书架上,摆满了经过精心选择的书籍。
这就是乔治的书房。想当初,他热心进取,在千辛万苦、灰心沮丧之中,偷闲学会了读书写字的本事,现在,仍然让他孜孜以求,把全部闲暇时间都花在自己进修方面。
这一刻他正在书桌旁边,从自己阅读的一卷家庭藏书中,做着摘记。
“来,乔治,”伊丽莎说,“你一整天不在家,快放下书,趁我泡茶的时候,说说话吧。快放下。”
小伊丽莎也支持妈妈的动议,蹒跚跑到爸爸面前,想把书从他手里夺下来,从而使自己坐到他膝头上去。
“噢,你这个小调皮!”乔治缴械投降了,因为处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总得这么办才好。
“这就对啦。”伊丽莎动手切着一方面包,说。她看起来年龄大了几岁,腰肢丰满了些,仪态也比以前更像主妇了。然而,跟别的女人一样,显然感到幸福与满足。
“哈利,我的孩子,你今天那道算术题做得怎么样了?”乔治用手摩挲着儿子的脑袋,问。
哈利长长的鬈发没有了,但他那眼睛和眼睫毛,以及他那英俊而高耸的前额,却依然如故。他脸上透红,得意扬扬地回答道:“我全部算完了,全是自己做的,爸爸,谁也没帮我!”
“对呀,”父亲说,“要靠自己,儿子。你的机会比你可怜的父亲好。”
这当儿,有人轻轻叩门,伊丽莎应声去开门。她欣喜的一声“哦,原来是你呀”的叫喊,引起了丈夫的注意。接着,阿默赫斯堡的牧师被请了进来。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两个女人,伊丽莎一一请她们坐下。
诸位,如果要把真实情况说出来的话,那个纯朴的牧师本来安排了一个小小的程序,整个事情都要按程序进行。来这里的路上,大家还小心谨慎地劝告彼此说,除非事先有变动,否则不能一下子就开门见山,泄露出去。
因此,让那个好心牧师惊愕的是,他挥手示意让她坐下,掏出手帕擦了擦嘴,正要按着顺序先来一番开场白时,都德夫人却一下子搂住乔治的脖子,打乱了全盘计划,接下来又说:“哦,乔治,你难道不认识我啦?我是你姐姐艾米莉呀!”这样,事情立刻便全部暴露出来。
凯茜比较平心静气地坐了下来。若不是小伊丽莎突然闯到她面前,她原来是能扮演好她的角色的。小伊丽莎,从身段体态、面貌轮廓和满头鬈发上看,无不与她当年分离的女儿一模一样。那小东西一直盯着她的脸,凯茜抱起她来,紧紧搂在怀里,说了一句在当时自己信以为真的话:“宝贝,我是你妈呀!”
实际上,这件事要完全有条不紊地进行,确实不容易。不过,好心的牧师最后还是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出了他原打算用以开演这幕戏的开场白。他讲得非常成功,使身旁的所有的听众一齐抽泣起来。这足可以令古今的演说家心里感到欣慰了。
大家跪在一起,好心的牧师祈祷起来,因为,人们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时,只有将爱倾注于万能上帝的胸怀,心情才能平静下来。然后大家站起身来,重新团聚的一家人,互相拥抱着,对于上帝,心里充满了圣洁的信赖。是他,利用意想不到的方式,从千难万险之中,让他们得到了团圆。
在进入加拿大的逃亡者当中,有一位传教士的笔记,记载了比小说更为离奇曲折的真实事件。当盛行的奴隶制度,犹如秋风横扫落叶一样,吹散一个个家庭,弄得人们妻离子散的时候,事情怎能不会这样离奇曲折呢?这条避难的海岸,仿佛是永恒的海岸,往往使多年来彼此痛悼,认为对方已经死去的人们,在这里再次欢聚。每一个初到这里的人,都受到难以形诸言辞的诚挚欢迎,因为,他们或许会带来仍然湮没于奴隶制度阴影中的母亲、姐妹、妻子或儿女的消息,也未可知。
在这里,当逃亡者置酷刑和死亡于不顾,心甘情愿地寻原路回到充满恐怖与危险的黑暗大陆,希望把自己姐妹、母亲或妻子救出来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英雄壮举,在传奇当中为数更多。
一位传教士告诉我们,有一个青年曾两次遭到抓获,并为他的英勇行动,受到可耻的鞭笞,终于又逃了回来。我们听人念过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信里说他打算第三次回去,好救出他的妹妹。好心的看官,这人是个英雄还是罪犯?难道你不会为自己的姐妹,做出这样的牺牲吗?你能责备他吗?
闲言放在一边,回头再表我们的朋友。由于突如其来的巨大喜悦,他们正在擦着眼里的泪水,心情逐渐恢复了平静。这时,全家人热热闹闹,坐在桌子周围,确确凿凿,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只有凯茜一直把小伊丽莎抱在膝头,不时用力搂她一搂,使小东西很是奇怪。同时,还固执地拒绝小东西随着自己的意思,往嘴里塞糕点,这又使孩子迷惑不解,但凯茜说,自己有比糕点还好吃的东西,所以不想吃糕点。
过了一两天,凯茜的变化确实不小,连诸位看官恐怕也快认不出她来了。脸上绝望的枯槁的神色,换成了温柔和信赖的表情。她好像一下子投入了家人的怀抱,而自己也十分珍爱那两个孩子,仿佛是她企盼已久的人。她的爱,似乎自然而然地更多地倾注在小伊丽莎身上,而不是自己女儿身上。因为小伊丽莎与她失去的女儿,在外貌和体态上丝毫不差。那小东西成了母女之间用鲜花编成的一条纽带,通过她,母女才熟悉起来、相爱起来。伊丽莎由于经常诵读《圣经》,使自己的虔诚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因此成了母亲那颗疲惫破碎心灵的正确指南。凯茜也立即全身心地接受种种有益影响,变成了虔诚而又温柔的基督徒。
一两天之后,都德夫人把自己的情况更详细地讲给了弟弟听。她丈夫死后,给她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自己想慷慨地拿出来,供全家人分享。她问乔治利用这笔遗产为他做什么最好时,乔治回答:“让我念书去吧,艾米莉,这一直是我的心愿,其余的你都不用操心了。”
经过充分的酝酿,他们决定全家去法国住几年。于是,他们便带着艾米琳,一起扬帆前往法国。艾米琳妩媚的姿色,赢得了轮船大副的倾心;轮船到达港口不久,她就做了他的妻子。
乔治在法国一所大学里攻读了整整四年,靠着自己不懈热情的孜孜以求,受到了完备的教育。
最后,法国发生了政治动乱,全家人才再次到美国来避难。
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乔治此时的感情和见识,在他致朋友的一封信中,表达得最为充分:
对于自己的前程,我也感到有些困惑。诚然,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在这个国家,我可混入白人的生活圈子。我的肤色很浅,我妻子和家人的肤色,也几乎难以辨别。嗯,也许在人们默许的情况下,我可以这样做。不过,说句心里话,我根本无意于这样。
我内心的怜悯之情,不是寄予我父亲的种族,而是寄予了我母亲的种族。对于我的父亲,我只不过是一条好狗或者一匹好马罢了;但对于我的母亲,我才是一个孩子。虽然那次残忍的拍卖使我们分散,一直到她去世,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但我明白,她是一直深深爱着我的。我从心底深处明白这一点。每当我想起她身受的全部苦难,想起我早年经受的折磨,想起我英勇妻子的不幸和奋争,想起我那在新奥尔良奴隶市场上卖掉的姐姐,虽然我不希望自己带有什么违背基督教义的感慨,但我这样说,是可以谅宥的,我决不愿意充当美国人,或者把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
与我共命运的是受压迫、受奴役的非洲种族。因此,倘若我还希求什么的话,那就但愿自己肤色再黑两分,而不是再白一分。
我心灵的渴望和希冀,就是取得一个非洲国家的国籍。我想找一个将来分明是能够自己独立生存下去的民族,可是,我到哪里去寻找呢?当然不是到海地去寻找,因为在海地,人们没有采取行动的渊源。一条小溪不可能高过它的源泉。构成海地民族性格的那个种族,是个衰竭、柔顺的种族,自然而然,一个臣属的种族,要想成就什么业绩,就需要好几百年了。
那么,我到哪里去寻找呢?我在非洲的海岸上,见到了一个共和国,一个由杰出超群的人民构成的共和国,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依赖自己的努力和自我教育的力量,独自摆脱奴役状态的。这个共和国经历了初期的软弱状态之后,终于变为一个得到全世界公认的国家,得到了法国和英国的承认。我想到那里去寻找自己的人民。
现在,我清楚,你们都会反对我去的,但是在提出反对之前,请先听听我的申辩。我在法国逗留期间,曾怀着深刻的关切,探索过我的人民在美国的历史。我关注过废奴派和殖民派之间的斗争,作为远在他国的旁观者,得到了一些直接参与者所永远无法获得的印象。
我承认,这个利比里亚曾经被我们压迫者玩于股掌之上,为了达到种种目的,利用它在我们之间进行挑拨离间。无疑,这种阴谋可以种种不正当的方式,用作延迟我们的解放的手段。然而,对我来说,问题是有没有超越人类各种阴谋的上帝,难道上帝不能摧毁他们的阴谋,并由此为我们缔造一个国家。
当前,一个国家的诞生,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一切有关共和国的生存和文明等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近在眼前。因此,它现在的创建无须再去寻寻觅觅,所需要的,只是付诸行动。让我们团结一心,用尽我们全部力量,来为这一新事业尽自己之所能,那么,一个辉煌的非洲,就会呈现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面前。我们的国家将沿着非洲海岸,掀起文明和基督精神浪潮,在那里培育起一些强大的共和国来。它们将犹如热带植物,迅猛成长,永存于未来的世世代代之中。
你认为我是在抛弃自己受到奴役的兄弟吧?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倘若在我生命的一时一刻,我忘记了他们,那就让上帝也忘记了我吧!然而,在这里,我能对他们有什么作为呢?我能打碎他们的枷锁吗?不能,作为个人,我无能为力,但是让我去做一个国家的一员吧。这个国家将在各国的会议上,拥有一席发言之地。那时,我们才能说出我们的意见。一个国家拥有辩论、抗议和呼吁,以及陈述自己种族事业的权利,然而,个人却没有。
如果将来欧洲变成各自由国家组成的大议会——我深信,上帝一定会做到这一点的,如果农奴制度、一切的非正义的、压榨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都被铲除净尽,如果他们仿效法国和英国,承认我们的地位,那么,我们将会在国际大会上,为我们受奴役、遭苦难的种族所进行的事业发出呼吁,陈述我们的观点。那时,自由开明的美国将不会不愿意从自己盾牌上抹去左边的、使它羞见于各国的线条[158],而这对于它和受奴役者,都是一种祸根。
然而,你肯定会对我说,在美利坚合众国,我们这个种族,同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一样,都享有杂居的平等权利。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应该自由地相处和共同居住,在完全不考虑种姓和肤色的条件下,依靠个人的价值来出人头地。而否认我们这种权利的人则说明,他没有忠于自己公开宣扬的那些人类平等原则。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应该允许我们拥有这种权利。我们应该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个受到损害的种族,应该拥有要求得到补偿的权利。然而,我却不要求这种权利,我要的是属于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我认为,非洲种族拥有尚需借助文明和基督精神进一步展现出的独特之点,而这些特点,倘或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在道德伦理方面,甚至属于更高的一类。
在斗争和冲突的开始时期,掌握世界命运的权力,赋予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个民族的坚忍不移、朝气蓬勃的素质,完全宜于肩负这一使命。然而,作为基督徒的我,则期待着另一时代的兴起。我相信,我们站到了新时代的边缘,那震荡着各国的剧痛,我希望只是兄弟情义和世界和平诞生时刻的分娩阵痛。
我深信,非洲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符合基督精神的一种发展。他们倘或不是一个占主宰地位、发号施令的种族,起码是一个充满仁爱、宽宏大量而又乐于饶恕的种族。经历了受天召唤来到不义和压迫的熔炉里的磨炼,他们应该更加深刻地牢记,那仁爱和宽恕的崇高原理。只有通过它,他们才能获取胜利,而他们的使命,也正是在整个非洲大陆传播这一原理。
坦白地说,这种原理,在我个人身上十分浅薄。在我的脉管里,足足有一半是孟浪暴躁的撒克逊血统,但我身旁始终有一个雄辩的传播福音的使者,那就是我美丽妻子本人。我彷徨之际,她那更加温柔的精神,每每使我迷途知返,在我眼前不断展示出基督对我们种族使命的召唤。我要作为符合基督精神的爱国者,作为基督教牧师,奔赴我的国家,上帝为我挑选的光荣的非洲!对于她,我在心里有时使用那些美丽的预言:“你虽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159]
你一定会说我是个狂热派,会说我对自己想从事的事业没有仔细考虑过。不过,我考虑过了,也计算过所付出的代价。我去的利比里亚,不是传奇中的福地,而是一个艰辛劳动的所在。我期待着用双手去劳动,努力地劳动,不顾种种困难和挫折地劳动,一直到我去世。这才是我为了什么到那里去,在这一点上,我肯定不会失望的。
你们对于我的决心,无论作何看法,但请不要对我丧失信心,而要认识到,我无论做什么,都将自己整个的赤诚之心,奉献给了我的人民。
乔治·哈利斯
几个礼拜之后,乔治便偕同妻子、儿女、姐姐和岳母,乘船前赴非洲。如果我们没有估计错误的话,人们还将得到他的消息。
至于其他的人物,除了对奥菲丽亚小姐和托普茜交代一笔,再专用一章的篇幅向乔治·谢尔比道别之外,作者再没有什么可以讲述。
奥菲丽亚小姐把托普茜带回了佛蒙特州的老家。新英格兰人以“我们的人”这个词语来称呼的那伙办事有条不紊的严肃人,很是吃了一惊。“我们的人”起初觉得,托普茜的到来,对于他们料理得头头是道的居家生活,既多余,又不相配。然而,奥菲丽亚小姐诚心诚意,恪尽自己的教养职守,收效全面,成绩斐然,孩子很快赢得了家人和邻居的喜爱和垂青。到了成人年纪时,根据她个人的要求,托普茜受到洗礼,成了当地教会的教徒,而且显露出了自己的颖慧、才干和热情,渴求对人世多行好事。因此受到推荐并经批准后,前往非洲一个教会充当了传教士。而且听说,她的幼年成长过程中,那使她花样翻新、永远静不下来的活力和机敏,现在已经更安全、更有益地用于对自己国家儿童所进行的教育中去。
附记:此外还有一则令母亲们欣慰的消息:由于都德夫人进行过多次寻查,结果于最近发现了凯茜的儿子。由于精力充沛,他先于母亲几年逃亡,由北方受压迫的朋友所收容,并受到了教育。不久,他也将前赴非洲去找寻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