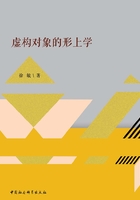
第五节 总结
根据前文分析,针对指称虚构对象现象、存在量化虚构对象现象和意向虚构对象现象,实在论者可以提供系统、简单、直接的解释。针对这三种现象,都尚未出现令人满意的反实在论解释。因此,我们有理由主张实在论解释,坚持虚构对象实在论。
针对实在论,前面论证是解释性的。我们仅仅指出支持实在论的证据,并论证针对这些证据的支持力的反驳意见都不成功。也就是说,假如承认虚构对象这类实体,我们将能够为待解释资料做出更合理的解释,至少到目前为止如此。然而,假如将来会出现可接受的反实在论解释,这里的论证便会丧失说服力。毋庸置疑,理论上,这样一种可能性似乎总是存在的。在此意义上,我们的辩护是间接的。那么,针对实在论,是否存在恰当的直接论证甚至证明呢?我们能否根据一些自明的前提和原则直接地推出实在论立场?
实际上,不止关于虚构对象的实在论面临这种问题。一般地,关于本体论立场,正如阿姆斯特朗所指出,本体论立场无法像数学和逻辑那样能被证明或证伪,也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找到可靠的信念辩护。[72]在笔者看来,对于本体论立场的最好辩护是所谓“最佳解释论证”。比如,阿姆斯特朗的共相实在论,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M.戴维特(M.Devitt)的常识实在论,都是诉诸最佳解释论证。仅以戴维特的常识实在论为例。根据戴维特的常识实在论,存在可观察物理对象。针对可观察物理对象实在论,我们能为其提供一个正面论证或证明吗?他认为,除了最佳解释论证之外,关于可观察物理对象的实在论无须更多辩护。其中,最佳解释论证思路如下:特定条件下,好像(it is as if)草坪上存在一只乌鸦,对此最直接的解释是,因为草坪上存在一只乌鸦,所以好像草坪上存在一只乌鸦。假若没有更好的解释,戴维特得出结论说,既然这个实在论解释是更好的解释,那么物理对象实在论成立。[73]
在笔者看来,好像虚构名字指称虚构对象,好像虚构对象被存在量化,好像虚构对象被意向,对这些现象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虚构名字就是指称虚构对象,虚构对象就是被存在量化,虚构对象就是被意向。既然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实在论解释便是最好的解释。笔者同样认为,除了这个最佳解释论证外,关于虚构对象的实在论无须更多论证。
实际上,的确有实在论者尝试对实在论进行“直接”论证(即非解释性论证)。在结束本章之前,笔者对两个著名的尝试进行简单评价。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论证的启发性大于合理性。
沃特里尼认为,为了给出虚构作品的同一化条件,必须承认虚构对象,这构成针对虚构对象实在论的直接的真正的本体论论证。[74]虚构作品被看作是依赖语言结构的语义性实体。沃特里尼设想,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写出具有相同语言结构(即包含相同虚构名字、相同谓词、相同修饰语且语词的组合结构也完全一样)的虚构文本。他认为,此时两个虚构文本对应两个不同的虚构作品。既然两个虚构文本的语言结构完全一样,决定所涉虚构作品差别的只能是在语义上,而谓词的语义以及量词等修饰语的语义与通常语义并无不同,没有差别。因此,差别一定发生在诸如虚构名字的单称词项的语义上,就是说,两个相同的虚构名字指称两个不同的虚构对象。简言之,为了解释虚构作品之不同,必须承认虚构对象之不同,因此,必须持有包含虚构对象的实在论。
作为一个实在论者,笔者当然同意沃特里尼的结论,但是,对该论证的说服力持保留意见。的确,一个人如果承认虚构对象,那么,承认虚构作品是非常自然的选择,毕竟虚构对象就是虚构作品中的虚构对象,虚构对象不能脱离虚构作品。但是,沃特里尼先承认虚构作品,然后论证说承认虚构对象是给出虚构作品同一条件之必需。这样的论证思路是令人质疑的,理由有二。其一,对于反实在论者而言,虚构作品实在论可能同样是可疑的。比如,虚构作品反实在论者可能会只承认虚构文本,但不承认虚构作品。这种态度自身并不会导致自相矛盾。关于虚构作品实在论的合理性,至少是存在争议的。其二,沃特里尼的论证依赖于一个假设,即在他所设想的情境下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虚构作品,而在笔者看来,这个假设并非确实。实际上,笔者认为,若两个人果真独立地写出相同的文本,他们便写出了相同的虚构作品,所涉虚构角色当然也便是相同的,这是更加符合直觉的。[75]
汤姆逊认为,虚构对象存在的条件是现实存在的,是没有争议的,因此,没有理由不承认虚构对象。[76]在汤姆逊看来,语词“虚构对象”(或“虚构角色”)的意义和用法本身便保证了虚构对象实在论的合理性,换句话说,使用“虚构对象”一词的言语行为具有以言行事的效果,效果之一就是创造相应的虚构对象。“否认虚构角色却从事关于虚构的实践便是扭曲了诸如‘虚构角色’等词项的日常用法……说‘简·奥斯汀(J.Austen)写了一个虚构作品假装指称艾玛’,然后说‘艾玛这个虚构角色出现在简·奥斯汀的虚构作品中’将是多余的。”[77]简单讲,人们的日常文学实践加上语词“虚构对象”的日常用法,便决定了必须承认虚构对象。
在笔者看来,汤姆逊的论证表明了一点,即虚构对象实在论与人们日常对“虚构对象”或“虚构角色”的用法和文学实践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一致性能否保证实在论的合理性呢?对此,笔者持保留态度。反实在论者可以一致地承认所有关于虚构对象的实践,承认关于虚构对象的谈论是有意义的,却并不承认虚构对象。前文提到的各种反实在论策略早已表明如此。作为一个实在论者,笔者同意汤姆逊的观念,即基于日常的文学实践和诸如“虚构对象”的理论词项的通常用法,而持有实在论立场是个自然的选择,但是,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支持关系或者推出关系呢?对此,笔者持保留态度。
笔者认为,沃特里尼和汤姆逊所做论证的效力是可疑的,但是,却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沃特里尼的论证带来的启发至少有两点。其一,虚构对象与虚构作品密切相关,若承认其中一类实体,最好也要承认另一类实体。如果已经承认了虚构作品,为什么还要费力消除虚构对象呢?其二,一个虚构对象理论若能同时回答虚构作品的本性问题,将是更加有吸引力的。[78]汤姆逊的论证带来的启发是:纵使缺少直接的论证,与反实在论相比,实在论也具有一个显见的优势,即我们的文学实践和关于虚构对象的谈论本身都“指引”我们接受虚构对象,包含虚构对象的本体论是最自然不过的选项。
最后,引用范英瓦根的文字来为本章的辩护工作做个有用的注脚:
“十九世纪的英国形上学家F.H.布拉德莱(F.H.Bradley)曾经说过,形上学是一种为那些你无论如何都会相信的事情找坏理由的尝试……有一件事几乎确定为真,亦即:无论我看到过多少哲学论证,都会去接受这样一些信念。当然,我会尝试尽量公平且客观地讨论与我立场相反的观点,不过,我不太可能会做得很成功……我曾经看过一些形上学的书,试图纯粹透过逻辑论证的基础,以及对细心收集到的资料所做的客观评断,而去辩护自己的立场。这些作者的写作方式,如果不是要暗示他们在形成其形上学主张时是没有偏见的,便是要暗示他们会将自己的偏见摆在一旁,而只考量证据与论证。我不是宣称能看穿别人的心思,但我怀疑有任何形上学家能够做到这点。”[79]
回应本章议题:我们是否应该持有包含虚构对象的本体论?对笔者而言,与反实在论相比,相对而言,实在论是更加合理的。笔者无意断言,实在论便是“正确的”本体论。然而,假如本章的论证是合理的,那么,我们至少拥有三类证据主张实在论,即指称虚构对象现象、存在量化虚构对象现象和意向虚构对象现象。在笔者看来,这三类现象展示的正是,关于虚构对象实在论的强烈直觉背后所隐含的根据之所在。[80]笔者认为,对关于物理对象相关现象而言,假如物理对象实在论是一种有用的本体论,那么,对虚构对象相关的现象而言,虚构对象实在论同样是一种有用的本体论。因此,假如物理主义是可接受的,那么,在同样意义上,虚构对象实在论也是可接受的。
[1] 扎尔塔曾尝试用具体性或者“占有时空”对“存在”进行解释(E.N.Zalta,Abstract Objects:An Introduction to Axiomatic Metaphysics,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3,p.52)。普莱斯特也曾做过类似定义,认为“存在”等同于“占有时空”或“拥有因果效力”(G.Priest,Towards Non-being:The Logic and Metaphysics of Intentionality,Secon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xxvi-xxviii)。
[2] 范英瓦根曾明确指责梅农式“存在”是神秘的词汇,是缺乏合适解释的技术词汇(P.van Inwagen,“Creatures of Fiction”,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14,No.4,1977,pp.299-300)。
[3] I.康德(I.Kant)将“存在”看作是逻辑谓词,而不是真正的谓词。前半句肯定性说法与这里的第三点吻合。后半句否定性说法与这里的第二点吻合。关于康德的存在观,可参见克里普克的说明性解释(S.Kripke,Reference and Exist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35-36)。
[4] W.V.Quine,“On Individuation of Attributes”,in his Theories and Thing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0-112.
[5] W.V.Quine,“On What There Is”,in his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orporated,1961,p.19.
[6] “包含”指的是“包含至少一个”。假设本体论O1包含柏拉图式理念和数学实体,而本体论O2仅仅包含数学实体。我们知道柏拉图式理念和数学实体都是抽象对象。因此,基于这里定义,关于抽象对象,O1和O2都是实在主义的,因为O1和O2都包含至少一个抽象对象。
[7] 根据该定义,说一个人是实在论者或反实在论者一定隐含着某个范畴标记。只有关于一类实体的实在论者或反实在论者,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实在论者或反实在论者。
[8] W.V.Quine,“On Individuation of Attributes”,in his Theories and Thing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0-112.
[9] M.Devitt,Realism and Trut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14.
[10] 根据传统定义,这里“反实在论”可能意味“虚构对象不存在”,也可能意味“虚构对象存在但依赖于精神而存在”,因此,“存在关于虚构对象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并不能准确表达这里涉及的分歧。
[11] 本章第四节将考察意向虚构对象现象。这类现象反映在语言上即意向性陈述,比如“彼得崇拜福尔摩斯”。意向性陈述也是对现实本身的断言,而不是关于虚构内容的断言,因此,应当归入到外虚构陈述。然而,意向性是一个引发哲学争论的重要哲学概念,因此,有必要对意向虚构对象现象特别进行讨论。因此,在内/外虚构陈述区分的基础上,笔者将外虚构陈述所处语境划分为普通外虚构语境和特殊外虚构语境。意向性语境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外虚构语境。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处理的是普通外虚构语境,第四节处理的是意向性语境。另外,读者将会看到,在第二章讨论虚构对象理论的解释力时,笔者也将创造性真理单列出来。在那里,创造性真理和意向性真理都被看作处于特殊外虚构语境。有了这里的说明,可知这与我们对虚构语境的分类并不冲突。
[12] 比如,创造主义者范英瓦根和汤姆逊认为,“福尔摩斯是一个侦探”要被分析为“根据故事福尔摩斯是一个侦探”,说的是,根据某个特定的故事,福尔摩斯这个虚构对象具有“是一个侦探”这个属性。一般地,内虚构陈述要进行重述,不能直接地进行解读。详细说明,请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A.普兰廷加(A.Plantinga)认为,“福尔摩斯是一个侦探”这样的陈述不能说是真的,也不能说是假的,因为它并不是真正地用来做出断言(A.Plantinga,The Nature of Necess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53)。
[13] B.Russell,“On Denoting”,Mind,Vol.14,No.56,1905,p.491.
[14] 用G.赖尔(G.Ryle)的术语来讲,罗素的思路是:(1)—(4)这样的陈述“在语法意义上关于福尔摩斯”,但是,并非“在指称意义上关于福尔摩斯”。关于这两种意义的区分,请参见G.Ryle,“About”,Analysis,Vol.1,No.1,1933,pp.10-12。
[15] S.Kripke,Reference and Exist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7.
[16] S.Kripke,Reference and Exist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2.
[17] W.V.Quine,“On What There Is”,in his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orporated,1961,pp.7-8.
[18] W.V.Quine,“On What There Is”,in his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orporated,1961,p.9.
[19] A.Church,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Logi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p.8.
[20] 简单讲,G.弗雷格(G.Frege)引入含义实体的目的是解释同一陈述认知差异难题。比如,“长庚星是长庚星”是无须任何经验观察便可知的平凡真理,相对照,“长庚星是启明星”却是需要大量经验观察和推理才可知的重要天文学真理。假如名字的意义仅仅在于所指称的对象,那么,看起来,上面两个陈述便应该是同义的,也因此,不可能承载不同的认知价值。弗雷格的主张是:名字的意义包含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指称对象,另一个维度是表达含义,而且含义决定了指称。一个陈述所承载的认知价值不但与它所包含的符号的指称有关,还和这些符号所表达的含义有关。概言之:在弗雷格看来,因为“长庚星”和“启明星”所指对象相同,所以,“长庚星是长庚星”和“长庚星是启明星”都是真的;但是,“长庚星”和“启明星”所表达的含义并不相同,这决定了两个陈述所承载的认知价值并不相同,一个是平凡真理,另一个却是重要的天文学发现。关于引入含义的动机、含义的形上学特征、含义的语义学功能,欲了解弗雷格的主张和论证,请参见G.Frege,“Sense and Reference”,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57,No.3,1948,pp.209-230。
[21] 比如,“我相信鲁迅是《朝花夕拾》的作者”和“鲁迅是周树人”看起来并不能推出“我相信周树人是《朝花夕拾》的作者”,因为很可能我并不知道鲁迅就是周树人。同一替换律失效提示我们此处的“相信”是内涵语境的标识。弗雷格认为,在内涵语境下,名字指称的是含义,而不是通常所指,并将所指的含义称为“间接指称”(G.Frege,“Sense and Reference”,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57,No.3,1948,p.212)。
[22] 弗雷格式反实在论策略被看作针对虚构名字和确定描述语的一个一般分析策略。
[23] 请类比弗雷格的著名例子“启明星是长庚星”。“启明星”和“长庚星”的含义不同但是指称相同。这里,“A就是B”是在故事中成立的同一陈述。
[24] T.Parsons,“Fregean Theories of Fictional Objects”,Topoi,No.1,1982,p.85.
[25] G.Frege,“Sense and Reference”,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57,No.3,1948,p.211.
[26] T.Parsons,“Fregean Theories of Fictional Objects”,Topoi,No.1,1982,p.82.
[27] F.Adams et al.,“The Semantics of Fictional Names”,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78,No.2,1997,p.130.
[28] F.Adams et al.,“The Semantics of Fictional Names”,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78,No.2,1997,p.135.
[29] 布朗曾是一个反实在论者。他通过空缺命题为虚构陈述提供语义解释,并认为关于虚构对象的看起来为真的陈述实际上表达的是关于虚构内容本身的命题(D.Braun,“Empty Names”,Noûs,Vol.27,No.4,1993,p.466,note 8);后来倒向实在论,持有包含虚构对象的本体论(D.Braun,“Empty Names,Fictional Names,Mythical Names”,Noûs,Vol.39,No.4,2005,p.609)。
[30] D.Braun,“Empty Names”,Noûs,Vol.27,No.4,1993,p.464.
[31] F.Adams et al.,“The Semantics of Fictional Names”,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78,No.2,1997,p.132.
[32] S.Brock,“Fictionalism about Fictional Characters”,Noûs,Vol.36,No.1,2002,p.11.
[33] S.Brock,“Fictionalism about Fictional Characters”,Noûs,Vol.36,No.1,2002,pp.8-14.
[34] 布洛克将这种处理方法称为“关于虚构对象的虚构主义”,就是说,他将诸如(1)—(4)的外部陈述当作某种虚构内容,而实在论理论就是包含这些虚构内容的“故事”。因此,在他看来,实在论理论正如故事一样是“假的”,并不是“真实的”,就是说,并不成立。下文中读者将会看到,笔者对此并不认同。
[35] S.Brock,“Fictionalism about Fictional Characters”,Noûs,Vol.36,No.1,2002,p.9.
[36] S.Brock,“Fictionalism about Fictional Characters”,Noûs,Vol.36,No.1,2002,p.14.
[37] 关于诸如(1)—(4)陈述的“常识性”,请参见J.Goodman,“A Defense of Creationism in Fiction”,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Vol.67,No.1,2004,pp.137-142;A.Thomasson,“Fictional Entities”,in A Companion to Metaphysics,J.Kim et al.ed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9,p.12。关于这些陈述的“科学性”,范英瓦根认为,它们属于“文学评论”这个理论学科。文学评论是对文学作品的内容、本质和价值进行严肃研究的学科。他认为,与物理学进行比较,文学评论和物理学都是理论学科,物理学属于狭义科学,但文学评论不是;然而,文学评论和物理学的共同点之一是能够提供真理,前者提供关于文学作品的真理,后者提供关于物理实体的真理(参见P.van Inwagen,“Creatures of Fiction”,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14,No.4,1977,p.303)。笔者同意,文学评论这个理论学科的科学性并不能与物理学等同,但是,两个学科都能各自提供真理。形上学家的兴趣在于,这些真理带来的形上学后承是怎样的。
[38] 比如,作为反实在论者,亚当斯也会认为有义务对这些陈述的真理性做出合适的解释,而不是逃避解释义务。
[39] F.Adams et al.,“The Semantics of Fictional Names”,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78,No.2,1997,p.130.
[40] S.Brock,E.Mares,Realism and Anti-realism,Stocksfield:Acuman Publishing Ltd.,2007,p.215.
[41] J.R.Searle,“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New Literary History,Vol.6,No.2,1975,p.330;S.Kripke,Reference and Exist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23-24.
[42] A.Everett,“Against Fictional Realism”,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02,No.12,2005,p.640.
[43] M.Crimmins,“Hesperus and Phosphorus:Sense,Pretense,and Reference”,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107,No.1,1998,pp.2-8.
[44] F.Kroon,“The Fiction of Creationism”,in F.Lihoreau ed.,Truth in Fiction,Munich:Ontos Verlag,2010,pp.219-221.
[45] P.van Inwagen,“Creatures of Fiction”,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14,No.4,1977,p.303.
[46] B.Russell,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Lond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01.
[47] 内部陈述牵涉的是假装有现实的人或物被指称并具有相应属性。埃弗雷特认为,外部陈述同样牵涉假装,只不过是假装有“虚构对象”并具有相应属性。
[48] 或许埃弗雷特式反实在论者会尝试论证虚构不是基本概念,若如此,他们有义务提供恰当定义。埃弗雷特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定义。假若果真存在这样的定义,这里的论证效力或被削弱。假若如此,基于前面做出的第一点和下文将要做出的第三点批评,笔者依然认为埃弗雷特式反实在论策略没有吸引力。特别是,如第一点指出的,笔者认为诸如(1)—(4)这样的外虚构陈述并不是虚构性的,而是真正的真理。这决定了布洛克式反实在论策略和埃弗雷特式反实在论策略都是没有吸引力的。
[49] A.Everett,“Against Fictional Realism”,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02,No.12,2005,pp.645-646.
[50] 范英瓦根提供了更为复杂的例句。比如,“有些19世纪的小说中的有的角色,其外形特征描写所含的财富细节要比任何18世纪小说中的任何角色都要多”和“有的小说中的角色紧密地以现实人物为模型,而另外的一些角色却完全是文学想象的产物,而且通常很难仅仅通过文本分析获知哪些角色属于哪种范畴”(P.van Inwagen,“Fiction and Metaphysics”,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Vol.7,No.1,1983,p.73)。
[51] T.Parsons,Nonexistent Object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p.32;P.van Inwagen,“Existence,Ontological Commitment,and Fictional Entities”,in M J.Loux et 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taphys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37-138;S.Kripke,Reference and Exist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69-70.
[52] K.J.J.Hintikka,“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s and Existential Commitments”,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56,No.3,1959,p.133.
[53] 所谓“自由逻辑”,就是摆脱存在预设原则限制的逻辑(logic free of existence assumption),具体可参见K.Lambert,Free Logics:Their Foundations,Character,and Some Applications Thereof,Sankt Augustin:Academia-Verlag,1997。
[54] 在本章第二节中,我们展示了指称虚构对象现象,然后论证实在论能够为该现象提供更好的语义解释。第二节的讨论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指称虚构对象现象是需要被严肃处理的语义现象。但是,我们在那里并没有为此进行论证。这里将要做的工作,实际上恰恰表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日常语言中的指称虚构对象现象,应该被看作是需要被解释的语义资料,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将之处理为指称失败现象。这实际上对第二节工作构成有益的补充。
[55] 帕森斯构造了类似的对话(T.Parsons,“Referring to Nonexistent Objects”,in J.Kim et al.eds.,Metaphysics:An Antholog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9,pp.36-37)。帕森斯设计的对话用来说明指称非存在对象与指称失败不同(“非存在”是梅农意义上的非存在)。这里,笔者用来说明指称虚构对象与指称失败不同。帕森斯用“门口的那个人”来说明指称失败现象。笔者也选用“门口的那个人”。这个确定描述语是个著名的例子,对其使用至少可追溯到奎因(W.V.Quine,“On What There Is”,in his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orporated,1961,p.4)。设计对话时,笔者并没有选择诸如“燃素”(Phlogiston)或“火神星”(Vulcan)这样的名字。这是因为纵使在虚构对象实在论阵营内部,关于这些名字的指称特征,也存有争议。比如,范英瓦根认为,“燃素”和“火神星”只是被科学家错误地认为有所指称,但实际上没有指称任何对象(P.van Inwagen,“McGinn on Existence”,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58,No.230,2008,p.58);萨尔蒙(N.Salmon)和D.布朗(D.Braun)却认为,它们都有指称,燃素与火神星是被科学家创造的抽象对象(N.Salmon,“Nonexistence”,Noûs,Vol.32,No.3,1998,p.305;D.Braun,“Empty Names,Fictional Names,Mythical Names”,Noûs,Vol.39,No.4,2005,p.615)。
[56] P.van Inwagen,“Why I Don’t Understand Substitutional Quantification”,in his Ontology,Identity and Mod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33-34.
[57] D.Braun,“Empty Names”,Noûs,Vol.27,No.4,1993,p.463.
[58] 比如,布朗认为简单的空缺命题都为假(D.Braun,“Empty Names”,Noûs,Vol.27,No.4,1993,p.463)。
[59] D.Braun,“Empty Names”,Noûs,Vol.27,No.4,1993,p.468.
[60] R.B.Marcus,“Nominalism and the Substitutional Quantifier”,in her Modalities:Philosophical Essay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19.
[61] 这不是量化语言经典语义学要求的一部分。一阶量化语言的模型定义允许有的对象没有名字。
[62] 这是量化语言经典语义学要求的一部分。根据模型定义,一个名字必须获得论域中的一个对象作为其指称。
[63] 这里假设坚持量词替换式解释者也会承认TC是成立的。就是说,在名字N有指称的情况下,“φ(N)”为真,当且仅当,“φ(x)”对N所指称的对象为真。坚持量词替换式解释者,是要避免没有指称的名字给解释存在量化语句带来的麻烦,对名字有指称的情况的处理,与坚持量词对象式解释者并无不同。
[64] P.van Inwagen,“Why I Don’t Understand Substitutional Quantification”,in his Ontology,Identity and Mod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35.
[65] P.van Inwagen,“Why I Don’t Understand Substitutional Quantification”,in his Ontology,Identity and Mod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36.
[66] R.B.Marcus,“Nominalism and the Substitutional Quantifier”,in her Modalities:Philosophical Essay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20.
[67] R.M.Chisholm,“Beyond Being and Nonbeing”,in J.Kim et al.eds.,Metaphysics:An Antholog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2,pp.36-37;S.Kripke,Reference and Exist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61.
[68] R.W.Rapaport,“An Adverbial Meinongian Theory”,Analysis,Vol.39,No.2,1979,p.75.
[69] 下文会多次出现表示意向方式的副词,有些地方的表达会显得不自然。比如“苏格拉底式地崇拜”,是很不自然的中文表达。实际上,对应的英文(“Socrates-ly admiring”)也是不自然的。诉诸形如“苏格拉底式地”的表达式是构造AC理论的需要。为了表示强调和引起读者的注意,下文出现的所有表示意向方式的副词,都将用黑体下划标出。
[70] R.W.Rapaport,“An Adverbial Meinongian Theory”,Analysis,Vol.39,No.2,1979,p.76.
[71] 一般地,M.彭德贝瑞(M.Pendlebury)用这种策略处理心理体验(M.Pendlebury,“In Defence of the Adverbial Theory of Experience”,in F.Orilia et.al.eds.,Thought,Language and Ontology,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p.102)。这里考虑的是,AC论者特别地用该策略来处理意向性问题。
[72] D.M.Armstrong,“Reacting to Meinong”,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No.50,1996,p.617.
[73] M.Devitt,Realism and Trut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74-75.
[74] A.Voltolini,“How Fictional Works Are Related to Fictional Entities”,Dialectica,Vol.57,No.2,2003,pp.225-238;A.Voltolini,“Précis of How Ficta Follow Fiction”,Dialectica,Vol.63,No.1,2009,p.54.
[75] 笔者还会对这种情形进行更多讨论,具体见本书第六章。
[76] A.Thomasson,“Fictional Characters and Literary Practices”,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43,No.2,2003,pp.138-157.
[77] A.Thomasson,“Fictional Characters and Literary Practices”,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43,No.2,2003,pp.150-151.
[78] 笔者将在第七章提出自己的虚构对象理论,在那里,笔者将严格界定什么是虚构作品(故事)、虚构作品的同一条件、存在条件以及虚构作品与虚构对象之间的关系。
[79] [美]彼得·范英瓦根:《形上学》,苏庆辉译,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1—22页。
[80] 为何支持实在论的证据会恰恰分为语义和意向性两个维度呢?或许是因为虚构对象的本性会牵涉语义和意向性。比如,有的实在论者认为,虚构对象就是语言用法创造的实体(S.Schiffer,“Language-Created Language-Independent Entities”,Philosophical Topics,Vol.24,No.1,1996,p.157)。有的实在论者认为,虚构对象就是依赖于主体意向性的实体(A.Thomasson,Fiction and Metaphys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