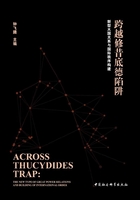
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1]
陈志敏[2]
“新型大国关系”是近年来中方提出的外交话语,以定位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形态。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时任国务委员的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3]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进一步提出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后,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核心话语。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次出访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共同呼吁在大国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4]李克强总理也在5月出访印度期间提出要发展中印新型大国关系。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用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5]对于中方提出的这一外交话语,美国方面也有积极的回应。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隆在3月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中美要建立“一种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a new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an existing power and an emerging one);[6]奥巴马总统也在6月与习主席见面时表示要推进“美中新型关系”(new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7]
本文试图从学理的角度来探讨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问题:它如何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关系?它可以呈现为哪些具体的可能形态?这些形态之间有何递进的水平差异?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路径有哪些?
一 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
亚历山大·温特从他的三种无政府体系文化出发界定了国家之间的三种关系形态。温特认为,国际体系本质上没有最高权威,仍然是一种无政府体系。但是,根据国际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或文化的不同,他认为无政府体系至少可以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结构或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基于不同的角色关系,即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霍布斯文化的逻辑是“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丛林法则。国家之间相互视为敌人,国家的政策是随时准备战争,争取消灭敌人。洛克文化基于一种特殊的角色结构——竞争,其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竞争对手共同认识到,相互行为的基础是相互承认主权,因此不会试图去征服或统治对方;另一方面,洛克文化中的行为体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相互竞争。此外,温特也发现,“二战”后,西方国家间一种新的康德文化正在出现,其逻辑是“多元安全共同体”以及“集体安全”,成员之间的角色关系是一种朋友性质的关系。[8]
中国国防大学的刘明福教授也提出了中美关系情景下大国关系的三种分类。他提出,中美双方如果互为“敌手”,在罗马角斗场搞你死我活的“角斗比赛”,不惜热战,势必同归于尽;中美双方如果互为“对手”,在拳击比赛场搞你败我胜的“拳击比赛”,不惜冷战,势必两败俱伤;中美双方如果互为“选手”,在田径赛场上进行你追我赶的“田径比赛”,虽然会有你先我后的位置变换、会有冠军亚军的名次之分,但是双方都会刷新纪录、创新成绩。在这类“田径比赛”中,比超越别人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超越了自己,都赢得了自己,因而可以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刘教授对“中美田径赛”里中国“夺冠”的前景具有“必胜”的信念,但并不认为美国“必败”。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并不是美国的失败,一个在比赛中创造了超越自己原来成绩纪录的亚军,比一个在比赛中成绩没有新突破的冠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9]
澳大利亚首相陆克文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了中美关系的三种形态,即“热战、冷战和凉战”,并担忧地认为,中美关系必须要摆脱凉战形态。在他看来,虽然中美关系既不是热战,也不是冷战,但双方之间存在的“战略信任赤字”,即存在于中美之间的隔阂,如果不加遏制,这种隔阂可能破坏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10]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细分出至少七种国家间关系的形态:热战敌人关系、冷战对手关系、恶性竞争关系、良性竞争关系、双边伙伴关系、传统盟友关系和共同体成员关系。
在热战敌人关系下,大国之间进行着传统的争夺权力和霸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惜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常常陷入大国争霸战争的泥潭,给各自国家也给世界带来惨痛的破坏。在冷战对手关系下,比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超级大国建立各自控制下的国家集团,相互对抗。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制约,两大超级大国在核恐怖平衡下维持了相互之间的非战状态,但世界生活在频繁的代理人战争和核战争的阴影之下。在恶性竞争关系下,大国之间虽没有热战和冷战关系中的严重对抗,但存在着激烈的相互拆台式的竞争,追求我赢你输的目标。在良性竞争关系下,大国间能够为竞争确立一定的规则,双方之间的竞争不以损害对方利益为最高目标,而是比拼谁能够做得更好。这更像是刘明福所谓的“田径比赛”,或选美比赛。大家以自己的实力在公平竞争的规则下争取第一的桂冠。在双边伙伴关系下,大国之间发展出合作机制,主动管控双方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在协调中追求共同利益的实现。在传统盟友关系下,国家之间结成安全同盟关系,承诺在对付外来军事侵略或威胁方面相互支持,包括军事支持。盟友关系是一种紧密合作的关系形态,但这种同盟的存在,对非同盟国构成压力,常常会激发国际安全困境,并成为主导国获取世界事务支配权的工具。在共同体成员关系下,国家之间有竞争,更有合作,且这些竞争受到普遍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合作得到国际规则的促进和保障,也能保证大国之间的合作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积极贡献。
二 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和理想形态
在七种大国关系的可能形态中,从否定性定义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应该不是热战敌人关系,也不是冷战对手关系。即使对于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敌我关系的美苏两霸而言,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持了40多年的相互非战状态。基于同样的道理,在相互核威慑有效存在的前提下,中国和有关大国之间的非战状态也能得到延续,中国和有关大国也能避免美苏之间的冷战状态。如同郑必坚曾经阐述得那样,与苏联在冷战时期走上了军事争霸的道路不同,中国在1979年以后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一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中国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而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11]因此,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是高度相互依存状态下的关系,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既没有完全敌对的利益冲突,也没有全面敌对的意识形态矛盾,无须依靠恐怖核威慑在大国之间维系和平,陷入一种类似美苏之间的冷战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结盟经历教训深重。一种传统的安全同盟一方面会带来所谓的“牵连”效应,令中国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一方面带来“抛弃”效应,在中国需要盟友支持的时刻被盟友抛弃。总体上,传统盟友关系是成为主导性盟友实现自身优先利益的工具。从中国的这一结盟经验出发,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确立了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原则。尽管近年来有关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联盟体系的呼声有所抬头,但不结盟这个中国外交的主导性原则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需要讨论的是,新型大国关系也不能是恶性竞争关系这一形态。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大国之间必定会出现影响力的竞争、经济竞争、发展模式竞争以及文化竞争等。但这种竞争如果是恶性的,那么,国家之间关系很容易滑向冷战关系形态,就像陆克文担心中美之间出现凉战状态一样。在恶性竞争下,国家之间虽没有军事冲突,甚至也没有冷战关系下的代理人战争,但它们会在相互关系的各个领域力图损害对方的重要利益,忽略双边合作的绝对利益,只追求自己的相对利益,千方百计地在削弱对方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把这种恶性竞争作为一种传统大国关系的形态单列出来,可以丰富我们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否定性定义。
从肯定性定义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形态包括良性竞争关系、伙伴关系和共同体成员关系。构建与有关大国的伙伴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的一大主题。经过将近2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与30多个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还与很多其他国家发展了合作伙伴或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一个伙伴关系中,两国之间建立起各种合作机制,推动和落实合作项目,确保关系具有总体合作的特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个全新的外交话语和实践,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起步的伙伴外交战略。

图1 大国关系的主要形态
尽管伙伴关系是中国力争实现的大国关系形态,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即使是中国的合作伙伴,甚至是战略合作伙伴,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中也不乏竞争。如前所述,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大国政治不可避免的一面,我们毋庸讳言,也无法否认。中国在争取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已经在经济上成为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大国,超过了俄罗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并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而且,如果发展顺利,中国也有望在下个10年中赶超美国,直取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地位。在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国早已在大批产品的生产上成为世界第一。在国防预算上,中国也超越了很多传统的国防支出大国,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在发展模式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羡慕中国的发展经验,西方国家也感到其“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所谓“北京共识”的挑战。因此,大国关系必然有竞争,这种竞争将继续下去;而且,中国也参与了竞争,并希望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所以,新型大国关系一定包含竞争关系,认识并承认竞争关系的存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务实地看待新型大国关系。当然,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竞争必须是良性的,是在公平竞赛的原则下进行的,是竞争谁做得更好,而不是相互拆台,以打败对手为最高目标。在2013年7月举行的中美第五届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了中美之间确立良性竞争的重要性。代表中国政府的汪洋副总理表示:“如果中美之间存在竞争的话,这种竞争也应该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进行的良性竞争。”[12]美国副总统拜登也说,中美关系是并将继续是竞争和合作的混合体;对双方而言,竞争是好事,而合作则是必需。对于中美这两个有影响的大国而言,出现竞争是最自然的事情。如果游戏是公平和健康的,政治和经济竞争可以激发出中美两个社会最好的能量。[13]
笔者还认为,共同体成员的关系也应该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形态。中国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一些人士在2009年提出的“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这是正确的选择。国际事务的处理不能由两个国家(即使是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来自行决定。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国际事务由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来共同决定。这并不排除作为国际体系的重量级成员,中国和其他大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事实上,追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并将继续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目标。关键是,中国和其他大国不能独断地为世界制定规则,而是要让各国有效参与,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而为国际事务建章立制,让各国的行为都受到国际规则的调节。在公正、公平和有效的国际规则下,大国关系就转化为国际共同体的成员关系。目前,中国和其他大国已经具有初级水平的共同体成员关系,受到了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贸易组织规章为代表的国际规则的约束。今后,各国能否继续强化在各个领域的国际制度,将决定大国之间的共同体成员身份是否能够进一步深化。
考虑到良性竞争、伙伴和共同体成员关系的合作水平不同,其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我们也可以把三种形态视为不同水平递进而又相互并存的三种新型大国关系。良性竞争是新型大国关系的起步形态,只有摆脱了热战、冷战和恶性竞争,大国关系才显现出新型关系的特征;伙伴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力争形态,在这一形态下,大国关系才具有更多合作、互利和共赢的内涵,新兴大国关系才会更加稳固;共同体成员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理想形态。在笔者看来,只有在国际社会进入了各国共同建章立制,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有共同的规则约束时期,国际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和普遍繁荣。这是各国,也应该是中国未来追求的理想境界。当然,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现实,这样的前景并不必然实现,但仍应该作为一种理想形态加以追求。
三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路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思考。
1.从传统大国关系到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出现历史上的霸权争霸战争或美苏之间的冷战关系的概率已经很小,但形成恶性竞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此,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最主要的是要防止恶性竞争的发展。这需要中国采取四管齐下的对策:一是拓展共同利益,来压缩恶性竞争的空间。在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更为发展的今天,中国和各大国的关系中有广泛的现实和潜在的共同利益,如何对这些共同利益达成共识,并通过合作来实现这些共同利益,将有效压缩恶性竞争的存在空间。二是要制定良性竞争的规则,让竞争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大国之间的竞争如果有规律可循,明确何为恶性竞争,何为良性竞争,将有助于大国更好地处理相互之间的竞争问题,让竞争成为竞优的比赛。三是采取更为平常的心态,来看待国际竞争或国家软制衡的现象。基于对恶性和良性竞争的区分,我们可以对良性的竞争行为采取更为平和的心态,而不是将对方的任何竞争行为都视为恶性竞争,并对恶性竞争行为进行回应,以防恶性竞争升级,使相互不信任强化为相互敌意,从而导致两国关系沦落到冷战形态。四是明确战略底线,来遏制恶性竞争的发展。一旦一国面临另一大国的恶性竞争,该国也需要明确自己的战略底线,宣示对方的行为已经越过良性竞争的底线,损害到一国的重要或核心利益,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不过,任何反制措施的实施应本着威慑的性质,目的是促使对方撤回有关的恶性竞争行为,回到良性竞争的轨道上来,而不是要让恶性竞争升级。在此过程中,反制措施要具有真实的制约效应,且该国须有真正实施该反制措施的决心,以便这类防御性反制措施真正具有威慑的效果。
2.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下提出的,在中美关系上使用最多,且新型大国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最为突出。在国内学界,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只适用于中美关系。但是,新型大国关系就字面意义而言必然是一个一般性的概念,势必带来有关大国对号落座的反应。英国《金融时报》就有一篇文章表示:“在中国单方面把它与美国的关系升级为两个平等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同时,中国实际上是把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降级’了。”这篇文章还说:“但按照中国受‘两国集团’概念启发而形成的新世界观,所有其他国家(美国除外)都不符合超级大国的定义,因此是可以抛弃和无视的。”[14]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正像习近平主席在俄国以及李克强总理在印度都谈到要发展中俄与中印新型大国关系一样,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外交应该适用于中国和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关系发展。除了和主要的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外,中国也应与具有超国家特征的地区国家联合体,如欧盟,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为此,笔者也建议把新型大国关系的英文表述,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改为new model of relations be tween major countries。
3.从低阶新型大国关系到高阶新型大国关系。如前所述,新型大国关系本身有多个形态,且依据合作水平以及对世界的贡献水平有高低之分。良性竞争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家之间合作较少,但良性竞争能够激发各国国家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以各自的发展推动世界发展,为其他国家带来好处。比如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竞争多于合作,但如果各自都能为非洲的发展带来切实的好处,都可以在非洲获得高水平的好感,则这种竞争就是健康良性和值得欢迎的。最近美国皮尤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的结果显示,在非洲受调查的六个国家中,美国和中国的影响都被认为对本国有高度积极的作用:尼日利亚(66%;80%)、肯尼亚(69%; 75%)、加纳(60%; 59%)、塞内加尔(77%;71%)、乌干达(75%; 69%)和南非(64%; 53%)。[15]如果两国有更多的积极合作,在伙伴关系下,两国关系会更加稳定,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并可能对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积极的溢出效应。在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伙伴关系形态方面,中国可以继续推行在过去20年中行之有效的伙伴外交战略,并通过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将大国合作层层推进,比如从合作伙伴,到全面合作伙伴,到全面战略伙伴,以至具有一定准联盟性质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共同体成员关系形态,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可以受到普遍国际规则的限制和约束,两国合作也会更加有保障地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当然,以国际社会民主的方式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通常是困难的,但如果大国之间能够发展起比较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更加全面和有效的国际规则也不是不可能的。
4.从新型大国关系到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关键任务。但是,新型大国关系外交既不是中国外交的全部,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他外交配合的情况下单骑突进。本着新型大国外交的精神,中国应该主张更为全面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主体出发,中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外交要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外交,也要包括新型大小国外交,以及新型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外交。新型大小国外交指的是中国作为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建设问题。中国在历史上曾发展出“以大事小、以小事大”的处理大小国关系的外交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又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今天,当中国重新成为真正的大国,如何处理国家间主权平等,同时又要兼顾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需要我们用新的观念来发展新型大小国关系。此外,中国作为大国如何构造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也需要中国学界同人来加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