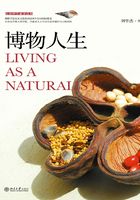
2.2 格斯纳与作为人文学术的博物学
普林尼博物学的百科全书研究进路,持续了1500多年,素材虽然在不断地增加,但基本风格没有实质变化。
这期间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博物学变得更有市场了。在中世纪学术界变得有些沉闷,草药学却在缓慢而坚实地积累材料。到了16世纪中叶,博物学与其他学术一样,全面复兴。科学史家的研究表明,在这之前从1490年代到1530年代,学者们做了两件事:(1)恢复有关动植物之历史和药用方面的希腊文作品和拉丁文作品;(2)在现实生活中辨识古人所描述的物种。而这类工作不是某几人做成的,它是一个共同体集体努力的产物。
虽然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但此时的博物学仍然不具有我们现在熟悉的面孔。那时的博物学与现在人们理解的博物学有很大差别,它们在内容上不是更接近19世纪的作品而是更接近公元1世纪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是作为整体的文艺复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准确地体认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博物学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所有先入之见抛在一边,才能了解本真的文艺复兴博物学”(W.B.Ashworth, 1996: 17)。
下面主要根据科学史家阿什沃斯(W.B.Ashworth)的研究进行叙述。那时的博物学有何特点?最好的办法是打开一卷16世纪的博物学作品,看看上面都有哪些内容。翻开有代表性的格斯纳(Conrad von Gesner, 1516—1565)的《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就能领略那个时代的博物学。格斯纳生于苏黎士,对植物、动物和多种语言颇有研究。五卷本《动物志》被认为是现代动物学的发端,主要讨论了四足兽、鸟、鱼和蛇。现在,瑞士医学史与科学史学会(SSHMS)的会刊名字就叫《格斯纳》。
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书中的动物画也是相当精美的,包括真实存在的或者传说中的动物。 以“狐狸”(vulpis=fox)为例,可以分析格斯纳作品的一般结构(W.B.Ashworth, 1996:17-37)。论狐狸的部分共占16个对开页,如果折算成16开本,大约有60页。开头有一幅木刻狐狸画像,接下来为由A到H共8节的文字描述。A节是一小段,主要描述名字:vulpis在法语中写作regnard,在英语中写作fox,在荷兰语中写作vos,此外还列出了在其他大量古代和当代语言中的对等词语。B节描述不同地区狐狸的差别,比如俄罗斯的狐狸红色中有点发黑,西班牙的狐狸通常是白色的。不过,它们也有共性,如都有长毛尾巴。C节描述狐狸的习性和活动,它独特的叫声、它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它的饮食、是否可食以及可药用等等。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格斯纳阅读了无数前人的著作,把与“狐狸”相关的事实、传说、格言几乎全部汇总起来了。格斯纳是极有造诣的厚古薄今的古典学者。对格斯纳来说,博物学依然主要是在图书馆中汇总前人文字材料,而不是建立在个人直接与大自然打交道基础上的一门观察性科学。“格斯纳是一名人文学者,至少在他眼中,博物学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追求(humanist pursuit)。”格斯纳是坐在书房中的博物学家,与今日时常跑野外的博物学家差别很大。
以“狐狸”(vulpis=fox)为例,可以分析格斯纳作品的一般结构(W.B.Ashworth, 1996:17-37)。论狐狸的部分共占16个对开页,如果折算成16开本,大约有60页。开头有一幅木刻狐狸画像,接下来为由A到H共8节的文字描述。A节是一小段,主要描述名字:vulpis在法语中写作regnard,在英语中写作fox,在荷兰语中写作vos,此外还列出了在其他大量古代和当代语言中的对等词语。B节描述不同地区狐狸的差别,比如俄罗斯的狐狸红色中有点发黑,西班牙的狐狸通常是白色的。不过,它们也有共性,如都有长毛尾巴。C节描述狐狸的习性和活动,它独特的叫声、它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它的饮食、是否可食以及可药用等等。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格斯纳阅读了无数前人的著作,把与“狐狸”相关的事实、传说、格言几乎全部汇总起来了。格斯纳是极有造诣的厚古薄今的古典学者。对格斯纳来说,博物学依然主要是在图书馆中汇总前人文字材料,而不是建立在个人直接与大自然打交道基础上的一门观察性科学。“格斯纳是一名人文学者,至少在他眼中,博物学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追求(humanist pursuit)。”格斯纳是坐在书房中的博物学家,与今日时常跑野外的博物学家差别很大。
最长的H节中列出了狐狸的各种秉性,如诡计多端、狡猾、不诚实等等,并且都配以大段的经典引文,这相当于一部“词源”,在此我们能找到foxy这一形容词具有的所有含义。格斯纳列出了狐狸作为隐喻的各种例证,包括《圣经》中狐狸的所有“出场”。在H节的后面,在没有任何说明和过渡的情况下,格斯纳列出了一些格言、寓言。初学者一开始搞不懂H节为何汇集了这样一些杂乱的内容。前面的若干节虽然也杂乱,但毕竟与狐狸的习性等还直接相关,但H节似乎根本不像是博物学,因为这与大自然没什么关系。在其他节中毕竟引用的还是亚里士多德、普林尼、阿伊连(指用希腊语写作的罗马博物学家Claudius Aelianus,175—235,著有《论动物的本性》),迪奥斯柯瑞德(Pedanius Dioscorides, 40—90)、大阿尔伯特等权威人物,而在此节我们遇到的则是普兰努德(Maximus Planudes,1260—1330)、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69—1536)、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i, 1492—1550),在通常的博物学著作中根本不会见到这些名字。

格斯纳《动物志》中的插图:鹰。作者不详。

格斯纳《动物志》中的插图:犀牛。作者为丢勒。
作为科学史家,阿什沃斯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让人们换种思路来理解格斯纳、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那个时代的博物学。格斯纳愿意用如此大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讨论有关狐狸的称谓、形象、寓言、象征等等,我们难道不应该假定这样一种可能性:动物象征主义的知识是16世纪中叶博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吗?我们现在的博物学中不再考虑符号、象征,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不同。如果我们多了解一些伊拉斯谟和阿尔恰托这两位巨人对格言和象征的关注,就会更好地理解文艺复兴文化及其博物学的特点(W.B.Ashworth, 1996:20-23.)。我们也再次看到布鲁尔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中所述“知识”定义的重要性。
格斯纳的博物学,在我们看来有许多缺点,比如不够纯粹、简明、准确、客观,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述说的狐狸具有极大的丰富性:维度非常多,“古今中外”,包含了与狐狸有关的人与自然的几乎所有知识。特别是,它不是关于对象的客观主义的学问,而是人与自然共同体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学问,而他本人首先是人文学者。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宽广的智识框架(intellectual framework),博物学正是在此框架内得以生根发芽、走向繁荣的(B.W.Ogilvie,2006:11)。即使到了博物学正式诞生的18世纪,布丰的《博物学》仍然被视为文学作品,被普遍阅读和收藏。1994年考斯莫斯国际奖获得者、法国自然博物馆的巴罗(Jacques FranÇois Barrau, 1925—)教授在评论布丰的《博物学》时指出,“博物学过去和现在都打上了人文文化的烙印”,今天,博物学对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有用的(舍普等,2000:6)。中国魏晋时期的博物学,更是人文主义的学问(于翠玲,2006:107)。
从维拉(Giorgio Valla, 1447—1500),沃吉尔(Polydore Vergil,1470—1555),维佛斯(Juan Luis Vives, 1493—1540)三位人文学者所编写的百科全书来看,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对动植物的讨论越来越多,前人所做的零星探索被汇总起来,这一切努力为18世纪严密的博物学研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B.W.Ogilvie,2006:2-4)。在中世纪,博物学的探索多分散在“医学理论”和“自然哲学”的标题之下。而在文艺复兴之前,受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影响以及自然哲学的影响,人们对自然事物的关注,更集中在大而化之的机理上,集中在关于原因和结果的抽象叙事上,不大重视对个体物种的记录、考察和描述。
奥高维(Brian W. Ogilvie)研究了从1490年到1630年间的四代博物学家,他发现虽然他们的关注点和工作方式有许多不同,但是他们之间有连续性,并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即“描述”(description),他们工作的过程和结果都表现为“描述”(B.W.Ogilvie, 2006:6)。他们追求对自然事物描述的准确性,并且指责古人对事物描写得不恰当、不精确。从1530年代到1630年代,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具雏形,它的中心工作就是描述大自然,把大自然中的奇异的、普通的造物分类、编目。认真测量、仔细记录和描写,可能是文艺复兴那个时代共同的文化气质,表现在文学、绘画、医学解剖、天文观测和对动植物的考察上。“描述”既涉及技术也涉及理论。
博物学家做着一些琐碎、细致、艰苦的工作,但从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就是人文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们从来没有被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牵着走,也许并非他们不向往胡塞尔所反思的数学化,而是当他们面对大自然造物的惊人的复杂性时,不得不保持谦虚。另外,这个领域相当长时间里有着自然神学的传统,这也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研究对象实在太复杂、太精致了,他们自觉地把对象的设计归结为上帝的智慧,而且不认为在短时间内人类能够完全搞清楚上帝创造万物的秘密,更不敢轻易尝试通过人的智识努力而与上帝一比高下,制造新的物种。
西方博物学的历史发展可粗略分出若干阶段和类型。第一阶段是草创期,以亚里士多德和老普林尼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准备期。第三阶段是林奈和布丰的奠基期。第四阶段是直到19世纪末的全盛期。第五阶段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衰落期。
博物学家五花八门,类型至少可分出:“亚当”分类型、百科全书型、采集型、综合科考型、探险与理论构造型、解剖实验型、传道授业型、人文型、数理型、世界综合型,等等。(刘华杰,2010a: 64—73)有的人物会同时在几种类型中出现,由此也可以看出博物学与实验科学甚至数理科学是平滑过渡的。限于篇幅,不可能对每一类型都讨论一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人文型的兴起和特点,这一类型与现象学所讲的“生活世界”关系密切,对于沟通科学与人文、培养人们热爱自然和保护自然都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