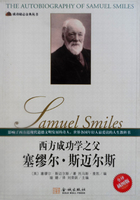
第8章 滚石不生
1834—1837年——乡村医生
在我的哈丁顿朋友当中,有一位名叫乔治·斯考拉,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尽管天生体质孱弱,他却有一个活跃的、想象力丰富的头脑。跟当时的每个人一样,他也是个狂热的政治家,对改革事业极感兴趣。他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一场为援助自治改革向议会请愿的公开会议上。令他的朋友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面色苍白、身体虚弱、额头大得使脸都黯然失色的人,居然也能发表这般铿锵有力的演讲。他说出了请愿者的心声,请愿被热情地采纳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演讲,一次比一次讲得好。但他的身体太虚弱了,承受不了这样的脑力劳动。后来,他患上了肠系膜病,被人送到了我这里。为了给他换换空气,我把他和他姐姐送到了爱丁堡附近的波特贝洛,并派人请来了我的老导师麦金托什大夫,作为顾问医师为他看病。大夫尽了力,可他已经病得无可救药了。回到哈丁顿不久,由于病情恶化,他最后安详地死去。
在波特贝洛跟麦金托什大夫见面的时候,他问我在哈丁顿的事业进展得怎样了。
“没有什么进展,”我说,“我快要混不下去了。”
“怎么啦?”
“医生太多了,”我答道,“多得足以叫人口翻番啦。”
“唔,”他说,“可要记住‘滚石不生’这个道理啊。”
“确实是这个理儿,”我说,“可是,自从我在那儿落脚以来,我什么都没有‘生’出来,我想,我最好还是‘滚’吧。”
“好啦,当然,你自己的决定才是最好的。”
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我的另一个朋友是北贝里克郡的卡斯泰尔斯大夫,那儿离哈丁顿有9英里远。他年纪与我相仿;跟我一样,也在为找生意而奋斗。他住在海边,住处一面临海,另一面靠着陆地,因此,能供他行医的村子就更少了。有一次他得了咽喉炎,卧病在床,就问我愿不愿意过去,代他出诊。于是我去了他家,逗留了几天。有一天,他派我去给邹克·怀特克罗斯这个品格高尚的人看病,他是坎提湾的一个渔夫。坎提湾是一个小渔村,差不多正好坐落在坦托隆古堡遗址内。邹克租下了离村子只有几英里远的鲈鱼岩,它是福斯湾上的一块圆形大石。在那儿,塘鹅嘎嘎直叫,海鸟飞来飞去。
不久前,邹克失去了他的儿子——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在风大浪急的海上翻了船,尸体被海水冲上了岸,几乎就在他父亲门口。邹克在提到这件令人悲伤的事时,对邻居说,“啊,伙计,那天,那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呀。”邹克只好每年送给教区牧师12只塘鹅作为“赎罪品”。可牧师却抱怨他送的鹅太少了,而且吃起来有股鱼腥味儿。有一天,邹克把所有的塘鹅都送到了牧师那儿,可牧师比从前更不满意了。
“我不能杀生”邹克说,“可把它们送给您,您也不满意,现在我把它们都送来了,任您处置吧。”
邹克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轶事,然而,这却是最后一个。我发现他染上了最严重的一种霍乱。当我赶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当我离开的时候,他就断了气,这是乡村医生常常看到的场面。
一天夜里,我被派往距离哈丁顿约7英里远的雷德豪斯出诊。看完病以后——这次也是免费出诊——我骑着那匹老母马往回走。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的光景,由于前两天也是熬夜出诊,我觉得困得要命。下山的时候,马踩到了一块石头,跌倒了。我从它头上掉了下去,一头扎在我的白帽子上,帽子压坏了,可就是它救了我的脑袋。我站起身来,彻底清醒了,可马却从山上摔了下去。我走了约四英里路,发现那可怜的家伙站在我几天前出诊过的人家的门口,膝盖摔坏了。我告别了它,再也没有买过马。
1836年——我的第一部作品
为了打发大把时间,我做了许多事,其中的一件事就是写书。这是一件麻烦事儿,不过,我下定了决心,勤奋地读书学习,还写了书稿,准备出版。我的主题是“体育教育”,这是个不错的主题,因为库姆贝大夫的《如何保持健康——生理学法则的运用》被认为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这让我想到,一部专门指导如何培养和管教孩子的著作,也许会一样有用。不管怎样,人的一生总是从受教育开始的。因为哲学已经错在没有更深入地从生理上对人进行研究,所以,人的道德也就止步不前。我把佩利[34]的下面这段话作为这本书的箴言: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否拥有健康和美德,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因此,无论什么因素,只要可能对它们产生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影响,都应该马上引起父母的重视。所以,我谈到了孩子的看护、环境营造和体格训练方面的问题;我力图阐明,对孩子进行早期体育训练是道德塑造和智力培养的基础;同时,我反对把不必要的知识塞进这些年轻的脑子里。
为写这本书,我竭尽了全力。但是,它的出版本该更顺利呢。不久后,安德鲁·康姆贝大夫的著作《论儿童的生理和道德管理》的确顺利地出版了。可当时我正在写我的书,不知道这位优秀的大夫也在写这样一部专题论文。完稿后,我把手稿交给爱丁堡的查姆伯斯兄弟,他们那时正致力于许多娱乐书籍和实用书籍的出版工作。我跟威廉·查姆伯斯见了面,他告诉我,康姆贝大夫会为他们出版社提供一部类似的作品。由于随身带着手稿,于是我又找到了朋友博伊德先生(奥利弗·博伊德出版社),请他提供印刷和出版这部小论文的费用预算。结果,它很快就付印了。但在它出版前,我收到一封来自威廉·查姆伯斯的信,信上说他对康姆贝大夫的作品感到失望,并将自己出钱出版一部专题论文,请我把手稿给他读读。可这太晚了,我的书出版了,并受到了《图书馆》、《议事期刊》及另一些刊物的好评。
我只印了750本。书相当畅销,不过,只要它物有所值就行了。在后来几年里,销售受益都被广告费耗尽了,最终还剩下100本没有装订的书。这些书,我是按以下方式处理的。我朋友的亲戚斯莱特先生,曾在伦敦出版了一系列廉价图书,包括爱默生的散文集和弗雷德里加·布莱梅的故事集,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廉价丛书”。尽管它们销量很大,可价格却极其低廉,最后叫出版商破了产。斯莱特把这些书收起来,准备去澳大利亚继续做他的书商生意。他问我可否给他一点儿“赞助”,于是,我把那些没卖出去的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希望它们对殖民地的居民和他们的孩子会有所帮助。后来我得知,斯莱特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定居在季隆[35],在妻子的帮助下,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1838年——离开哈丁顿
我必须提一提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因为这对我将来的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个职业就是为一家爱丁堡报社撰写主要文章。当时《爱丁堡周报》的编辑是托马斯·默里博士,他是一位政治经济学演讲家。我认识这位博士,他有时会请我交一些报导文章。我做的比他要求的多了一点儿,是定期交文章给他的。终于,他把我的文章登上了主要专栏,我也开始以“我们”的口吻写文章了,就象我就是编辑一样。我成了一个定期撰稿人,就象后来默里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重要撰稿人。”这不就证明了这是通向出版社的大门吗?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当《泰特报》打出一则广告,要招聘一位《利兹时报》编辑,以接替于1837年12月去世的诗人罗伯特·尼科尔的时候,我申请了这个职位。
我接到了报社经营人的复信,要我寄一份能证明我实力的样文——就选举权为题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附在回信上寄走了。文章通过了,但他们却通知我说,基于长远考虑——因为《利兹时报》遭到了新报《北极星》——宪章派和极端激进分子的机关报——的强劲抵制,他们认为必须任命一位报社工作经验十分丰富的先生为编辑,他就是当时《太阳报》的编辑查尔斯·胡顿先生。毫无疑问,他是个极有造诣的人,一位能干的作家,也是《比尔贝里·瑟兰德历险记》、《科林·克林克》等精彩小说的作者。我不能对这个结果抱怨什么,因此也就彻底放弃了这个愿望。毫无疑问,另外的机遇总会来的。
同时,我把自己的财产安排了一下,卖掉了药品存货,准备离开哈丁顿。1838年5月,我离开了哈丁顿。我打算前往莱顿[36]或海德尔堡[37],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外,还打算学习德语,进修法语。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带上了一些推荐书——它们来自我敬重的牧师霍格先生、恩师格雷厄姆先生、老友伯顿大夫、我的邻居以及担任乐队大提琴手的教区长李,还有许多我所挚爱的朋友和熟人——离开了故乡,乘船向赫尔进发。
伯顿大夫真诚地说,“在人口有限,而且也不再增长的地方,在市场被老一辈专业执业者占据了的地方,留给年轻医生——无论他多有才能——大显身手的机会少的可怜,因此,他们不必浪费时间去受这种煎熬;我相信,你走的这一步是明智的,无论你在哪里落脚,你理当成功,你也会取得成功的。”在这儿补充一下,卡斯泰尔斯大夫已经离开了北贝里克郡,在塞菲尔德[38]落了脚,他在那儿干得很好;克鲁克夏克大夫后来也离开了哈丁顿,在北贝里克郡行医,最后去了澳大利亚;伯顿大夫自己不久后也去了沃尔索耳[39],在那儿把生意做大了。
我还要补充一下,在我离开哈丁顿之前,我被推选为镇议会议员,如果我再等等的话,我或许还能当上市政官呢!可我等不了了,因为我想谋生,因此,我得物色另一个行当的工作。
1838年——荷兰之行
我安全抵达赫尔,休息了几天以后,我登上了前往鹿特丹[40]的“海马号”轮船,经过24小时的愉快航行,我到达了目的地。我在一家英国旅馆里住了几天,在慕名参观了布姆吉斯——一座沿着河岸延伸了约1.25英里远的码头,并参观了整个镇区的公共设施、运河和桥梁以后,我拜访了苏格兰牧师史蒂文斯先生,因为我有一封写给他的推荐信。他友好地接待了我,还向我提供了有关莱顿大学的许多信息,了解到这些信息以后,我决定去莱顿大学攻读学位,尽管我还有一封写给海德尔堡的泰德曼教授的推荐信。我坐着运河专用平底船,经由特莱克斯库特前往莱顿,这种船是当时流行的交通工具。
我们穿过肥沃的平原地区往莱顿进发,经过了农舍、村庄、风车、菜园、绿油油的牧场,以及从小桥底下向四面八方蔓延的河道。接着,这座古老的大学城出现在眼前,在落日的映衬下,房屋高高的尖顶成了黑色暗影。同船的一位客人把我领到了老城区的一个家庭旅馆,我在那儿逗留了几天。这家有一位男主人、一位女主人、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经营着这个小小的家庭旅馆,而我是唯一的客人。父亲和两个女儿是音乐爱好者,我很喜欢他们的表演。我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还了解了荷兰的许多民风民俗。
我及时地参加了医学院院长范·德·霍文教授等人的入学考试。这次考试没有几年前爱丁堡大学的那次考得那么全面。由于考官操着一口不正规的拉丁语,有许多信息我都不得而知,考试费也比我想象得贵得多,几乎让我掏空了钱包。不过,第一次考试结束后,我还有足够的钱按原计划徒步游览荷兰,沿莱茵河上行观光。6月15日清晨,我撇下行李,背着装有几本书和空白亚麻稿纸的背包,从东城门离开了莱顿。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灿烂。为了全方位地观察这个国家,我选择了步行。只要你喜欢,你可以手拄拐杖,背一个背包,沿着大路拐进小道;偶尔在乡村旅馆的门廊下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前进;你可以听听从原野那边远远传来的钟声,你可以仰望游云变幻,观察它们把紫色阴影投在地面显眼之处的过程;有时,空中的浮云会开一个口子,太阳从那儿投下一道道明艳的光束,照亮了远处风车的白色叶片,照亮了穿行在农场和牧场间的荷兰划艇上的白色风帆。步行是游览一个国家的正确方式。要全面地欣赏清新、健康和美丽的大自然,你必须步行;只有乐意在工作期间进行必不可少的体育锻炼的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愉悦[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