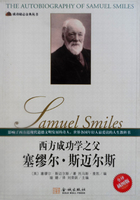
第3章 少年时代及所受教育
我曾经写过很多部作品,然而,在着手一份新稿的时候,我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展开以下叙述那样激烈地动摇过。如果不是哈德斯菲尔德的老朋友威廉·罗尔斯顿·海格的反复劝说,我或许不会产生把这些回忆记录下来的想法。这位老朋友是哈德斯菲尔德的地方官员,我常常在那儿受到他的热情款待;我在利兹和布拉德福的时候,也跟他有密切往来。
海格先生是一位十分睿智的人,也是一位伟大的读者,特别是在人物传记方面。多年以前他曾问我,“您写自己的传记了吗?”
“唔,还没有呢!”我答道,“我不可能把它写出来。我太忙了,此外,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确,像其他许多作家、艺术家等名人一样,我也曾接受过采访。可相比之下,我的一生却显得平淡无奇、空空如也。”
“空空如也?”我的顾问反问道。“哎呀,您的著作在英国和美国都拥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它们几乎被译成了欧洲每一种语言,还被译成了印度语,甚至泰国语和日本语。我敢肯定,您的访谈员们发表的那些文章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们很想对您有更多的了解。”
“也许吧,”我说道,“可我觉得,在我一生里,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公众感兴趣的东西。我的书应该自圆其说,事实也正如此,它们不需要我的传记来做推介。”
“得啦!”他最后说,“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吧:我相信,您的自传一定会比您的其他著作有趣得多。”
这是1897年的一次对话。我对朋友的劝告心存疑虑,而他却一再提起这个话题,甚至不辞辛苦地告诉我,应该怎样写自传。他帮我起了个头,洋洋洒洒写了4页纸。他还把约翰·巴川姆劝他的朋友本杰明·富兰克林写自传的建议抄给我看。
当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自传问世的时候,海格先生写信给我妻子,“告诉您的丈夫,让他也像特罗洛普那样,写一部自传。”我的答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著名的哲学家,安东尼·特罗洛普是杰出的小说家。成千上万的读者会去读他们的书,却少有人会去读我的书。他们有自己的历史,而我没有——至少,我的这些历史不值一提。不过,我将在业余时间里写一些与往事有关的文章,供我的子孙们消遣,或者,如我的儿子们所愿,供众人评说。
1812年——童年的回忆
我于1812年12月23日出生在哈丁顿。这座我睁眼看见第一道光的房子,坐落在主街的一端,从那儿能望见邮递马车、公共马车、会馆和星期五市场[1]。
大约在这个世纪初,拿破仑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这座小镇成了兵站的中心。3万多法国精兵在布伦集合——带着炮,马,还有运输工具——平底船——威胁着要对英国发动侵略。虽然结果证明这只是佯攻,但英国对此已有准备。有人认为阿伯雷迪海湾有可能是法国部队的登陆点,因此,军队在哈丁顿到处安营扎寨,安置步兵、骑兵和大炮。其余部队驻扎在丹巴附近的贝尔黑文。海岸线上竖起了灯塔,以及时发现法国军队的靠近和登陆。军营里,一队队民兵鱼贯而入,这是为维持常备军军力而进行的公开征召。
然而,拿破仑打败了所谓的“英格兰大军”,进而入侵澳大利亚、普鲁士和俄国。这场陆战持续了几年。那时候,威灵顿正带着他的胜利之师在英格兰半岛上奋战。到了1812年末,也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拿破仑正在收拾他的残兵败将退回法国,却在途经俄国的时候,遭到了大雪的封锁。在我们的小镇里,定期招兵还在持续,不断有民兵在这里安营扎寨。
接着,莱比锡战役打响了,拿破仑退回了法国,巴黎在遭到围攻后投降,拿破仑退位,逃到了厄尔巴岛[2];但不到一年光景,他又潜回法国,召集军队,向北挺进。随后,他兵败滑铁卢。回忆起当时欢欣鼓舞的情景,就跟一场梦似的——一队队民兵和鼓乐队在镇子里游行,后面还跟着彩灯队。第二年,苏格兰高地兵团第42军——“黑看守”——从镇上经过。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们每经过一座小镇,人们都会向他们报以热烈的欢呼;当他们进入爱丁堡的时候,人们的热情更是难以名状。
1815年——威尔士家庭
家人的谈话始终离不开战争,他们对近期的战事津津乐道。镇子周围的军营终于被拆掉了,军用物资也被卖掉了。我父亲[3]买来了大批军用物资,主要是毯子和大衣。我还记得一个农夫买走了最后一批军用大衣,扛在背上走了。
当时,粮食昂贵得要命。所有物品的赋税都高得不得了。一块4磅重的面包卖到了16便士,糖卖到了9便士或10便士,茶卖到了7先令到9先令,不过,苏格兰人的“生命支柱”——用来煮粥的燕麦,价格还算合理——尽管跟现在的价格相比还是贵了。
在我的童年时代,大哥约翰生病这件事让我深受震撼。他感染了肺炎,家人请来附近的约翰·威尔士大夫为他看病。大夫为他放了血,我还记得,我看见医生从他手臂放出来的鲜血装了满满3杯,杯子摆在桌上,等着大夫的下次来访。尽管约翰年仅7岁,但放血疗法很快就救了他的命。那时,大夫们已经不怕给病人放血了。几天以后,约翰下了楼,威尔士大夫又被请来为他看病。他把手指伸进约翰的汗衫松开的扣眼儿里,挠他痒痒,约翰笑出声来了。“哈!”大夫说,“他的肺全好了,他很快就可以出门儿啦。”
威尔士大夫是一位十分和蔼乐观的人。大家都喜欢他。他长着一副英俊标致的面孔,表情生动而丰富。他是镇上和周边地区数一数二的从业医生。就在约翰的病治好后不久,这位不得不面对各种风险的威尔士大夫,在为一位病人看病的时候感染了伤寒,暴病而亡,全村人都沉痛地悼念了他。
1820年——学校和同学
良好的教育抵得上一大笔财富。这是我父母的共同看法,尽管他们留给这个大家庭的几个孩子的钱比较少,但他们给予孩子们的早期智力教育,成了他们未来跟困难作斗争的最佳装备。约翰·诺克斯是个土生土长的哈丁顿人,“让大众受教育”是约翰·诺克斯的训诫之一。人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使穷困贫瘠的祖国变得繁荣了起来。苏格兰的教区学校和市区学校,以及在那儿所进行的教学活动,正是约翰·诺克斯学说的延伸。
我的启蒙老师是帕特里克·哈代。他在圣安街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我在这里学到了基础知识。几年以后,镇议会派哈代先生去市区学校教英文和数学,我也就随他赴职去了。
哈代是一位优秀的老师。他教的科目是阅读、写作和算术,他教得很好。他还培养了学生们的记忆天赋。他让我们先用心去记,然后凭记忆把诗歌和演讲稿背出来。我还记得当时,他叫我跟另一个同学尼斯贝特学霍姆的悲剧——《道格拉斯》里的一幕和《坎贝尔[4]诗集》里的一段名叫《巫师的警告》的长诗,然后让我们背出来,甚至还叫我们学习情节和修辞最复杂的文章。这些练习对我们来说大有裨益;多年以后,这些在学校里学到的文章还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作为老师,这些都是哈代的优点。不过,他还另有一些截然相反的特点。他是个暴君,还是个爱拍马匹的人。他宠爱的学生大多是教务长、市政官和镇议员的儿子,因为他的位置就是他们的父母给的;另一些宠儿则是富家子弟,因为他们的父母能给他吃、给他喝。我的父母并不是这种贵人,因此我也就不是一个受宠的学生。我父亲是一位自由教教徒——长老教的一种,他不愿意参加选举——因此,他也不可能当上镇议员或市镇官。哈代讨厌新教徒,特别是自由教徒,尽管他曾经也是个新教徒。
1820年——一位严厉的老师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最大的特点就是贪玩儿。我兴冲冲地盼望着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因为在那时,我们不是在打曲棍球,就是在沙地上踢足球,或者围着村子转悠,搜寻鸟巢、野李和山楂。尽管我是个好学生,但恐怕跟学习相比,我更爱玩呢。要不是有一天,哈代用他那种黑色幽默式的语气,亮开嗓门儿吐出了这句可怕的预言:“斯迈尔斯!你将会一事无成的,只有呆在你们镇上扫大街的份儿”,我就不会那么懂事了,这对一个小小的学生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学生们总爱模仿老师的“暴行”。他们爱模仿他激动时说的那些狠话;同学们还给我起了个“镇上扫大街的”绰号,但我不久就离开了学校,当查尔斯·谢里夫——一个蒙高韦尔斯的农夫的儿子——提起这些往事时,我早就把绰号的事忘光了。他比我还讨厌哈代,他说,他从那位老师那儿什么都没有学到。不过,这样说也不对,因为,尽管他很残暴,但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老师。
哈代有时会用最可怕的语言来对付他的学生。我曾听他说过:“看我不抽你,把你往死里打,”“看我不拿你脑袋往墙上撞,”“看我不把你脑袋打开花!”可怜那些被吓得战战兢兢的小学生们了!我曾亲眼看见哈代狠狠地抽打一个男孩,一直抽了好久,累得他不得不叉着腰,精疲力竭地瘫坐在地上。最后,由于体力不支,他才不得不停手。
他对自己宠爱的学生总是唯唯诺诺、甜言蜜语。后来,这些宠儿们常常去烧石弹(他的刑具),好把它们烧得又黑又硬,因为他们知道,哈代的皮带再怎么样也不会往他们背上抽。
哈代有时还暗中在别的学校上课。在规定学时里,哈代并没有好好地上拉丁文和希腊文课,因为这附近还有一所传统学校,也是由市政官赞助的;因此,他就能在放学后去那所学校上拉丁文课,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为我们上拉丁文课的时候,他要先上楼吃点儿东西再回来上课,这时他的情绪往往十分亢奋。有一次,他正听着詹姆斯·汤姆森——另一位自由教教徒的儿子——朗诵课文;可这伙计不太机灵,笨嘴笨舌的,后来他答错了一个问题,答得很愚蠢;哈代一听就上火了,把书狠狠地迎面朝他脸上扔去。书一侧的封皮划破了他的上唇。他顿时血流满面,课也散了。对于这些事,继任校长加菲尔德是这么说的:“我始终感到困惑,有哪个爱学习的孩子能受得了如此暴戾的学校教育。”
教师在教学上鲁莽而专横,孩子在学习上就不会有进步。这些言行足以促使一个孩子草率地干出蠢事。我一向很反感某些又懦弱又残忍的教师,就因为自己比孩子强大,便利用自己的权力折磨这些无助的孩子。
1820—1825年——格雷厄姆校长
当父母就要把我从哈代的学校领走的时候,我别提有多感激他们了。他们把我送进了隔壁的那所传统学校念书。哈代有多残暴,格雷厄姆校长就有多文雅。他俩的外貌和性格都截然不同。哈代脾气暴躁,面色苍白,头发红里泛黄,黑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光芒。而格雷厄姆身材圆肥,总是快快活活的,尽管有点儿自负,却很有幽默感;他喜欢引用拉丁语,对每一个孩子都笑脸相迎,不管他是不是市政官的儿子。石弹是哈代折磨孩子的刑具,尽管格雷厄姆也有石弹,他却从来不用。这所学校是以道德戒律来进行教学管理的,但学校却被管理得井然有序。我觉得,学校的每个孩子都喜欢老格雷厄姆。
这里的学生当然比哈代那儿的学生听话。他们中间大部分是英国人、印第安官员或东洛锡安地区大农场主的儿子。每一科的学习都是快乐的,没有憎恨,只有感激。我们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学习上取得了进步。我还记得一些趣事儿,可要费上好些篇幅呢。我不是一个成绩斐然的学生。夏季考试考到全年级第一或第二的学生,除了能得到满满一袋糖果,还能得到其他奖品,有的孩子还会抱上一摞奖品图书回家。
一所学校的宠儿和另一所学校的优等生,未来怎样呢?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惊世骇俗的成就。有的成了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叫人无法容忍,而优等生们也从神童沦为了失败者。家长实行的强制性教育对孩子毫无裨益。在生活这场斗争中,填鸭式的教育对孩子们来说也相当无益。
多年以后,原来的一个笨学生成了同学当中最成功的人。当时,哈代根本没法叫他把数学课听进去,他在学校也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一个又一个教师尝试过教他,可结果都一样。最后,父母把他从学校接了出来,交给一位家庭教师管教。接着,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智商。他父亲是一位大商人,父亲的突然去世使责任压在了这个独子身上,这一变故立刻唤醒了他的才智和良知,他开始打理父亲留给他的产业。他是个精力充沛、百折不回的小伙子,很快就把生意做大了。这个所谓的“笨学生”最终成了一位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名人,还当上了家乡的市长。
总之,如果能做到坚持不懈,这些让人们不抱什么希望的年轻人就能成为最成功的人。至于我自己,如果说我取得过什么值得让人铭记在心的成绩,那么我依靠的不是过人的天赋,而是适度的天赋、精力和勤奋专注的习惯。事实也的确如此。跟大家一样,我的知识大多来源于自学;我想,就我自己而言,自学的效果比老师教学更好。另外,我还保持了健康的体魄,这比任何奖品都好。锻炼,从兴趣和工作中得到的乐趣,对自己才能的运用,是一个孩子的真正生命力,也是一个成人的真正生命力。乡村生活也使我受益,为我带来了许多乐趣,让我见识了许多奇趣纷呈的事物。
1820—1825年——我的父母
我的本性和天赋跟遗传也有很大关系。孩子不仅是人类之父,还是其父母的精神和身体状况的继承者,也往往是其祖辈的精神和身体状况的继承者。对于我的家系,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父母是光荣而正直的公民的后代;他们除了要还债,还要拨出一部分钱用于孩子的教育。我父亲的祖宗是理查德·卡梅隆的追随者,其中有塞穆尔·德鲁蒙德。1666年11月,他在彭特兰湾参加盟约会议的时候,被当时由达西尔将军统领的苏格兰皇家骑兵团逮捕。幸运的是,藏在无边帽里的一本圣经救了他的命。这个家族的成员一直是改革长老会信徒,而我的祖父是长老会元老;我记得,当他们在彭特兰湾山区的一个村子里举行民间讲道的时候——塞缪尔·德鲁蒙德也曾参加过这种危机四伏的讲道——我也在场。祖父给我和哥哥约翰写过一封信,满纸都是善意的忠告,这封信我还留着。虽然信上没写日期,但我想应该是1821年写的,那时我9岁。
我母亲的祖宗是边境居民。她的父亲罗伯特·威尔逊是一位步兵少校的后代,在安妮女皇统治时期,他住在斯迈尔霍姆附近。罗伯特跟伊丽莎白·叶娄利斯结了婚,她是伊尔斯顿附近的考登娄斯的一个自由民的女儿。我母亲的一个堂兄,名叫乔治·叶娄利斯,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他在爱丁堡学习时,来了一趟哈丁顿,为我的父母画了几张肖像画,这些画我现在还留着。后来,他去了伦敦,在绘画上取得很大进步,最后被封为苏塞克斯公爵的内阁肖像画师。
我母亲的兄弟们,达尔克斯的威尔逊家族成员,都是聪明的机械师。最早的收割机之一就是乔治发明的,为此,达尔克斯农场俱乐部还给了他一笔奖金。大哥罗伯特是建筑工人,也是木匠,手头经营着大生意。
1820—1825年——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遵循了奥格[5]的部分箴言。他们既不屈从于贫困,也不为没有富裕的生活而沮丧。尽管食品昂贵,赋税也高,他们也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开支。他们有足够的钱——尽管有时需要做出自我牺牲——让孩子们接受教育。父母能把我们放在公平的人生起跑线上,尽管别人比我们拥有更多的金钱和赞助者。但这些都是短暂的,而教育给人的益处才是永久的。因此,我不能不深深地感激父母,是他们这么早、这么坚定地让我们踏上了求知的旅途。
父母为我们树立的另一个榜样就是勤奋——这比知识重要多了。有空的时候,母亲总是在纺车前工作;她不仅想维持家里那家店铺的亚麻布存货量,还想让女儿们能穿得好好的。但是,家里的人口增长很快,亚麻布和棉布也越来越便宜,纺车最终成了贮藏室里的闲置品。后来,我们不得不饲养奶牛,因为人们要用牛奶来伴麦片粥,作为孩子们的日常早餐。于是,牛栏搭起来了,在花园尽头跟房子连在一起。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园丁,他为自己种的报春花、郁金香、樱草等花草感到骄傲,当时,它们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们不得不帮父亲把花园打理得井井有条,尽管大多数人更愿意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出去玩,因为这两天下午,我们本来可以在泰恩河钓鱼、找鸟巢、爬加勒顿山、在华莱士山洞用自制的弓和箭玩爱国者游戏的。不过,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常常玩得热火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