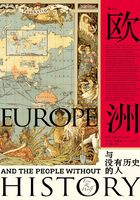
1997年版前言
自本书面世至今,15年过去了,似乎是适切的时机对成书的初衷与读者的理解做一回顾。此版前言也让我有机会澄清评论提出的几个问题,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批评的。
我以人类学家的身份撰写此书,书中也涉及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我试着提出历史的观点,分析跨越时间显现的结构与模式。我也尝试将人类学的发现与历史取向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联结在一起,尤其着重于历史的面向。“政治经济学”一词,通常被界定为关于社会与国家的资源如何集中与分配的研究,倾向于混淆两种问题取径。其一采取衍生自市场经济学的技术评定国家财政政策。另外一个取径,也是我所从事的,研究诸社会、诸国家与诸市场,视之为随历史演化的现象,并质疑当中资本主义的经验衍生的特定概念,是否可以普遍化以涵盖各时代和地区。我们必须特别记住,马克思将《资本论》的副书名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我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用以指称对于不同国家与社会的经济基础演变轨迹的怀疑。
我运用历史与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将人类学研究的群体摆置在更广的权力场中,此一权力场产生自控制社会劳动的权力系统。这些系统并不恒久,它们会发展与改变。因此,去了解它们如何在时间与空间中开展并影响更多人群很重要。尽管我以人类学家而非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本书,但我的确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去了解这些系统如何、为何发展并扩展对于各群体的支配也很重要,基于此,我尤其着重政治权力与经济如何彼此维持与相互驱策。尽管我并非经济学者,但我认为描绘深植于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学,对于了解决定并环绕人类生活四周的结构是极其必要的。我不同意某些意见,认为这无法告诉我们多少“真实的人民从事的真实的事”,我认为这正是此一取径所能说明的。或许就像“天国的馅饼”般是无法实现的许诺,但在现世如何派发馅饼仍旧是一个与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
如何以一个适切的书名描绘上述问题意识,着实煞费苦思。关于“没有历史的人”一词,我不敢掠美,其发明须追溯至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此语表述他们对于东欧的国家分离主义运动缺乏同情。我的用意是反讽的,但这层意思并没有为某些读者理解。我意在挑战那些认为仅有欧洲人造就了历史的想法。选择1400年作为展示这一点的最初时间点,我希望清楚显示出,欧洲在扩张历程中,四处碰上拥有长远与复杂历史的人类诸社会与诸文化。我主张这些发展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互相联系的,而这种相互关联的特质,于欧洲建立的世界亦然。欧洲扩张的历史与它包含的诸群体的历史交错,而这些群体的历史又会回过头与欧洲的历史发生联系。既然这些历史的绝大部分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有关,“欧洲”一语也可看作了解此一生产方式发展的捷径。此一生产方式孕育于欧亚大陆欧洲半岛,并逐渐支配其他各大洲的广阔地域。
写作本书的目的,并非提供范围广阔、涵盖全球的历史记录,或资本主义如何在全球扩张的世界史。初衷是为指出,我们无从适切了解人类诸社会与诸文化,除非能勾勒出它们历经漫长时空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倚赖。
我的断言具有实证基础,而不只因为我相信世上所有一切最终都彼此联结。在方法论上,过去社会科学中被称为“功能论”的分析仍然有用,特别是针对那些既不清楚、也不明显的内在关联。同时,我们也需不停自我提醒,任何组成结构的元素极少是稳定的,也极少回归最初的平衡状态。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被压力、矛盾、破裂的缝线标示出来,在更广大领域的互动产生的压力环绕下暴露出来。诸社会与诸文化永远是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兴起前的时代如此,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殖民全球更多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生活的现今,更是明显。此种扩张造成全球各地域的群体在社会与文化生活方面的巨大改变已是常识,但还有更重大的工作亟待进行,即概念化与解释扩张的原因以及带来效应的本质。
为了点出这些相互倚赖和影响,我援引马克思众多极为有用的有关“生产方式”的概念库藏。如同文中解释的,我发现此概念在分析上卓有成效,就智识而言也极为丰硕。此概念强调社会如何动员社会劳动,将重点放在人类个体和整体对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群对人群的社会关系,引导了这些关系的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结构,以及传递这些关系的思想。这些关系性的概念用途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重要遗产。
马克思思想于我而言是取之不尽的,对此我并无歉意。现今有一种倾向要将这套思想都丢到智识史的废纸堆中。我们必须自我提醒,马克思主义传统包含多种思想与政略,其中有部分远比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政治影响力最大的那些,要丰富。我有意使用“马克思的”(Marxian)一词,用以表明该传统的多样性,而非“马克思主义”(Marxist),因为此词的意涵已经被限缩成专指特定的政治。如果不能善用马克思的遗产,我们的智识与政治世界将陷入贫困,就如同社会学的门徒若因为马克斯·韦伯是热切的德国主义者便抛弃他,或物理学因为牛顿的秘密炼金术士身份便舍弃他,而造成损失那般。当然,并不需要将任何一位重要人物供奉在恒久不变的真理的万神殿,因为他们在各自的时代也并非总是正确,有时也会修正自己提出的理论与观点,某些诠释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就马克思而言,尤其要将他分析者与先知的身份划分开来。马克思的许多分析仍然启发我们,但他对于新的阶级“自在”(in itself)如何得到“自为”(for itself)的阶级意识的预测,即便在他的时代,也缺乏社会学的实证。
使用马克思的概念也意味参与一场为时已久的辩论,关于马克思传统作为看待世界的方式。此传统通常被认为可以划分出两个范畴,“系统马克思主义”(Systems Marxism)与“普罗米修斯式的马克思主义”(Promethean Marxism)。“系统马克思主义”期许成为一门科学,一门有着逻辑上相关的假定的学科,可以用来制定历史上社会发展的普遍定律。“普罗米修斯式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将人类自经济与政治的剥削中解放获得自由的愿望,赞颂革命的意志,并视革命为通往此一愿望实现的未来的必经道路。
部分读者以近乎相反的政治立场阅读《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将这本书看作“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操演,不是将它视为智识圈的“特洛伊木马”,就是哀叹它欠缺普罗米修斯式的热切。我的确引用了马克思的概念,但并非援引基本的意涵,即以归纳出普遍法则为目标的科学。我将这些概念看作是引导研究发现的假说。对一个范围更广的任务而言,它们仅是最初的估计,其后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将看到它们是否适用。此一努力也牵涉使用外加的或替代的解释策略。至于普罗米修斯,我想对于革命意志的颂扬和美誉更适宜去标记精英分子带领的革命,而非期许改变基础广泛的普罗人民运动。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本身也不怎么支持这一点。他偷盗天火并带给凡人的举动,其下场是被永远锁在山崖,肝脏为宙斯的隼鹰日日啄食。
我提出以上思考,以更清楚界定《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的主题。这本书并不是要介绍整合的全球发展的马克思理论。书中引用马克思的理论概念,是帮助我定位人类学研究的诸群体,在权力场域中他们成为研究对象。如同某些读者提到的,我的书并非针对理论概念的研究。如果我为此受责难,我只能说这就是我写的书,其他人可以写他们要写的。诸如我关注资本主义中重要商品的历史与分布,我的兴趣并不在于“商品崇拜”概念的问题意识,我的目标是展示商品的生产与贸易如何与生产出这些商品的群体发生关系,因为这一点影响他们的生活至深。
与某些评论指出的正好相反,我从未在这本书里或任何其他地方主张,被并入资本主义的网络就必然摧毁了诸群体独特的、植根于历史的文化理解与实践,使得既有的文化模式失去作用,不再相干。我的确将商品采集与生产者描绘为“资本主义的中介者”,如同我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工群体描绘为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劳动力赚取工资者。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全世界各个区域群体的生活已经愈发在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之下,包括那些提供劳动力待售的区域。这里并不是要提供更多“资本主义宇宙论”(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下“忧郁的转义”(tristes tropes)。资本主义或许有、也或许没有使得特定的文化失去活力,但资本主义太过赤裸真实的传散确实引发几个疑问,究竟接连被拉进资本主义运行轨道的诸群体,如何提出与更新他们的理解,以回应新处境带来的机会与危机?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意味民族志的终结。正好相反,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民族志,因为获知问题的答案不能仅仰赖理论。
为了更适切地评估关于人类行为本质某些未经检验的浪漫想法,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民族志。类似的想法日渐普遍,从对于本书的回响中也可以看出来。未经检验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能够随心所欲地表现和自我创造。另一种浪漫想法则是认为人类会本能地抵抗权威支配,并且“抵抗”可以被一元化地看待和研究。我相信这些就是类似思想的源头。人并非总是抵抗身处的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文化建构下重新进行自我改造。文化改造与文化变迁在多变的、但也是极为限定的环境下持续发生。这些环境会活化也会抑制,既引发也使得抵抗消散。只有实证的研究能回答不同的群体如何在他们各自的多变环境下形塑、适应或抛弃他们的文化理解——或相反地,发现自己受阻于达成以上这些。还有待我们解答的问题是,某些群体的文化理解为何与如何适应认同资本主义,由此更加繁荣,另一些却不然。
另外,我也要澄清资本主义概念于本书的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地也许同样都被资本积累与劳动力两者的动态互动所驱动,但此一动态互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外观形式与表现。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一书中,我把重点放在资本所有权与管理阶层雇用劳动力进行工厂生产的组合模式上,以此作为策略性手段,资本主义得以复旧其他种类的生产方式。在另外一些情形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在商业资本的挹注之下走得更远。在我看来,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控制与资讯技术,联同新的运输模式,足以支持分散化的资本主义,借由家户生产与“弹性的”工作坊强化资本累积。历史上,此一生产方式曾经屈从于扩张与收缩的阶段。不同阶段的改变,伴随包括产量调配、以生产为目的的技术与组织配制、工厂设备与市场的地理分布、工人招募与人事安排等变革。驱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也许是单一的,但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运作方式也造就差异化与异质的外貌。我在本书强调了此论点。当资本主义扩大影响范围并寻得新利基,它同时造就获取利润的多变方式。这些赚取利润的不同方案吸引新的劳动力、新的中产阶级与创业阶层的注意。由此,他们全都要面对如下问题,即差异的文化理解如何符合持续改变的政治经济的要求。而他们会如何适应,这一点无法事先预测。
最终,问出正确的问题并找到满意答案,要求我们回归基础的理论问题。所有的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在内,都横跨在两种真实之间,即自然世界的真实与人类借由技术与组织对它做的转化,以及人类彼此之间沟通习得的层级化、有组织的知识与象征操作的真实。两种真实的对比困扰着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的观点在内,并持续在人类学浮出水面,不论我们如何变着辩证的戏法希望跨越两者的区分。面对这个僵局的方法之一就是忽视它。某些人类学家视物质世界的行为为首要,对于人类自己的心灵活动报告并不照单全收。另一些以人类界定自身的心灵图式为优先,把物质世界的行为看作是理智世界的短暂现象。还有一些人务实地赋予行动与理念同等的重要性与价值,尽管他们推迟任何关于二者如何协调的讨论。
解答这个争议的关键或许仍未掌握在手中,但是,借由聚焦特定领域内物质与心灵活动的交会,我们或许能得到部分的答案,并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的终章,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做法,即应该更仔细地探究权力关系,因为它是社会中社会劳动力的调配,以及规定劳动分工中哪些人做哪些事的心灵图式二者的中介。这个建议有几个意涵。其中之一是,让我们注意到社会分工与心灵图式都随着男性与女性、年轻者与年长者、富裕者与贫穷者、定居者与移民、有权势者与无权势者,以及得为精神代言者与无法做到者变异。这一点反过来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引到使得这些社会分布与理解和想象变得协调一致的各种过程。由此,我们或许可更清楚看出知识如何在言语与非言语表达中累积、沟通或受到禁制。而普世的秩序又是如何增进、诉求建构和积累某些形式的权力,并使另外一些噤声、再不被提及。还有,为何某些心灵图式相较另一些在性别、阶级与族群构成中取得主导地位,尽管也有另外的图式试图挑战主导权。这些相互联结的疑问,应该会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问题上,而非随意地关注有限的社会与文化实体。关切历史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的历史学二者都有必要,文化分析与田野的民族志二者亦然。已有部分工作此刻正在进行,还有更多亟待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