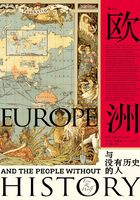
1982年版前言
我在1968年写道,人类学应该发掘历史,尤其是解释当代世界的社会系统如何演变为现今面貌的历史,需要的是对于诸社会的分析眼光,包括我们身处的社会。我相信,我们需要这种分析历史以抵挡现今人文学科中日渐取得优势的形式化的理性,形式化即不再探求人类行动的原因,只寻找大体由制式词语堆砌问题的制式解答。研究方法愈渐精细,成果却是陈腐老调。由琐细趋向无关紧要,我想,我们要从过去寻找现在的成因。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才能理解推动诸社会与文化演变成今天面貌的力量。本书的信念源自于此。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此种分析的历史无法仅通过对单一文化或国家、单一文化区域,甚至某一洲单一时期的研究得知,而必须回到早期人类学的洞见,恢复曾经导引阿弗烈·克鲁伯(Alfred Kroeber)、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等人类学家的灵感,借由他们努力建立的全球文化史。他们明白,我们却似乎遗忘,文化是从和其他群体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而非孤绝地形成。
但早期人类学甚少着墨推动诸文化自1492年以来互动的主要力量,此力量驱使欧洲进行商业扩张与工业资本主义。然而,这些人类学家试图勾勒的文化联系,只有透过它们各自的政治与经济脉络才能被清晰理解。因此,人类学的洞见必须在新的、历史取向的政治经济学的映照下重新被审视。
这样一种再思考,必须超越描述西方历史的惯常方式,考虑到西方与非西方的群体是如何共同参与这个世界性进程的。多数人类学家研究过的群体早就被卷进欧洲扩张造成的改变中,他们也是造就这些改变的力量。我们不能再自满于撰写有关得胜精英的历史,或再添上几笔族群顺服的记录。社会史学家与历史社会学家已经说明,普罗大众是历史进程中积极的行动主体,就像他们同时是受害者与沉默的见证人。因此,我们要揭露“没有历史的人”的历史,即关于“未开化的族群”、农民、工人、移民与被征服的少数族群的鲜活历史。
为达目的,本书致力跨越划分不同人文学科的分界线,消除西方与非西方历史之间的界限。我在这本书中秉持的信念是,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处境,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
本书的构想诞生自20世纪60年代末的思想重估风潮。1973—1974年,在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赞助下,我在英国进行了为期1年的研究。对于基金会给予的支持,我衷心感谢。
我自1974年春天起着手撰写本书,全书定稿于1981年。几位友人以批判的眼光审阅过此书。我心怀感激,他们是罗德里克·艾亚(Roderick Aya)、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艾什勒弗·贾尼(Ashraf Ghani)、雪莉·林登鲍姆(Shirley Lindenbaum)、雷娜·拉普(Rayna Rapp)、罗杰·桑杰克(Roger Sanjek)、简·施奈德(Jane Schneider)与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与文思理(Sidney Mintz)花时间与我通信讨论书中的众多论点。他们提出的部分意见我并未遵从,此责任自然在我。我深深哀悼挚友安杰尔·帕勒姆(Angel Palerm)的离世,他未及见到本书完成,我怀念他深入而极具洞察力的评论。
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士提供资料使用方面的协助,包括安妮·贝利(Anne Bailey)、马里奥·比克(Mario Bick)、查尔斯·毕夏普(Charles Bishop)、沃伦·迪波尔(Warren DeBoer)、艾什勒弗·贾尼、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雪莉·胡内(Shirley Hune)、赫伯特·克莱恩(Herbert Klein)、卡罗尔·克雷默(Carol Kramer)、赫尔曼·里贝尔(Hermann Rebel)、罗杰·桑杰克、杰拉尔德·赛达(Gerald Sider)、胡安·维拉玛林(Juan Villamarín)、伊丽莎白·沃尔(Elizabeth Wahl)与弗雷德里克·怀亚特(Frederick Wyatt)。在图片资料部分,我得到以下人士的帮忙与协助,包括海耶基金会(Heye Foundation)赞助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Museum of American Indian)的馆员安娜·罗斯福(Anna Roosevelt)、詹姆斯·史密斯(James G. E. Smith)与唐纳德·维尔纳(Donald Werner);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芭芭拉·康克林(Barbara Conklin)与戈登·埃克霍尔姆(Gordon Ekholm);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威廉·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以及兰布罗斯·科米塔斯(Lambros Comitas)、琼·芬弗尔(June Finfer)、弗雷德·波珀(Fred Popper)、露西娅·伍德·桑德斯(Lucie Wood Saunders)、伯纳德·夏皮罗(Bernard B. Shapiro)、阿奇博尔德·辛汉(Archibald Singham)。诺尔·迪亚兹(Noël L. Diaz)与卡里尔·戴维斯(Caryl Davis)为本书绘制了绝佳的地图。我要向以上每一位致上最深的谢意。我还要感谢伦敦大学的伦敦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允许我利用图书馆馆藏。在研究过程中,纽约城市大学的赫伯特·莱曼学院(Herbert H. Lehman College),以及研究生院与大学中心的人类学博士课程,在研究、教学与思想交流等方面对我都极具启发。能有此机会,我要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
若没有我的助手和另一半席黛尔·西尔弗曼(Sydel Silverman)提供的意见、编辑技巧与源源不绝的鼓励支持,与最重要的,她给予的人类学批判,以上种种努力无法化作丰硕的成果。“这么多的事物,我已经全部窥觑。凭借你的美善、你的大能,它们的恩泽和力量我方能瞻盱。”(《神曲3·天堂篇》,第三十一章,黄国彬译)怀抱着爱意与尊敬,我将这本书献给她。
埃里克·R.沃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