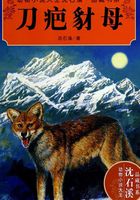
第7章 刀疤豺母(7)
红毛雪兔是一种穴兔,所谓穴兔,自己不挖洞,居住在天然的地缝和洞穴里,习惯在地底下生活。尕玛尔草原特殊的地质结构,那些布满洞窟的珊瑚礁,是红毛雪兔最理想的栖身之地。它们的听觉和嗅觉十分灵敏,一听到猎狗的吠叫,一闻到猎枪的硝烟味,立刻顺着洞穴窟窿从地面钻进地下。猎人和那些高大勇猛的狼狗无法跟着红毛雪兔钻进狭窄的洞穴,身体玲珑娇小的土狗,虽然能勉强挤进窟窿去,但缺乏在黑暗的地底下追捕厮斗的胆魄与勇气,往往衔着兔尾钻进洞窟,追不了几米深,便丧失了勇气,抽身退了出来,蹲在洞口悻悻吠叫。有一条身材细长胆量出众名叫阿龙的牧羊犬,在追逐一只红毛雪兔时,不顾一切地跟着逃犯钻入几十公尺深的地底下,结果在迷宫似的洞穴中迷了路,怎么也回不到地面来了,它的主人耳朵贴在地面的洞穴口,还能隐隐听到自己爱犬如泣如诉的吠叫声,两天后,地底下的狗吠声才逐渐衰竭……
理应是猎狗驰骋的战场,却成了活埋猎狗的坟场。
其他狗目睹阿龙被活埋的惨状,更不敢追进洞穴去了。
狡黠的红毛雪兔,把远古珊瑚礁形成的地下迷宫当作避风港和防空洞,开展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同猎人和猎狗进行巧妙的周旋。
“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到附近的村寨找人来帮忙,多借些猎狗来,看这些该死的红毛雪兔还能猖狂多久!”强巴用拳头擂着桌子说。
当天夜里,强巴就骑了一匹骏马,到附近几个村寨联络。两天后,开来好几个狩猎队,还牵来许多猎狗,再次对红毛雪兔进行围剿。人海战术和狗海战术并用,尕玛尔草原到处都是猎人和猎狗,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
战绩仍谈不上辉煌,每天最多也就是捕猎到百十只红毛雪兔。
猎人太多,又是从各个村寨来的,很难协调指挥,古老的牛角号也难以保持联络畅通,发生混乱在所难免。卡扎寨一位汉族牧民开枪误伤了纳珐寨一位康巴猎手的腿,松甸村一位藏族猎人将躲在草丛里想守株待兔的庆迪寨一位汉族牧民的胳膊打断了。各个村寨的猎狗更是难以调教,公狗打架斗殴,母狗争风吃醋,还拉帮结伙打群架,自相残杀,咬伤了好几条猎狗,闹得乌烟瘴气。
大规模围剿仅维持了一个星期,各路诸侯便不得不草草收兵。
整整一个冬季,狩猎队天天出征,虽然战绩不尽如人意,但累积起来数量也不算少了,总共大约消灭了七八千只红毛雪兔,可红毛雪兔的总体数量并未明显减少。金黄的牧草仍像理发似的一片片被剃掉,落日黄昏时成千上万只红毛雪兔形成的庞大军团依然像红潮似的在草原上涌动,给人一种红色恐怖的感觉。
卡扎寨离尕玛尔草原约有两华里,坐落在日曲卡雪峰脚下,过去从未发现过红毛雪兔的活动踪迹,可冬末这几日,也不知是受食物的压力,还是想扩展生存地盘,红毛雪兔渐渐向卡扎寨靠拢,寨子四周的树林,许多大树的树皮都被兔牙啃得斑斑驳驳的。
“这是怎么回事?”强巴望着打谷场上堆积如小山的被打死的红毛雪兔,迷惑不解地搔着头皮问我,“它们怎么会越杀越多呢?”
我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古诗用到红毛雪兔身上倒是蛮恰当的。”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我都快愁死了。”强巴不满地说。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红毛雪兔之所以会越杀越多,道理很简单,一只红毛雪兔倒下去了,千万只红毛雪兔站起来了。”
“这话怎么讲?”
“你们狩猎队虽然捕杀了不少红毛雪兔,但并未破坏红毛雪兔的繁殖机制,它们的繁殖速度远远超过你们的猎杀速度,当然只能是越杀越多喽。”我认真地说。
十一
冬天过去了,稀薄的阳光渐渐变浓,树枝绽出新绿,怒江的冰层嘎嘎开裂,融化的冰水叮叮咚咚唱着春天的赞歌流向远方。到南方去越冬的大雁和黑天鹅成群结队地飞回尕玛尔草原。
以往这个时节,尕玛尔草原就像一位参加时装表演的妙龄女郎,淅淅沥沥的春雨就像是为表演奏响的乐曲。第一场春雨过后,灰黄的草原爆出星星点点嫩绿的草芽;第二场春雨过后,密密的小草铺满大地,草原像穿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绿纱裙;第三场春雨过后,草原像身穿翡翠绿色紧身衣裤的女妖,妩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第四场春雨过后,浓绿的青草间绽放姹紫嫣红的野花,艳丽得就像贵妇人参加晚宴的盛装……
可今年春天,尕玛尔草原却丑陋得惨不忍睹。草芽刚刚冒出地面,便被贪婪的红毛雪兔洗劫一空。融化的雪水下刚刚泛起一片绿意,便会有数以万计的红毛雪兔蜂拥而上,把那片绿意糟蹋殆尽。
红毛雪兔啃食青草的风格与牦牛和山羊迥然不同,牦牛和山羊只吃冒出地面的草叶,不会去伤害草根,草叶被啃食后,春雨一浇,春阳一照,草根上又会蓬蓬勃勃蹿出新叶来。红毛雪兔吃起草来就像强盗掠夺一般,不仅将冒出地面的草叶啃吃了,还要扒开泥土将草根咬断嚼烂,根系遭到破坏,当然也就不再生长新叶了。
下了四五场春雨,明媚的阳光殷勤地照耀着大地,然而,尕玛尔草原仍显得支离破碎萎靡不振,东边枯黄西边绿,还裸露着大片大片黑色的泥土,野花也开得有气无力,花瓣凋零,色彩暗淡,半死不活的样子。放眼望去,尕玛尔草原就像衣衫褴褛的叫花婆。
卡扎寨的牧民秋天将青稞的秸秆晾晒在名叫“青稞架”的木架子上,作为越冬的饲料,在大雪纷飞牧草匮乏时,切碎了喂养牛群和羊群。饲料储存的数量家家户户都是计算好的,刚够牲畜一个冬季消耗,春雷隆隆时,青稞架上的饲料告罄,牲畜赶往尕玛尔草原,不再需要喂饲料,改食茂盛的春草。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对牧民而言,尤其是这样。冬季喂的是干饲料,口感和营养都不太理想,维持牛羊生命而已。春草肥,牛羊壮,冬天掉膘春天补,牧民所有的希望都在春季。牛羊晒着暖烘烘的阳光,大口大口啃食口感甚佳营养丰富的春草,不几日,冬天熬瘦的身体变得油光水滑,憔悴的容貌变得青春焕发,懒懒散散的生命变得激情澎湃,发情交配,传宗接代,添丁增口,种群兴盛。
可今年春天,对卡扎寨牧民来说,却成了一道鬼门关。
尕玛尔草原稀稀落落的春草,根本无法满足整个卡扎寨牦牛群和山羊群的需要。牧民储存的越冬饲料早已用光了,拿不出东西来喂这些饥肠辘辘的牛羊。应是长膘的季节,可怜的牛羊却因为吃不饱肚皮而迅速消瘦下来,不少牦牛瘦得肩胛支棱,许多山羊瘦得肋骨暴突。饥饿使牛羊丧失了生命的活力,公牛成了太监牛,公羊成了太监羊,母牛和母羊成了计划生育的模范,耽误了好时光。
牧民的生活全靠这些牛羊,望着骨瘦如柴的牛群和羊群,他们眉头紧锁,表情凄苦,整日唉声叹气。
虽然能捕猎到一些红毛雪兔,能得到一些兔肉和兔皮,但比起因草场受到破坏牛羊饲料不足而遭受的损失来说,这些兔肉和兔皮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占了小便宜,却吃了大亏呀。
更让牧民提心吊胆的是,春季也是红毛雪兔繁殖的高峰期,数量迅猛增长。红毛雪兔属于育幼期极短的哺乳兽类,也就是说,幼兔在娘胎里就长齐一身绒毛,刚钻出产道就能睁开眼睛,绒毛被母兔一舔干就能蹒跚奔跑,吃上十来天奶,就能长出门齿来啃食嫩草活下去。进入春季才半个多月,新一茬红毛雪兔就活跃起来,在草原上蹦跳嬉闹,放眼望去,涌动着一片让人头皮发麻的红潮。
尕玛尔草原上的牧草,还不够这些红毛雪兔啃吃和糟蹋的。
终于发生了让牧民目瞪口呆的事。一天夜晚,饥饿的红毛雪兔袭击了村民李某搭建在寨门边一座粮仓,将一千多斤青稞连同那座用芦席做建筑材料盖起来的小粮仓一起吃了个干净。紧接着,好几家坐落在寨子边缘的菜地和果园又被红毛雪兔洗劫一空。有两条看家狗,半夜听到动静,冲进菜地想把正在行窃的红毛雪兔缉拿归案,结果寡不敌众,一条黄狗被愤怒的红毛雪兔活活咬死,另一条黑狗身上的狗毛被红毛雪兔啃了个干净,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变成了一条赤膊狗。
村民们人心惶惶,有的说:“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房子怕也会给红毛雪兔吃掉的呀。”还有人说:“等尕玛尔草原上的牧草被吃得精光后,这红毛雪兔就会变得像豺狼一样可怕,来吃牛羊,说不定还要吃人哪!”
强巴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将藏袍往腰上一系,裸露着一只臂膀,高擎火把,声嘶力竭地叫道:“我就不信没办法治这些红毛雪兔了,用火烧,烧死这些该死的家伙!”
牧民紧急动员,有的捡干牛粪,有的割芦苇,有的砍柴火,到尕玛尔草原实施火攻战术。四面八方点起火堆,遗憾的是春季多雨,地上又没有多少枯草,火焰难以形成燎原之势,只见浓烟滚滚,不见火势蔓延,而红毛雪兔又随时能钻进地下洞窟躲藏,折腾了数日,效果甚微,不得不放弃了愚蠢的火攻战术。
“投毒,毒死这些讨厌的红毛雪兔!”强巴咬牙切齿地说。
于是,派人到城里去购买五花八门的老鼠药,什么磷化锌、灭鼠灵、鼠魂散、鼠必倒……与食物搅拌在一起,投放到尕玛尔草原,为了方便红毛雪兔就近食毒送死,还将毒饵扔进珊瑚礁洞穴去。
投毒战术开始时效果不错,仅两三天时间,尕玛尔草原上涌动的红潮就消退了许多,山旮旯、树角落、水塘边和石头底下,随处可见红毛雪兔横七竖八的尸体。牧民拧紧的眉头舒展开了,凄风苦雨的脸也逐渐晴朗。可谁也没有想到,投毒战果仅仅辉煌了几天,便形势陡转,朝坏的方面发展了。那红毛雪兔是一种善于总结经验的动物,目睹同类中毒身亡的惨状,很快就明白是人类在有意陷害它们,懂得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谢绝牧民们投放的毒饵。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血的教训和生命作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又记得非常牢,大概还有一套快速传播信息的系统和渠道,不管牧民怎么花样翻新投放用高价购买来的新型老鼠药,不管将老鼠药撒在草根还是投放进珊瑚礁的洞穴,不管饿得饥肠辘辘还是饿得眼睛发绿,所有的红毛雪兔步调一致地回避那些伪装成五颜六色闻起来还有一股柠檬或巧克力香味的老鼠药。红毛雪兔不是笨蛋,会前赴后继地被人类毒杀。
投毒战术流产了,更糟糕的是,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恶果。
实施投毒战术前,曾告诫家家户户,千万看牢自己的牛群和羊群,在投毒期间别让牛羊跑到尕玛尔草原上去,以免发生误伤现象。这就像颁布了戒严令,划定了不准擅自闯入的军事禁区。可牛羊太多,卡扎寨的牧民又不习惯圈养牲畜,没有足够的牛厩羊栏来安顿这些自由散漫惯了的牦牛和山羊,免不了有些牛羊趁主人一时疏忽,溜出残缺破陋的厩栏,跑到尕玛尔草原去,吞食了那些老鼠药,糊里糊涂踏上了黄泉不归路。
那些先前被老鼠药毒死的红毛雪兔,有的死在地穴,有的死在树洞,有的死在隐秘的旮旯角落,尸体收拾不干净,春天潮湿温暖,细菌繁殖得快,不几日红毛雪兔的尸体便腐烂变质,方圆百里的尕玛尔草原恶臭熏天,连惯食腐尸的大嘴乌鸦也吓得搬家了。草原上不可避免地流行起了可怕的瘟疫,牦牛和山羊本来就因为食物短缺而瘦弱不堪,抵抗力很差,天天都有好几头牦牛好几只山羊死于非命。
让猎狗帮忙搜寻红毛雪兔尸体,当收尸搬运工,那尸体上有毒,猎狗用嘴叼咬,也发生中毒现象,死了好多条猎狗。
灾难频频,雪上加霜,有几户牧民不堪忍受这种生活,动身迁移他乡。有一户汉族村民,本来家境就不佳,仅有四头牦牛七只山羊,瘟疫一传播,他所有的牛羊死得一头不剩,只能携家带小到城里乞讨求生去了。在卡扎寨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外出逃荒。人们脸上阴霾密布,老人终日唉声叹气,女人终日哭哭啼啼,男人终日借酒浇愁,更有一些迷信思想很重的牧民,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
强巴走投无路了,借用一个略含贬义的词——黔驴技穷。他不得不来找我,满脸羞红,嗫嚅着说:“沈老师,都怪我,不懂科学,没……没想到会……会闹到这个地步……过去我不尊重您的意见,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是动物学家,您一定要想想办法,消灭这些该死的红毛雪兔,救救我们卡扎寨!”
强巴说这番话的时候,眼圈红红的,似有悔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实在是心里太难受了。卡扎寨牧民遭受的灾难,是他引起的,他身上的压力很重,思想负担也很重。
对卡扎寨发生的灾难,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不会因为强巴曾经没听我的劝告并嘲讽过我,便耿耿于怀,在他遭难之际,躲在暗处看他的笑话。再说,我是个动物学家,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来帮助卡扎寨牧民解危济困。
“办法是有的,”我说,“就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只要能让尕玛尔草原重新绿起来,要我做什么都行。”
“把金背豺重新请回尕玛尔草原来。”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这……”强巴像患牙痛似的苦起脸来。
我晓得他语塞的原因。豺在当地牧民心目中,等同于恶魔,大半年前好不容易才将它们驱赶走,现在要把它们请回来,这思想弯子一下子很难转得过来。
“沈老师,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譬如说除了豺之外,寻找另一类红毛雪兔的天敌?”强巴眼巴巴地望着我说。
我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