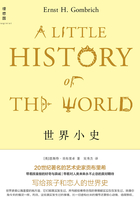

现在,我们要去世界的另一端。先是印度,然后到中国。我们想看一下,大约在波斯战争期间,这两个庞大的国家情况如何。就像两河流域一样,印度文化也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就在吾珥城里的苏美尔人特别强大的时候,也就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印度河(这是巴基斯坦境内的一条大河)河谷有一座非常大的城市,里面有水管和水渠,有庙宇、房屋和商店。这座城市叫莫亨佐-达罗(Mohendjo-Daro),在20世纪20年代年被发现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在几年之前 ,人们对那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就像在掩盖了吾珥城的废墟里发现的东西差不多。到底是什么人曾经在那里住过,我们还不太清楚。人们只知道,今天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居民,是后来才迁入的。他们说的语言,与波斯人和希腊人的语言、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语言有亲近的关系。“父亲”这个词在古代印度语是Pitar,在希腊语是Patr,在拉丁语是Pater。
,人们对那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就像在掩盖了吾珥城的废墟里发现的东西差不多。到底是什么人曾经在那里住过,我们还不太清楚。人们只知道,今天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居民,是后来才迁入的。他们说的语言,与波斯人和希腊人的语言、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语言有亲近的关系。“父亲”这个词在古代印度语是Pitar,在希腊语是Patr,在拉丁语是Pater。
由于印度人和日耳曼人是两个都说这类语言、空间上却相距最远的两个族群,所以这种语言被称为印度-日耳曼语言。不过他们是只在语言上有相似之处,还是在血缘上也有关联,我们并没有确切的了解。不管怎样,讲印度-日耳曼语言的印度人入侵了这个地方,就如同多利安人入侵希腊一样。他们肯定也将原来的当地居民征服了。后来,入侵者的后代征服了这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与当地居民严格地分隔开来。这种分隔固定化为一种叫种姓制度的社会秩序,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种制度里,每一个职业都被严格区分开来。在其中,是武士的那部分人,必须一直是武士,连他们的儿子也只能成为武士。这就是武士种姓。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种姓,也和武士种姓一样是封闭的,比如手工业者和农民。谁要是属于这样一个种姓,就不可以从里面出来。一个农民永远不可以成为一个手艺人,反过来也不行。他们的儿子也一样。他们不可以同其他种姓的姑娘结婚,甚至不可以与其他种姓的人坐在一起吃饭和坐车。在印度某些地方,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最高级的种姓是祭司,叫作婆罗门,地位在武士之上,他们主持献祭、对庙宇负责,也掌管知识(与埃及的情况非常相似)。他们必须背诵神圣的祈祷词和圣歌,要几千年保持不变,直到它们被记录下来。印度一共有四个不同的种姓,而每个种姓里面又有若干亚种姓,彼此也有所区别。

蜂巢?不对,是印度的庙宇,其外形特别大,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样子。
不过,还有很小一部分的人口,根本上不能属于任何种姓。他们是贱民。人们只允许他们干最脏、最不愉快的工作。谁也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哪怕那些属于低级种姓的成员也不行。他们会说,只要一碰贱民,就会被弄脏。贱民甚至得留心不能让自己的影子落到别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的影子同样能弄脏别人。人竟然能这么残酷。
在其他方面,印度人倒不残忍。正好相反。他们的祭司是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人,经常隐退到孤寂的树林里,好好地冥想最困难的问题。他们会思考很多野性的神,还有最高级的主神梵天(Brahma)。他们感觉到,大自然中的生命,无论神还是人,动物还是植物,都是靠这位最高神的呼吸气息才得以活着;这位最高神无所不在:在太阳的光线中,在土地上长出的嫩芽中,在生长和死亡中。神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就如同将一颗盐粒放入水中,里面的每一滴水便都有了咸味一样。我们在大自然中看到的差异,一切的循环和变更,都是表面上的。同一个灵魂可能变成了一个人,在死后又可能会成为一只老虎或者一条眼镜蛇,这样的循环会一直进行,直到灵魂得到净化,与神的本性合而为一。这是因为梵天的气息是万物之本。印度的祭司们为了让弟子们更正确地理解教义,想出了一个很美的公式(你也可以在脑子里思考一下),这个公式是:“这是你。”这意味着你所见到的一切——动物、植物以及和你一样的人——都是同一的,包括你自己,都是神的一缕气息。
为了能够感觉到这种大一体,印度的祭司们想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办法。他们坐在茂密的原始森林的某个地方来思考问题: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就这么僵直而安静地坐在地上,两腿交叉,目光低垂。他们尽量少呼吸,尽量少进食。对,有些人还以特殊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忏悔修炼,好在自己的身上感受到神的气息。
三千年以前,印度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圣人、忏悔者和遁世修行者,今天也还有。但是,有一个人与其他人非常不同。这就是王子乔达摩(Gautama),他生活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00年。
人们讲述说,乔达摩——人们后来将其称为“觉者”、“佛”——是在东方最豪华、最富有的家庭里长大的。据说他有三个宫殿,一个夏天住,一个冬天住,一个供他在雨季的几个月住,那里总有动听的音乐,而他也从来不离开宫殿,因为他父亲不想让他走下那些富丽堂皇的高台,想让他远离一切悲伤之事。因此,受苦人不可以出现在他的身边。可是,有一次乔达摩从宫殿里出来时,看到一个驼背弯腰的老人。他问陪同他的驾车人是怎么回事。驾车人只好解释给他听。他若有所思地回到了自己的宫殿里。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患病的人。疾病这事,从来没有人和他讲过。回到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身边后,他陷入了沉思。第三次,他看到了一个死人。这次,他不要再回到宫殿里了。最后,他看到一个遁世修行者时,决定自己也要走进荒野,去思考人世间在衰老、生病、死亡中呈现出来的苦。
在某一次说法时,他曾经这样说:“我正当青春年少,享受着幸福的青年时代,光彩照人,一头黑发,在少壮之年违背了父母的愿望,不顾他们的哀哭悲叹,剃掉了头发和胡子,穿上破旧的衣服,离开家里走进茫茫荒野之中。”
他当了六年的修道者和忏悔者,比任何人都思考得更深入,也比以前的任何人都更严酷地折磨自己。当他坐着的时候,他几乎不呼吸了,他忍受着可怕的痛苦。他吃得非常少,因为衰弱几乎晕倒。但是,在这些年里,他还是无法找到内心的安宁。因为他所思考的,不但包括“世界是什么”,是否在本质上一切都同一,他还要思考世上的一切不幸,那些无处不在的疼痛和悲苦,以及衰老、生病和死亡。在这方面,无论多少忏悔都帮不上忙。
慢慢地,他又开始进食,开始积攒力气,开始呼吸了,像所有的人一样。因此,那些迄今为止敬慕他的修道者们,现在蔑视他。但是他不为所动。有一天夜里,当他沐浴着宜人的森林光线,在菩提树下打坐时,忽然有了新的认识,顿时明白了这些年自己在找的是什么。就好像他突然之间看到了一束内在的光。因此,他现在是一位被照亮者,是觉者,是佛陀。他把自己的内心发现告诉了所有人。不久以后,他就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这些人相信他发现了一切人类痛苦的解脱之途。这些敬仰佛陀的人,成立了一个群体,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僧尼教团。在许多亚洲国家,今天还有这样的教团。他们的追随者身着黄色的衣服,生活方式简朴。
现在你会想知道,乔达摩在无花果树下,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菩提树下,究竟悟到了哪些解脱一切困惑的方法。如果我要给你做些解释的话,你也必须去思考一下。毕竟,乔达摩用了整整六年只思考这个问题呢。他得到的最大启发、人类痛苦的解决之道就是:如果我们想从痛苦中解脱,就必须从自己开始。所有的苦来源于欲望。大体上讲就是,如果你因为得不到想要的一本漂亮的书或者玩具而感到难过的话,你有两件事可做:一是想办法得到它,二是不再想得到它。如果你能做到其中的一个,你就不会难过了。佛陀教导说:如果我们不再期望拥有漂亮、舒服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再一直渴望幸福、舒适、他人的认可、柔情的呵护,那么在得不到时,我们就不会感到那么难过了。人们只需减少欲望,就能减少痛苦。

在无花果树下打坐时,乔达摩得悟。在很多雕像中,这位曾经是王子的佛陀都是这一姿势。
“但是,人没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啊。”你也许会这么说。但佛陀有另外的观点。他教导说,经过长年的自我修行,人们可以做到想有多少欲望就有多少欲望。也就是说,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人,就像赶大象的人和大象的关系那样。在人世间能做到的最高级就是:什么都不想要。这就是他讲的“内心的风平浪静”,一个人最大、最平静的福分,就是在人世上一无所求。他对众生一视同仁,不对任何人有所要求。谁能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人——佛陀接着教导说——谁就不会在死后重新转世。因为印度人相信,灵魂之所以转生,是因为它还牵挂在生命上。谁不再对生命有所牵挂,死后就不会挤进“生命轮回”当中,而会进入“空”,进入没有愿望、没有痛苦的“空”,佛教徒称之为“涅槃”。
这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得到的启发——这种学说教导人们不要屈从于欲望,而是要将自己从欲望中解放出来,就像口渴时不去理会这种感觉,它就自然会消除。这条路并不简单,你可以想得到。佛陀称之为“中道”,因为它在无用的自我折磨和无思虑的美好生活之间通向了真正的解脱。这里的关键是:正确的信仰、正确的决定、正确的言行、正确的生活、正确的追求、正确的意识、正确的自我沉浸。
这是乔达摩说法布道中最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人追随、膜拜他,像对待神一样。今天世界上的佛教徒,差不多和基督教徒一样多,在“后印度” 、锡兰(今天叫斯里兰卡)、日本、中国(特别是西藏地区)都有很多佛教徒,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遵从佛陀的教导去生活,达到内心的“风平浪静”。
、锡兰(今天叫斯里兰卡)、日本、中国(特别是西藏地区)都有很多佛教徒,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遵从佛陀的教导去生活,达到内心的“风平浪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