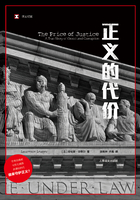
第3章 序(1)
若真想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当煤矿工人。
矿工们生命中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的宿命思想。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煤矿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是在1971年,当时我读了哈里·考迪尔(Harry Caudill)的《夜幕降临坎伯兰》一书。在他的笔下,对肯塔基州东部阿巴拉契亚高原的民众遭受剥削、贫困潦倒生活的描写堪称经典。他们的人生中,贫穷和苦难随处可见,然而细细品味,却也不乏某种坚毅和真实的特质蕴含其中。我知道,这些特质在我自己的人生中是缺失的,于是,我放弃了自己位于曼哈顿西区的寓所,驱车南下,前往西弗吉尼亚州,希望创作出以那个地区和人民为主题的作品。
当时,煤炭行业正值多事之秋,乱象纷呈。1969年,改革派候选人约瑟夫·“乔克”·雅布隆斯基(Joseph “Jock”Yablonski)竞选矿工联合会主席失利,在自家床上被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和他们二十五岁的女儿夏洛特。这次谋杀给煤炭行业留下了恐惧和猜疑的阴影。直到四年后,矿工联合会主席安东尼·“托尼”·博伊尔(Anthony“Tony”Boyle)因雇凶谋杀雅布隆斯基被定罪,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来到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时候,主张改革的“民主矿工”组织正在开展运动,意在接管贪污腐败的工会。同时,煤炭公司也在紧张地提防着所谓的外来煽动者挑动矿工闹事。在那里,我唯一的社会关系是一位朋友的朋友,他在贝克利经营一家家具店。贝克利人口一万六千人,是西弗吉尼亚州中南部最大的城镇。这位朋友告诉我,若真想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当煤矿工人。
矿工联合会和威斯特摩兰煤炭公司同意我到矿井工作,前提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是记者,而且我的写作内容只能涉及矿工工作本身,不能涉及工会政治。第二天,我来到贝克利城外被称为埃克尔斯六号的矿井上班,我的班次是大夜班,时间从午夜到次日早晨八点。
当上矿工的第一天夜里,我按时赶到更衣室。矿工们上班前在那里换上工作服,下班后在那里冲洗掉身上的煤尘。我到那儿的时候,正赶上第二班矿工离开矿井。身穿崭新的工作裤和绿色长袖衬衫,头戴崭新的黑色头盔,我看上去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新手。当我和同班次的其他矿工乘电梯下降到一百五十英尺深的竖井中时,心里非常紧张。1914年,从我工作的矿层下行三百英尺处,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一百八十六名矿工在那次事故中丧生,那是西弗吉尼亚州采矿史上第二大矿难。十年后,又发生了一次爆炸,这次十九人遇难。
那之后这个矿井没有再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故。不过,矿工们在每次下井之前,都会把写有自己名字的锡制标签挂到更衣室的布告板上;当他上完班回到地面上,再把自己的标签摘下来。如果矿工被困井下或是死于事故中,这块八角形的金属片就能够告诉人们,井下被困和遇难的都有谁了。
矿工在井下工作一辈子,平均能赶上三到四次重大事故,事故有时会严重到矿工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当矿工退休时,他们往往会罹患黑肺病而咳喘不已。这种病就是由于长期大量吸入煤尘所致,病人往往身体虚弱,痛苦不堪。即使没有患上黑肺病,矿工也会患上其他疾病而缩减寿命。
尽管面临种种风险,对于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普通人来说,煤矿的工作仍然可以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此外,当时男人们赚大钱的途径还有一种,那就是离开他们热爱的山地,到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上找份工作。
我告诉大家,我之前是纽约北部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来到此地是因为我需要工作养家糊口。而大家对我的解释深信不疑,原因就在于此。一个男人丢下他看重的一切,去陌生的地方谋生,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合乎情理,不足为奇。可以这样说,几乎从我在煤矿的第一个夜班开始,矿工们就接纳了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人们不喜欢你,那么你很可能就呆不长。
如今,矿工初次下井之前必须接受为期一周的安全教育。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可没有为矿工上岗提供这样的准备工作。新来的矿工要依赖同班组的前辈传授自我保护的办法。比如,如何避开头顶上悬着的明线以免触电;再比如,如何系紧鞋带以免鞋带卷进传送带把人也绊倒在传送带上,轻则皮肉受伤,重则丢掉性命。
起初的几个夜班,我的任务是负责为白班补充所需物品和给养。后来,我成为一个八人采矿小组的成员。在我们小组中,一名矿工负责操作连续采掘机,旋转的锯齿状刀片不断掏挖出煤块;两名梭式矿车司机每次铲起五吨新开采的煤,把这些煤运送到传送带上。梭式矿车司机干活很熟练,但难免会将一些煤洒落在传送带旁边的地面上。我负责站在传送带旁边,把洒落的煤再铲到传送带上。如果我不能及时把煤铲起来,传送带会暂停作业,梭式矿车也无法正常传送煤炭。我必须时刻留心梭式矿车的到来。这些梭式矿车就像一只体型巨大的蜈蚣,照明前灯穿越重重黑暗,从坑道尽头闷声闷气地开了过来。最初的一个夜班中,我的手指头就被磕破了两处。
午餐时间或者设备停止作业时,我们都有大量的时间来交谈。很快我就了解到,大部分矿工,除非曾经去军队服役,否则终其一生离开贝克利的最远距离也不会超过五十英里。他们谈论的话题只有煤矿和山脉,此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些人与世隔绝的程度与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先相比别无二致,当年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山谷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在矿井下工作了三十年,他们甚至对煤炭行业实现机械化之前的采煤岁月还记忆犹新,那时他们使用的采煤工具是镐头和铁铲。
上完夜班,我们向外走去,从一辆又一辆矿车边上挤过去,车上满载着我们刚刚采掘的煤炭。一个夜班如果顺利的话,我们能够采掘出八十车或者更多的煤。许多人认为煤矿工人很不幸,可是我共事过的矿工却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骄傲和自豪。理由很充分,他们觉得自己干的是可以计量出价值的工作。每天早晨,他们都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完成的工作量。矿工们不会讨论那些煤车象征着什么,不过,如果没有煤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燃煤发电厂会污染空气,所以正在慢慢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但是那时,即便是工业时代末期,假如没有煤的话,美国的照明将会黯淡无光,制造钢材的焦炭同样无从谈起,城镇的楼房自然也无法建造。
我在煤矿也就工作了几个月。离开那里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描述了矿工的生活,1971年12月发表在《哈珀斯》杂志上。文章讲述的故事在西弗吉尼亚引起了轰动,好几家报纸以专题文章的方式刊登,其中包括贝克利的《注册先驱报》。
一年之后,我回到贝克利,为《纽约时报》撰文记述煤矿工会内部的冲突。一天晚上,我参加工会集会,遇到了两位以前曾经共事过的矿工。“伙计,你去哪儿了?”其中一位工友问道。“你只说离开一天,可是你离开我们再不回来了。”他们对我发表的文章一无所知。我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他们。来到他们身边时,我编了谎话;离开他们时,我还是没有告诉他们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要来到他们身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