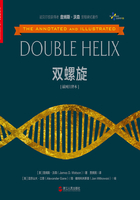
![]()
06
费尽周折的转学
有一天午饭后,我来到马克斯・佩鲁茨的办公室,他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当时约翰・肯德鲁还在美国,但是我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外。肯德鲁事先已经寄回了一封短信,说明年将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来与他一起工作。我对佩鲁茨解释说,我是来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的,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佩鲁茨向我保证,学习这门技术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而且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学过化学,这使我放下心来。我需要做的无非是读一本X射线结晶学教科书,从中学到足够的理论去做X射线照相工作。佩鲁茨还以自己的工作为例向我说明,在鲍林的α-螺旋模型问世之后,他产生了一个验证该模型的简单想法,他花了一天时间就拍到了关键性照片,证实了鲍林的预见。当时的我其实完全听不懂佩鲁茨的话,甚至连结晶学最基本的布拉格定律也一无所知。
随后,我和佩鲁茨出去散步,借机讨论我在来年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当他知道我是从火车站直奔实验室,还没有参观过剑桥大学的任何一个学院时,他带我穿过国王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巨大的中庭(Great Court)。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美丽的建筑。如果说之前我也许还犹豫过要不要放弃作为一名生物学家的生活,见到此景,我的这种想法已经不复存在了。

国王学院礼拜堂(从后院看)

三一学院巨大的中庭

克莱尔学院
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学校里那些作为学生宿舍的阴暗潮湿的房屋时,也只是稍微有点沮丧。我读过狄更斯的小说,也不愿遭受连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不过当我后来在基督草坪(Jesus Green)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个房间时,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宿舍的位置非常好,到实验室只需步行不到10分钟的时间。
第二天一早,我又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因为佩鲁茨让我见见布拉格爵士。佩鲁茨给楼上布拉格爵士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拉格爵士下来后让我用几句话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接着,他和佩鲁茨避开我交谈了一会儿。几分钟之后,他们回到了实验室,布拉格爵士正式通知我,说他已经同意我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了。这次见面是百分之百英国式的。在这次会面中,我觉得布拉格爵士早就成了一个偶像,现在的他应该每天都安稳地坐在伦敦某个俱乐部里(比如雅典娜神庙俱乐部),消磨掉自己的大部分时间。

伦敦雅典娜神庙俱乐部的咖啡室,摄于20世纪50年代
那时我根本没想到,日后我还会不时与这个“老古董”接触。布拉格爵士似乎是过去时代的一个奇迹,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拉格爵士就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一直一来都享有崇高的声誉。我猜想他必定已经处于实际退休的状态,应该不会再来关注基因了。我对布拉格爵士接受我在他这里工作表示了感谢,并对佩鲁茨说,我要先回哥本哈根一趟,在三个星期后赶回来。回到哥本哈根后,我收拾好了仅有的那点衣物,并告诉了卡尔卡这个好消息:我终于能成为一名X射线结晶学家了。
卡尔卡非常支持我,他立即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说他强烈赞同我改变学习计划。同时,我也给华盛顿方面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解释我那时在哥本哈根做的病毒繁殖生化实验其实意义不大。我打算放弃学习传统的生物化学,因为我深信它无法揭示基因的作用机理,而X射线结晶学才是遗传学研究的关键。因此,我请求改变我的学习计划:我要到剑桥大学去,在佩鲁茨的实验室工作并学习如何从事X射线结晶学方面的研究。
按理说,我应该留在哥本哈根等华盛顿方面的批准,但我认为这没有任何意义。留在哥本哈根只能浪费时间,这种荒唐的事情我不能做。一个星期以前,马勒已经动身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去了,他将在那里停留整整一年,而我对卡尔卡式的生物化学也从来没有感兴趣过。虽然依照正式程序,我不能提前离开哥本哈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的要求也无法拒绝,因为大家都知道卡尔卡那时正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华盛顿方面必定一直在担心我究竟愿意留在哥本哈根多长时间。而我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卡尔卡经常不在他的实验室,不但有失风度,而且也不必要。我根本没有考虑过华盛顿方面不同意我到剑桥大学去的可能性。然而,当我回到剑桥大学10天后,却收到了卡尔卡转过来的一封令我非常沮丧的信(这封信被寄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的住处)。默克奖学金委员会不同意我转到一个X射线结晶学实验室去,理由是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他们认为我不能胜任结晶学工作,因此要我重新考虑学习计划。不过,奖学金委员会却愿意资助我转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卡斯皮森细胞生理学实验室去。

卡尔卡写给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拉普博士的信件中的一个片段,该信写于1951年10月5日
引起麻烦的根源很明显。奖学金委员会的负责人已经不再是汉斯・克拉克(Hans Clarke),而他是卡尔卡在生物化学界的好朋友。当时,克拉克正准备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我的信因此落到了新任主席的手中,而这位新主席更加热衷于指导年轻人。我在否认生物化学能带给我的好处时,话说得有些过头,对此这位新主席相当不快。于是我写信向卢里亚求救,他和新主席算得上泛泛之交。我希望通过卢里亚把我的决定以更恰当的方式解释给新主席听,这样也许能改变当前的决定。
起先,种种迹象表明,卢里亚的介入可能会促进事情朝合理的方向演变。我收到了卢里亚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我们愿意做出承认错误的姿态,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这封信令我精神为之一振。我打算写信给华顿盛方面,向他们解释我来剑桥大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研究植物病毒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罗伊・马卡姆也在这里。随后,我走进马卡姆的办公室对他说,我这个挂名学生将会成为一名模范学生,不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因为我的实验仪器不会塞进他的实验室。马卡姆对我的这个计谋很不以为然。他把我这个计谋看成了美国佬不懂得如何正确行事的一个典型例子。不过幸运的是,马卡姆还是答应帮我演完这出无聊的戏。
在确信马卡姆不会走漏风声后,我以非常谦卑的语气给华盛顿方面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列举了与佩鲁茨和马卡姆一起工作能带给我的所有好处。除此之外,在这封信的末尾,我开诚布公地申明,我已经到了剑桥大学,并且打算一直留在这里直到华盛顿方面做出决定为止。但是,华盛顿奖学金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迟迟没有回复。直到有一封回信寄到了卡尔卡的实验室,这事才算有了点眉目。信中说奖学金委员会正在考虑我的申请,如果做出了决定,他们马上就会通知我,奖学金支票则继续在每个月的月初寄到哥本哈根。在这种情况下,把支票兑成现金似乎不是一种谨慎的做法。
不过幸运的是,尽管他们可能不愿意资助我来年研究DNA,但是这种可能性最多只能令我烦恼一阵,从根本上看并不致命。我在哥本哈根时的奖学金津贴是3000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富裕的丹麦大学生生活费用的三倍。即使在支付了我妹妹新买的两套巴黎时装以后,还可以剩下1000美元。

罗伊·马卡姆在冷泉港参加定量生物学国际研讨会,摄于1953年

卢里亚写给沃森的信,写于1951年10月20日
这笔钱足够我在剑桥大学一年的开销了。我的女房东也帮了我一个忙。我住了不到一个月,她就把我赶了出来。我的主要“罪状”是在晚上9点以后回家时没有脱掉鞋子,那是她丈夫的睡觉时间;我偶尔会忘掉在这个时间不能放水冲洗厕所的禁令;当然,更加“恶劣”的是,我在晚上10点以后还要外出。在她看来。这个时间剑桥大学所有机构都关门了,我出去的动机很值得怀疑。这时候,肯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肯德鲁(Elizabeth Kendrew)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们把位于网球场路的一个小房间让给我住,几乎不收取任何租金。 虽然这个房间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它仅有的取暖设备也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电热炉,但我很乐意住在这里。尽管在这里可能会染上肺结核,但与朋友住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比找其他地方住要好得多。就这样,我决定开开心心地住在网球场路的这个房子里,直到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为止。
虽然这个房间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它仅有的取暖设备也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电热炉,但我很乐意住在这里。尽管在这里可能会染上肺结核,但与朋友住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比找其他地方住要好得多。就这样,我决定开开心心地住在网球场路的这个房子里,直到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