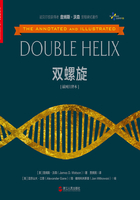
![]()
03
拜师卡尔卡
威尔金斯是第一个激发我利用X射线对DNA展开研究的人。这源于一个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以活细胞大分子结构为主题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那是1951年的春天,当时我还根本没有听说过克里克。我对DNA的兴趣则要早得多。事实上,自从我来到欧洲,以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身份学习生物化学以来,就多次参与了DNA的研究工作。我对DNA的兴趣源于大学时期萌发的一个愿望,我想搞清楚基因到底是什么。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希望不必学习任何化学知识就能解决基因问题。
那是1951年的春天,当时我还根本没有听说过克里克。我对DNA的兴趣则要早得多。事实上,自从我来到欧洲,以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身份学习生物化学以来,就多次参与了DNA的研究工作。我对DNA的兴趣源于大学时期萌发的一个愿望,我想搞清楚基因到底是什么。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希望不必学习任何化学知识就能解决基因问题。 当然,这种想法部分是因为我的懒惰。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鸟类,并且想方设法免修任何化学或物理学课程——即使它们只是中等难度。总体上说,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是鼓励我学习有机化学的,但在我用煤气灯直接去加热苯之后,化学就与我彻底绝缘了。辞退一个无知的博士,无疑要比面临另一次爆炸的危险更加安全一些。
当然,这种想法部分是因为我的懒惰。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鸟类,并且想方设法免修任何化学或物理学课程——即使它们只是中等难度。总体上说,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是鼓励我学习有机化学的,但在我用煤气灯直接去加热苯之后,化学就与我彻底绝缘了。辞退一个无知的博士,无疑要比面临另一次爆炸的危险更加安全一些。

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时的沃森,摄于20世纪40年代末

沃森(左起第三)与他的观鸟伙伴在一起,摄于1946年
直到我到哥本哈根,在生物化学家赫尔曼・卡尔卡的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前,我再也没有学习过化学。最初看来,出国留学可以圆满地解决我对化学几乎一无所知的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是在意大利接受教育的微生物学家萨尔瓦多・卢里亚,他对我不愿意学习化学的态度很纵容。 确实,卢里亚明确表示自己厌恶大部分化学家,尤其是生活在纽约这样的都市丛林中的那些争强好胜的家伙。但是,与这类化学家不同,卡尔卡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他拥有文明的欧洲大陆人的一切优点,卢里亚希望我能够从卡尔卡那里学习掌握从事化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各种工具,同时也不必提防那些唯利是图的化学家。
确实,卢里亚明确表示自己厌恶大部分化学家,尤其是生活在纽约这样的都市丛林中的那些争强好胜的家伙。但是,与这类化学家不同,卡尔卡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他拥有文明的欧洲大陆人的一切优点,卢里亚希望我能够从卡尔卡那里学习掌握从事化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各种工具,同时也不必提防那些唯利是图的化学家。

沃森的博士论文的封面,当时,沃森认为这一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很沉闷
当时,卢里亚的大部分实验都在研究噬菌体的繁殖。很多年以来,在一些很有灵感的遗传学家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猜测:病毒是裸基因的一种形式。倘若真的如此,那么对病毒的研究就将变成解释什么是基因以及基因如何进行复制等方面的问题。由于最简单的病毒就是噬菌体,所以在1940年至1950年之间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他们被称为噬菌体研究小组),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噬菌体,最终搞清楚基因是怎样控制细胞遗传的。
领导这个小组的正是卢里亚和他的朋友、出生在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 德尔布吕克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希望只用遗传学方法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卢里亚则在考虑是否只有在把病毒(基因)的化学结构完全搞清楚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卢里亚非常强调这一点——当我们还不知道某个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就不可能细致地描述这个事物的行为。卢里亚知道,他不可能重新去学习化学了,因此他觉得最明智的办法是把我——他的第一个治学严谨的学生,送到一个化学家那里去。
德尔布吕克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希望只用遗传学方法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卢里亚则在考虑是否只有在把病毒(基因)的化学结构完全搞清楚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卢里亚非常强调这一点——当我们还不知道某个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就不可能细致地描述这个事物的行为。卢里亚知道,他不可能重新去学习化学了,因此他觉得最明智的办法是把我——他的第一个治学严谨的学生,送到一个化学家那里去。

马克斯·德尔布吕克(站立者)与萨尔瓦多·卢里亚在冷泉港实验室观察噬菌体,摄于1941年
而关于究竟是把我送到蛋白质化学家那里去,还是核酸化学家那里去,卢里亚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虽然DNA只占细菌病毒质量的一半(另一半是蛋白质),但埃弗里的实验说明似乎只有DNA才是基本的遗传物质。因此,搞清楚DNA的化学结构可能是了解基因繁殖的关键步骤。然而与蛋白质相比,当时关于DNA化学性质的可靠知识还非常少,只有极少数的几位化学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除了知道核酸是一种由较小的构件——核苷酸——组成的大分子之外,遗传学家们掌握的有关DNA的其他化学知识微乎其微。而且,在DNA领域探索的化学家多为有机化学家,他们对遗传学没有兴趣。但卡尔卡显然是一个例外。1945年夏天,他曾在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听过德尔布吕克的噬菌体课程。 因此,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两人都认为,哥本哈根实验室是一个适合我学习化学的地方,在那里,通过化学和遗传学的技术融合,很可能最终会结出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学硕果。
因此,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两人都认为,哥本哈根实验室是一个适合我学习化学的地方,在那里,通过化学和遗传学的技术融合,很可能最终会结出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学硕果。

赫尔曼·卡尔卡在冷泉港听噬菌体课程,照片上的注释是曼妮·德尔布吕克(Manny Delbrük)加的,摄于1945年
然而,他们的计划完全落空了。卡尔卡完全无法激发出我对化学的兴趣。我发现,即使置身于他的实验室里,我对核酸的化学性质依然无动于衷,就像我身处美国时一样。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看不出卡尔卡当时的研究课题(核苷酸代谢)与遗传学的直接联系,其他原因则包括卡尔卡虽然很有教养,但他的英文实在是很难理解。
无论如何,我还是听得懂卡尔卡的好朋友奥莱・马勒(Ole Maaløe)的英语。马勒刚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回来。在美国时,他对我在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研究过的噬菌体很感兴趣。他回来以后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研究课题,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对噬菌体的研究中去了。当时,他是研究噬菌体的唯一一个丹麦人。对于我和冈瑟・斯腾特到哥本哈根与卡尔卡一起从事研究这件事,马勒觉得非常高兴。斯腾特也是研究噬菌体的,而且也是从德尔布吕克实验室来的。不久之后,斯腾特和我就都注意到了,我们两人都定期到马勒的实验室去。马勒所在的实验室离卡尔卡的实验室只有几公里远。有好几个星期,我们两人都积极地与马勒一起做实验。

冷泉港实验室

1951年3月,微生物遗传学会议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举行。上图是会议期间部分与会者的合影。在此次会议上,像20世纪物理学巨匠尼尔斯·玻尔这样的学界前辈与像沃森这样初出茅庐的后起之秀都发了言。第一排:奥莱·马勒、R.拉塔捷特(R.Latarjet)、E.沃尔曼(E.Wollman);第二排:尼尔斯·玻尔、N.维斯康蒂(N.Visconti)、G.埃伦斯瓦尔德(G.Ehrensvaard)、沃尔夫·韦德尔(Wolf Weidel)、H.海登(H.Hyden)、V.博尼法斯(V.Bonifas)、冈瑟·斯腾特、赫尔曼·卡尔卡、芭芭拉·赖特(Barbara Wright),詹姆斯·沃森和M.韦斯特加德(M.Westergaard)
一开始,我偶尔会觉得与马勒一起做常规的噬菌体研究有点不大自在,因为我的奖学金资助条款明确规定我是来跟卡尔卡学习生物化学的。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我正在做的事情已经违反了这些条款。而且,我来哥本哈根刚不到三个月,有关方面就要求我提出下一年的计划。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并没有什么计划。唯一妥善的解决办法是申请奖学金再跟卡尔卡学习一年。如果直接说我不愿学习生物化学,那肯定行不通。另外,我也看不出有关方面有什么理由在同意我延期后又不允许我改变研究方向。于是,我写信给华盛顿方面,说我希望留在哥本哈根这个非常能催人奋进的环境中。最终,我如愿以偿,有关方面批准了我的奖学金延期申请。看来,有关方面认为让卡尔卡去培养一个生物化学家是比较合适的(在奖学金评委当中,有好几个人都很了解卡尔卡)。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卡尔卡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也许他会介意我很少出现在他的实验室。事实上,从表面上看来,卡尔卡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的,也有可能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经常不在实验室。不过幸运的是,这方面的担忧在变得沉重起来之前就烟消云散了。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事件的发生,使我在道德层面觉得问心无愧。10月初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实验室准备找卡尔卡谈话,因为语言问题,我原以为这必定又是一次迷人而又难以理解的交谈。但是事实不然,卡尔卡的话很容易理解。他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他的婚姻触礁了,正准备离婚。很快,这件事就不再是一个秘密了,实验室中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了。几天之后,情况越发清楚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卡尔卡的心思都没有放在科学研究上,这段时间也许与我待在哥本哈根的时间一样长。因此很显然,他不必教我核酸生物化学正是上帝安排的一件大好事!于是,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每天骑自行车到马勒的实验室去了。相对于勉强卡尔卡与我讨论生物化学相比,对奖学金评委隐瞒我的实际工作地点无疑更好一些。
此外,我对我当时从事的细菌病毒实验有时也是相当满意的。在短短三个月内,马勒和我就完成了一系列实验,揭示出了一个细菌病毒颗粒在细菌体内繁殖为几百个新的病毒颗粒的过程。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数据,可以发表一篇相当不错的论文。按照常规标准衡量,即使我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什么研究也不做,我也不会被人认为毫无成果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所有的工作都没有说明基因是什么,也没能说明它们是怎样繁殖的。除非我能够成为一个化学家,否则我根本无法知道怎样才能完成这方面的研究。

马勒和沃森联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
当卡尔卡建议我和他在春天一起到那不勒斯动物研究所开会时,我立即欣然接受了。他想要在那里度过整个4月和5月。 到那不勒斯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哥本哈根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城市,待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显然没有道理。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灿烂的阳光可能有助于我学习与海洋动物胚胎发育有关的生物化学知识。我也能静下心来在那里阅读一些遗传学著作。如果对遗传学厌倦了,或许我还可以拿起一本生物化学教科书随便翻两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写信给美国有关方面,请求批准我随同卡尔卡一起去那不勒斯的计划。华盛顿方面很快就批准了,回信的措辞令人愉快,信中还祝愿我一路顺风。更棒的是,信中还附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我的差旅费。出发前往阳光明媚的那不勒斯时,这张支票使我对自己的不诚实心生歉疚。
到那不勒斯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哥本哈根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城市,待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显然没有道理。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灿烂的阳光可能有助于我学习与海洋动物胚胎发育有关的生物化学知识。我也能静下心来在那里阅读一些遗传学著作。如果对遗传学厌倦了,或许我还可以拿起一本生物化学教科书随便翻两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写信给美国有关方面,请求批准我随同卡尔卡一起去那不勒斯的计划。华盛顿方面很快就批准了,回信的措辞令人愉快,信中还祝愿我一路顺风。更棒的是,信中还附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我的差旅费。出发前往阳光明媚的那不勒斯时,这张支票使我对自己的不诚实心生歉疚。

那不勒斯动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