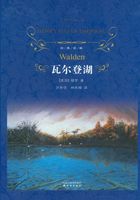
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目的
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某个阶段,习惯于把每个地点都视为可能安家落户的处所。我就这样把方圆十来英里内乡下地区的方方面面,都作了一番调查。我在想象中把所有的农庄接二连三地全都给买了下来,因为所有的农庄都得被买下来,而且我已知道它们的售价。我漫步走到各个农民的田地上,品尝他的野苹果,同他闲聊起庄稼,照他的开价买下他的田地,随便任何价钱,心里想反正可以抵押给他;甚至会出一笔更高的价钱;我把每件东西都买下来,就是没立契约——把他说的话当成契约,因为我非常喜欢谈天;我栽培了这片田地,同时,我相信,也在某种程度上栽培了他,我在尝够了欢乐之后便离开了,让他去继续耕耘下去。这段经历使我被朋友视为某种房地产经纪人。不管我坐在哪里,我都会在那里住下来,而风景也就由我而辐射出去。住宅不就是一个座位(sedes)吗?——如果是乡村里的座位那就更好。我发现许多可以营造住宅的地点短期内不大可能被改进,有些人会认为这里距离乡村太远,但在我看来,倒是乡村离它太远。好吧,我说,我可能在那里住下来;我的确在那儿住下了,一个小时,过了夏天和冬天的生活;看到我怎样让岁月流逝,把冬天打发走,迎来春天。这个地区未来的居民,不管把住宅建造在哪里,都可以相信有人比他们捷足先登了。只需一个下午就足以把一片土地设计成果园和牧场,决定哪几棵最好的橡树或松树宜留在门口,每一棵枯萎的树在什么地方可以有最好的效果;然后,我就让那片土地搁置在那里,也许可称之为休耕地,因为一个人的富裕程度如何,就看他能放得开多少东西。
我的想象力把我带得很远很远,我甚至得到了几个农场的优先取舍权——取舍权正是我所要的东西,但我从没有让实际占有这种事弄得苦恼不堪。我差一点做到实际占有是在我买到霍洛韦尔农场的那次,当时我已经着手挑选种子,捡起一些木料做独轮车,以便把这件事推下去或拉下去;可是,就在农场主交给我一份契约之前,他的妻子——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位妻子——改变了主意,想把农场保留下来,于是他赔我10美金,解除了约定。现在,说句实话,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角钱,我已算不清我究竟是身有一角钱的人,或者是拥有农场,或身有10元钱的人,或者是兼而有之的人。不过,我把10元钱退还给他,农场也物归原主,因为我已经走得够远了;或者说,是我做得宽宏大量,我把农场卖给他的价钱,正是我买农场的价钱,并且,由于他不是富人,我送给他10元钱,何况我还留下了一角钱,外加种子以及制造独轮车的材料。因此我觉得我始终是一个无损于自己贫穷本色的富人。不过我把风景保留了下来,从那时起我每年无需用独轮车便把美景所产生的果实带走。谈起风景,请看:
“我君临万象,风光尽收眼底,
不容置疑,我拥有一切权利。”
我时常看到,一个诗人在欣赏了农场上最珍贵的部分以后便离去,而那个粗鲁的农夫则认为他只不过拿到几个野苹果。哎,诗人把农场入诗,而农场的主人却经过了许多个年头还不知道。须知这诗歌是一道最美妙的无形篱笆,诗人把农场几乎全围起来,挤出它的奶汁,刮走它的奶油,得到了全部乳脂,留给农场主的只是脱脂奶。
在我看来,霍洛韦尔农场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远离市井,距乡村约两英里之遥,离最近的邻人也有半英里,并且有一片宽阔的田野把它和公路隔开;它位于河畔,据农场主说,河上起雾,使得农场春季时节不会霜冻,然而我对此无所谓;农舍和棚屋那灰蒙蒙的颜色,东歪西倒的景象,还有坍坏了的篱笆,在我与上一位居住者之间形成了一段间隔;让野兔子啃空了树心的、覆满地衣的苹果树,可以看出我得和什么样的邻居打交道;但最主要的是我早年溯河而上的那次旅游记忆犹新,当年屋舍掩在密密的枫林红叶中,我听到那深处传来了家犬的吠声。我急急忙忙要把这农场买下来,不能等业主把石头搬掉,把空心的苹果树砍倒,并掘掉一些生长在牧场上的白桦树幼苗,总而言之,做出进一步的改进措施。为了享受这些好处,我乐意把它扛起来;像阿特拉斯那个顶天巨神一样,让我肩扛天宇——我没有听说过他为此得到什么补偿。除了能花一笔钱然后安安稳稳不受干扰地拥有这农场之外,我做所有这些事没有别的动机或借口;我始终认为,只要我能任这片地自由生长,那它一定能生产出我所需要的最丰富的庄稼。但后来的结果却如上所述。
那么,关于大规模从事农耕一事(我一直在培育着一座花园),我所能说的只是:我已经把种子准备好了。很多人都认为种子随着岁月而优化。时间会区分出良莠,我对此毫不怀疑;到了最后我要去种植时,我大概是不会失望的。但我想给我的同伴们交个底说:尽可能长久地自由自在地、不受束缚地生活。束缚在一个农场里,同关进县牢里并没有多大区别。
老加图所写的《农书》对我起了“栽培者”的作用,他说(不过我所见到的唯一译文简直是糟糕透了):“当你想要买下一个农场时,你得把它放在心上反复掂量,别贪得无厌地去购买;别怕花力气去看它,也不要以为到那边转一圈就够了。要是那片农场的确很好,那你越是常到那边就越喜欢它。”我想我是不会贪得无厌地去购买的,我会一趟又一趟地到那边转转,一辈子这样,死了就埋葬在那儿,这会使我最终获得更大的欣慰。
摆在面前要写的是我对这类事的下一次实验,我打算更加详细地加以描述;为了方便起见,我打算把两年的经验合并为一年。我已经说过,我无意歌颂垂头丧气,而要像雄鸡站在栖木上起劲地放声报晓,只要能把邻居唤醒就行。
当我首次定居于我的林中住所,也就是说,开始日夜都待在那里时,刚好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即1845年7月4日。这时我的屋子还没有竣工,无法过冬,只能供避雨之用,屋子尚未粉刷,也无烟囱,墙壁用的是饱经日晒雨淋而斑驳变色的粗木板,到处是大裂缝,一入夜屋子里就变得凉爽起来。削得笔直的白色立柱,还有刚刚刨平的门窗外框,使屋子看上去既清洁又通风,尤其是在早晨,屋子的木料饱含着露水,以至于我猜想,到了中午会有一种甜树脂渗出来。在我的想象中,这幢房子整天都多少仍保存着这种晨光熹微的特色,使我不禁想起前年我游览过的一座山上小屋。这是一幢没有粉刷的通风小屋,适于款待云游的神仙,也适于一位女神在里面轻曳罗裳。在我住所上空掠过的风,一如那股在山脊上横扫而过的风,响起了裂帛般的旋律,或者在人间响起了那种只应天上有的曲调。晨风永远吹拂,创造性的诗篇永不中断;但能够听见这种乐音的耳朵却不多。奥林匹斯山只不过是大地的外部,无处不有。
如果不把一条船计算在内,那么以前我所拥有的唯一房屋就是一顶帐篷,夏天我偶尔外出旅游时使用,这顶帐篷现在仍然卷着放在我的阁楼上;不过那条船在几经易手之后,已随时间之流并逝了。如今我拥有更坚固的蔽身之所,可以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定居落户已取得了一些进展。这幢房屋的框架,虽然包装得很单薄,却是一种在我周围的结晶形式,对营造者产生了影响作用。这令人想起画中的素描。我无需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屋子里的空气一样新鲜。我坐的地方与其说是在屋内,不如说是在门后,甚至大雨滂沱的天气也如此。哈利梵萨说:“鸟儿不到的住宅,就像不加作料的肉。” 那不是我的住宅,因为我发现自己突然与众鸟为邻;我用的办法不是把鸟儿关在笼中,而是自己住在一只靠近它们的笼子里。我不但和一些时常飞到花园和果园的鸟儿更加亲近,而且还和一些更具野性而扣人心弦的林中鸣禽接近起来,这类鸣禽从不(或极少)向村里人唱小夜曲——它们是林中画眉、韦氏鸫、猩红裸鼻雀、野雀、三声夜莺等等。
那不是我的住宅,因为我发现自己突然与众鸟为邻;我用的办法不是把鸟儿关在笼中,而是自己住在一只靠近它们的笼子里。我不但和一些时常飞到花园和果园的鸟儿更加亲近,而且还和一些更具野性而扣人心弦的林中鸣禽接近起来,这类鸣禽从不(或极少)向村里人唱小夜曲——它们是林中画眉、韦氏鸫、猩红裸鼻雀、野雀、三声夜莺等等。
我坐在一个小湖的岸边,大约在康科德村南面约一英里半的地方,地势比村子略高一点,就在市镇与林肯之间的一大片森林中间,在我们唯一闻名于世的战场“康科德战场”南面约2英里处;但我所处的地点是在林中极低的地方,所以半英里外那片和别处一样林木葱郁的对岸,就成了我最远的地平线。在头一个星期,不管什么时候我往湖上眺望,它就像是个高高悬挂在山边的冰川湖,底部比其他湖泊的水面高出很多。当太阳升起时,我看见它脱下了夜晚的雾衣,湖上轻柔的涟漪或波平如镜的湖面也逐渐地在各处显露出来,雾气就像幽灵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各个方向隐入森林,像一次夜间秘密集会散场那样。正是这露水白天还披在树上,像在山腰那样,比通常停留的时间更长。
8月一阵阵急雨轻扫,乍雨乍晴的天气,与这个小湖为邻最为珍贵。在这个季节里,完全风平浪静,但天空却乌云密布,下午才刚过半便已一派黄昏宁静的气氛,画眉在四周歌唱,隔岸相闻。这样的一个湖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平静了;湖上那片澄空变得不那么深远,乌云把它遮暗。波光潋艳的水面变成一个下界的天空,显得更加夺目。从一个不久前被砍掉林木的山顶附近,隔湖向南望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对岸的山峦间有一个开阔的缺口,两侧的山坡相向倾斜,使人觉得有一道溪流穿过郁郁葱葱的山涧,从那个方向流出,不过那边并没有溪流。我于是从近处的翠绿山峦之间或之上眺望天边的远山和更高的山峰,那些层峦染成了蔚蓝色。的确,我踮着脚便能望见西北角一些更加蔚蓝更加遥远的连绵山脉,苍天从自己的模子里印铸出来的那种纯蓝,还能瞥见乡村的一角。可是,换了个方向,甚至从同样的立足点,我却什么也看不见,看不透,因为四周的林木把我的视线挡住。附近有点活水是很惬人意的,水给土地以浮力,让它漂浮起来。甚至最小的一口井也有这样一个价值:你俯瞰井底时,发现大地并不是连成一片的陆地而像是孤立的岛屿。这一点很重要,正如井可冷藏黄油一样。当我从这个山峰眺望湖对面的萨德伯里草地时(在涨水期间,我觉得那片草地升高起来了,这大概是水气蒸腾的溪谷里海市蜃楼的感觉吧),它像是水盆里的一枚铜币,湖外的土地看上去成了一层薄薄的外壳,被这片小小的水面隔开并浮载起来,我这才注意到,我所住的这块地方原来只是一片干燥的土地。
尽管从我的门口望出去,视野更加狭小,但我丝毫没有拥挤或禁闭之感。这里有一片够大的牧场可供我的想象力驰骋。对面河岸顶上那片生长着低矮橡木的高原,向西部大草原和鞑靼干草原伸展开去,为所有流浪人家提供一片宽阔的活动空间。当达摩达拉的牛羊需要新的、更大的牧场时,他说:“世界上没有比自由地享受着广阔地平线的人更加幸福的了。”
地点与时间都转换了,我的居住更接近宇宙中最令我神往的那些地区和那些时代。我生活的地方遥远得有如天文学家每夜观测的许多天体。我们惯于想象那遥远的天边一角,在仙后座背后,远离喧闹与杂乱的世界,有一些令人格外心旷神怡的地方。我发现我的房屋实际上正好位于宇宙间这么一块偏僻但却终古常新、不受玷污的地方。要是住在靠近昴宿星团或毕宿星团,靠近毕宿五或牵牛星的地方是值得的话,那么,我正好住在那里,距离那让我抛在后面的凡世生活一样遥远,发出一缕同样柔美的光线,朝着最靠近我的邻居闪烁,不过只有在月黑的夜晚他才能看见。这便是我所占据的宇宙中那个地方——
“有个牧人在那儿住过,
他的思想像高山巍峨,
山上放牧着他的羊群,
给他营养,时时刻刻。”
是他的羊群不断朝着比他的思想还要高的牧场上跑,那么我们对牧人的生活该作何感想呢?
每个早晨的降临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邀请,使我的生活变得和大自然本身同样朴素,也可以说,同样纯洁无瑕。我始终像希腊人那样,是曙光女神的真诚崇拜者。我很早起床,到湖里洗澡;这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我所做的最称心的事情之一。据说成汤王的浴盆上刻有大意如下的文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我能够理解个中道理。黎明带回了英雄时代。曙光初露,我敞开门窗坐着,一只蚊子穿过我的房间作一次看不见也无法想象的旅行,发出了微弱的嗡嗡声,这声音对我的影响,一如我听到号角昂扬、歌颂英雄的美名时那样。这是荷马的安魂曲;它本身就是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唱出了自己的愤怒与漂泊。这里有着一种宇宙为怀之感,是在宣扬世界上活力长存、生生不息,直至被禁止时为止。早晨是一天中最难忘的时刻,是觉醒的时光。此时此刻我们最少睡意;至少有一个小时,我们身体的某个部分从整天整夜的沉睡状态中清醒过来了。是被自己的天赋之资唤醒,而不是被一个仆从机械地轻轻推醒,是被我们自己内心重新获得的力量和渴望所唤醒,伴随的不是工厂的门铃,而是天籁回荡的乐调,还有扑鼻的芬芳——要是我们从睡眠中清醒过来时没有像这样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生活境界,那么这个白天,如果可称之为白天的话,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就这样,黑暗结出了它的果实,证明它本身是好的,不比白昼差。一个人如不相信每天都包含着一个没有被他亵渎过的更新、更神圣的曙光时辰,那么他对生活已告绝望,正在走一条黑暗的下坡路。感官生活部分地停止了一阵之后,人的心灵,更确切点说,是心灵的器官,每天都重新恢复元气,他的天赋之资也再度试图实现它可能创造的崇高生活。我应该说,一切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都发生在早晨的时间和早晨的氛围里。《吠陀经》说:“一切知,俱于黎明中醒。”诗歌和艺术,以及人类最美好最令人难忘的行为,都始于这个时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一如门农那样,都是曙光女神之子,在日出时弹奏出他们的乐音。对一个思想敏捷活跃,与朝阳同步的人来说,白昼是一个长长的早晨。不在乎时钟怎样鸣,也不在乎人们态度如何或干的什么活。早晨就是我清醒过来心中有一片黎明的时刻。精神上的改革就是力图驱散睡意。要是人们不曾一直处在沉睡之中,又为什么会把他们的白昼说得那么乏味呢?他们并不是一些很差劲,不懂得琢磨的人。要不是让睡眠弄得昏昏沉沉,他们应能做出一番事业。几百万人清醒到可以从事体力劳动;但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清醒到足以从事有效的智力活动,而一亿人中只有一人清醒到投入诗歌或神圣的生活。清醒即活着。至今我还未见到过一个十分清醒的人。所以我又怎能面对面直视着他呢?
我能够理解个中道理。黎明带回了英雄时代。曙光初露,我敞开门窗坐着,一只蚊子穿过我的房间作一次看不见也无法想象的旅行,发出了微弱的嗡嗡声,这声音对我的影响,一如我听到号角昂扬、歌颂英雄的美名时那样。这是荷马的安魂曲;它本身就是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唱出了自己的愤怒与漂泊。这里有着一种宇宙为怀之感,是在宣扬世界上活力长存、生生不息,直至被禁止时为止。早晨是一天中最难忘的时刻,是觉醒的时光。此时此刻我们最少睡意;至少有一个小时,我们身体的某个部分从整天整夜的沉睡状态中清醒过来了。是被自己的天赋之资唤醒,而不是被一个仆从机械地轻轻推醒,是被我们自己内心重新获得的力量和渴望所唤醒,伴随的不是工厂的门铃,而是天籁回荡的乐调,还有扑鼻的芬芳——要是我们从睡眠中清醒过来时没有像这样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生活境界,那么这个白天,如果可称之为白天的话,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就这样,黑暗结出了它的果实,证明它本身是好的,不比白昼差。一个人如不相信每天都包含着一个没有被他亵渎过的更新、更神圣的曙光时辰,那么他对生活已告绝望,正在走一条黑暗的下坡路。感官生活部分地停止了一阵之后,人的心灵,更确切点说,是心灵的器官,每天都重新恢复元气,他的天赋之资也再度试图实现它可能创造的崇高生活。我应该说,一切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都发生在早晨的时间和早晨的氛围里。《吠陀经》说:“一切知,俱于黎明中醒。”诗歌和艺术,以及人类最美好最令人难忘的行为,都始于这个时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一如门农那样,都是曙光女神之子,在日出时弹奏出他们的乐音。对一个思想敏捷活跃,与朝阳同步的人来说,白昼是一个长长的早晨。不在乎时钟怎样鸣,也不在乎人们态度如何或干的什么活。早晨就是我清醒过来心中有一片黎明的时刻。精神上的改革就是力图驱散睡意。要是人们不曾一直处在沉睡之中,又为什么会把他们的白昼说得那么乏味呢?他们并不是一些很差劲,不懂得琢磨的人。要不是让睡眠弄得昏昏沉沉,他们应能做出一番事业。几百万人清醒到可以从事体力劳动;但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清醒到足以从事有效的智力活动,而一亿人中只有一人清醒到投入诗歌或神圣的生活。清醒即活着。至今我还未见到过一个十分清醒的人。所以我又怎能面对面直视着他呢?
我们一定要学会再觉醒,并保持清醒,办法不是靠机械的助力,而是寄无穷希望于黎明,因为黎明不会在我们熟睡中抛弃我们。人类毫无疑问有能力靠自觉的努力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世间最鼓舞人心的事实。能够画出一幅独特的画卷或刻出一件雕像,从而使一些事物为之美化,这多少总是一种收获;但更加辉煌的是雕刻出和画出那种气氛和环境本身,使我们得以透过它去看事物,在精神上我们可以做到这样。能对平日的质量施加影响,这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应磨炼自己,使他的生活,甚至生活的细节,经得起其最高尚最严苛时刻的审视。要是我们拒绝,更确切点说,耗费掉我们所得到的那点无价值的消息,那么,神谕必然会清楚地告知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我到林中去,是因为我希望过深思熟虑的生活,只是去面对生活中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能学到生活要教给我的东西,而不要等到我临死时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生活过。我不愿过着不是生活的生活,须知生活无限珍贵;我也不愿过消极顺从的生活,除非必须这样做不可。我要深入地生活,吸取生活中所有的精华,刚强地、像斯巴达人那样坚毅地,清除一切不成其为生活的东西,大刀阔斧加以扫荡,仔仔细细加以清理,把生活逼到一个角落去,将其置于最低的条件之中。要是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么,就把整个真正卑微的情况弄清楚并公诸于世;要是它是崇高的,那就去体验它,在我的下一次出行中作一个真正描述。因为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对于生活到底属于魔鬼还是属于上帝,还是摇摆不定,并且有些匆忙地下结论说:人类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并永远享受神赐”。
可是我们仍然生活得很卑微,像蚂蚁一样;尽管寓言说很久以前我们就被变成了人;可我们却像希腊神话中的小矮人一样,总是在和仙鹤战斗;这是错上加错,糟而又糟,而我们最美好的德性却带上了多余的、原来可以避免的一副可怜相。我们的生命在琐事中浪费掉。一个诚实的人需要计算的数字,无需比十个指头更多,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他可以加上十个脚趾,其余全可笼而统之。简单,简单,再简单!我说,你的事情要安排成二三件,而不是成百成千件;不是按百万计,而是按半打计算,账目可以记在你大拇指的指甲上。在这个惊涛骇浪的文明生活海洋里,一个人如果不想栽下去,沉入海底,以致永远无法入港的话,就必须靠精确的计算,把可能出现的乌云与风暴,流沙与一千零一件事故都估计进去,成功的人必然是一个精明的计算家。要简化,再简化。如有必要,就每天只吃一餐而不是三餐;不是一百道菜,而是五道菜;别的东西也按比例递减。我们的生活就像德意志联邦,是由众多小邦组成的,它的边界始终变动不定,所以连德国人也无法随时告诉你确切边界在哪里。这个国家本身,连同它所有那些所谓内部的改进设施(顺便说一句,那其实全是些徒有其表的装门面的东西),都是些不切实际的畸形发展的机构,到处乱糟糟地堆满家具,自作自受,由于奢侈和任意挥霍,缺乏深谋远虑和高尚的目标,一切都给破坏掉了,正如这片土地上百万户人家的情况一样。要对国家进行治疗,正如对各户人家进行治疗一样,只有厉行节约,实行严格的、比斯巴达人更为简朴的生活方式并提高生活目标。现在生活太放纵了。人们认为国家毋庸置疑必须拥有商业,把冰块出口,用电话通话,一小时跑30英里,无论他们自己是否这样做;可是我们到底应该生活得像狒狒还是像人却有点不那么确定。要是我们不做枕木,不锻造铁轨,日夜埋头工作,而是把时间花在修缮我们的生活上,借此改进生活,那么,还有谁去建筑铁路呢?要是铁路没有筑成,我们又怎能及时到达天堂呢?可是,如果我们待在家里,只管自己的事,那么又有谁需要铁路呢?不是我们在铁路上驱车,反而是铁路躺在我们身上。你可曾想过,铺在铁路下面的那些枕木是什么?每一根枕木就是人,爱尔兰人或北方佬。铁轨就放在他们身上,而上面又盖上了沙子,车辆就平稳地在他们身上奔驰而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就是熟睡的“枕木”。每隔数年,便有一批新的枕木安放下来,车辆又在上面奔驰;因此,要是有些人喜欢乘车在铁轨上奔驰,就会有另一些人很倒霉地被压过去。当他们从一个梦游的人,也即一根出轨的多余枕木上辗过去,并把他惊醒过来时,他们急刹住车,大喊大叫,好像这只不过是一次例外。我很高兴地获悉,每隔五英里便需要安排一批人来使枕木平平稳稳地像现在这样躺在床上,因为这表示,枕木有时也可能会起床站起来。
为什么我们要生活得这样急急忙忙,这么消耗生命?我们是下定决心要未饥先挨饿。人们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因此,他们今天缝上千针,就为免得明天缝上九针。至于工作,我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工作。我们都患有舞蹈病,无法保持头部静止不动。我只须拉几下教区钟楼的绳子,发出火警的信号,就是说,还没有让钟声长鸣,康科德郊区的农场上的任何一个人(尽管今天早上他多次借口说工作十分繁忙)——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妇女,我敢说,都会放下所有的工作,朝着钟声的方向跑去,这主要倒不是要去从火中救出财产,而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讲,要去观火,因为火既然烧起来了,而且事实明摆着,又不是我们放的火;——或者去看大家如何把火扑灭,要是做起来不费劲的话,也可帮上一把救救火;不错,甚至教堂本身失火也是这样。一个人饭后打了半小时的盹,当他醒过来时,便会抬起头来问道:“有什么新闻?”好像世界上其余的人都在为他放哨。有些人指示别人每半小时叫醒他一次,显然并没有别的原因;随后,为了报答人家,他们便谈起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梦。通宵睡眠之后,新闻成了早餐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请给我谈谈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新鲜事好吗?”——于是他在喝咖啡,吃面包卷时阅读新闻,知道当天早晨在瓦奇托河上有一个人眼睛给挖掉了,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自己就生活在世上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眼睛早已退化了。
至于我,我没有邮局也能照样过得好好的。我认为很少有重要消息要经由邮局去传递。严格地说,我一生中至多收到一两封值得付邮资的信——我几年前是这么说的。通常花费一便士的邮寄制度,是你通过邮局认真地向一个人出价一便士买他的思想,可他的思想却十有八九以玩笑的方式提供给你。我相信,我从未在报上读到一则值得注意的新闻。要是我们读到的就是一个人被抢、被杀或因意外事故丧命,或一幢房子烧了,一架飞机失事,一艘汽船被炸毁,一头牛在西部铁路上被车子辗过去,一只疯狗被打死,或者冬天来了一大群蝗虫——那就再也不需要读别的新闻了。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熟识了原则,又何必去关心各种各样的实例及其应用呢?对一位哲学家来说,所有所谓新闻,无非就是些说长道短的东西,而编辑和阅读它们的人,则都是些正在喝茶的老太婆。可是,不少人却对这类闲扯听得津津有味。我听说,前几天突然有一大群人蜂拥前往报社,想了解最新的外国新闻,竟把该机构的几大块厚玻璃板给挤碎了——我认真地在想,这种新闻,一个头脑灵敏的人在12个月或者12年之前便可相当准确地先写了下来。以西班牙为例,如果你懂得把唐卡洛斯和公主、唐佩德罗和塞维利亚以及格拉纳达等字眼搬来搬去,不时调动,只要摆得恰当就行——自从我读报至今,这些字眼可能有点小变动;当其他可供消遣的新闻找不到时,便把斗牛端上来,包您准确,它让我们了解到的西班牙的现状或衰败情形,一如从那些最简明的西班牙报道中得到的概念一样。至于英国,几乎可以说,来自那个地区的最重要的新闻片断就是1649年的革命。如果你已知道英国谷物每年平均产量的历史,那你就不再需要去注意这件事了,除非你所做的纯粹是与金钱相关的投机买卖。要是一个很少读报的人能作出判断,那么,外国其实未曾发生过什么新的事,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什么新闻!懂得什么永不衰老,这要重要得多!“蘧伯玉(卫大夫)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在周末的休息日里(因为星期天是过得很窝囊的一周的适当结尾,而不是另一周的焕然一新的勇敢开端),牧师不应用另一套又长又臭的说教来在昏昏欲睡的农民耳边唠叨,而应用雷霆般喊叫道:“停!停下!为什么表面上很快,实际上慢得要命?”
在周末的休息日里(因为星期天是过得很窝囊的一周的适当结尾,而不是另一周的焕然一新的勇敢开端),牧师不应用另一套又长又臭的说教来在昏昏欲睡的农民耳边唠叨,而应用雷霆般喊叫道:“停!停下!为什么表面上很快,实际上慢得要命?”
虚假和欺骗被奉为最可靠的真理,而真实却被视为谎言。要是人们注意到的始终只是真实的东西,不容许自己受骗,那么生活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类事比较起来,就像神话故事和《天方夜谭》了。要是我们重视的只是那种不可避免的和有权存在的事物,那么音乐和诗歌就会沿街回荡起来。一旦我们不慌不忙而又智慧明达,我们就会领悟到,只有那些伟大而又有价值的东西才会永恒地真正存在下去——琐细的忧喜只不过是真相的阴影罢了。真相始终令人振奋而又崇高。人们由于闭上眼睛打瞌睡,同意被表面现象欺骗,这才到处建立并巩固起他们的日常生活惯例,这种生活规律仍然是建立在纯粹的幻想基础之上的。小孩子在嬉戏中生活,比大人更清楚地辨认出生活的真正规律,而大人却无法生活得有意义,可他们还以为自己更加聪明,就凭有经验,也就是说,有失败。我曾经在一部印度书中读到:“有个王子,幼年时被逐出他的城市,由一个林区居民抚育,他就在这样的状况下长大成人,也以为自己属于那个和他生活在一起的野蛮种族。他父亲的一个大臣后来发现了他,透露了他的出身,于是角色的误认消除了,他知道自己是个王子。”印度哲学家接着说:“所以,灵魂寄托的环境使得它错认了自己的性格,直至一位圣师把真相透露出来为止。这之后,灵魂知道它自己是属于婆罗门。”我领悟到:我们这些新英格兰居民之所以过着这种卑贱的生活,是因为我们没有透过事物的表面看问题。我们以为事物一如其外貌。如果一个人穿过这座城市,并且只看见真相,那么,你想想看,“磨坊水坝”又会在哪里呢?如果他把在那里见到的真相给我们作一番描述,我们一定认不出他所描述的那个地方。你看看一个聚会所,或一座县政府大楼、一所监狱、一家店铺、一幢住宅,说出你见到的东西在真正的洞察之下是个什么样子,它们在你的描述中一定全都会分崩瓦解。人们尊崇渺茫的真理、体系之外的东西,在最遥远的星体背后,在亚当之前、人类灭绝之后。在永恒之中的确存在着真理和崇高的事物。但所有这些时间、地点和场合都存在于此时此地。上帝本身在此时此刻才至高无上,决不会随着时代的逝去而更加神圣。只有永远沐浴和沉浸于我们四周的现实之中,才能领会什么是崇高与宏伟。宇宙经常顺从地和我们的构想相适应;不管我们走得快还是慢,总是有条路为我们而铺设。就让我们毕生致力于构思设想之中吧。诗人或艺术家迄今尚未提出一个美好而崇高到无人能实现的设计——至少总有一些后代能够加以实现。
让我们像大自然那样从容不迫地度过每一天,不让任何一片落在铁轨上的坚果壳或蚊子翅膀把我们抛出轨道。让我们黎明即起,迅速吃顿早餐,平心静气,毫不心烦;任客人来来去去,任钟鸣孩子哭——下决心过好这一天。我们为什么要屈服,要随波逐流?让我们不要在那个位于子午线浅滩区被称为午餐的可怕急流与漩涡中被打翻、淹没。经受住这阵危险,你也就平安无事了,因为再往前去都是下山的路。不放松神经,带着清晨的活力,绕过它,转过头去,像尤利西斯抵御海妖那样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要是发动机发出了啸叫声,就让它去吼叫到喉痛声音嘶哑吧。要是钟鸣起来,为什么我们要跑呢?我们会想它像什么样的音乐。让我们自己平静下来,把我们的两只脚踩进那污泥般的意见、偏见、传统、错觉和表面现象中去,这个冲积层把地球全给蒙蔽住了,穿过巴黎和伦敦、穿过纽约、波士顿和康科德,穿过教会和国家,穿过诗歌、哲学和宗教,我们两只脚一直在踩着,直至踩到一片可称之为现实的坚硬的地面和岩石上,这时我们会说:就是这里,错不了。然后,由于有了这个支点,你可以在山洪、冰冻和火焰下面开始筑墙或建造一个国家,或安全地立起一根灯柱,也许可以安装一个测量器,不过不是水位测量标尺,而是真相测量器,使得未来的时代知道,虚假与表面现象的洪流有时竟积得如此之深。如果你直面事实,你会看到它两面都反射着阳光,看上去似乎是一把东方的曲剑,你会觉得那快意的锋芒把你的心脏和骨髓都给劈开,这样你就可以愉快地结束你的有生之年。不论生还是死,我们需要的只是真实。要是的确快要死了,就让我们听到喉咙里发出来的格格声,四肢也感到冰冷;要是活着,就让我们去干自己的事。
时间无非就是供我垂钓的河流。我饮着河水,但当我喝水的时候我看见河底的沙,发现河流是多么浅。它那薄薄的流水逝去不复还,可是永恒却留了下来。我要更痛饮一番;到空中去钓鱼吧,天上的河底到处嵌着卵石般的星星。我一个也数不出来。我不懂得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我始终引以为憾的是我的智慧还不如出生之日。智力是利器,它能洞彻事物的奥秘。我不希望手头的活计超过必需的程度。我的头脑就是手和足。我感到我所有的才能全都集中在头脑之中。天性让我懂得,我的头脑是深入发掘奥秘的器官,正如某些动物运用它们的口鼻和前爪那样,我将用头脑在山中挖掘和开辟出我的道路。我认为最丰富的矿脉就在这附近。因此,靠着这根魔杖和升起的薄雾,我便能作出判断;我要在这里开始进行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