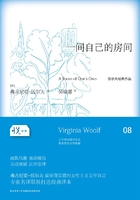
第4章 选篇二(2)
至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将几位年轻作家所共有的品质说明白,说明他们的作品与前辈们的相比,何以会如此不同。而詹姆斯·乔伊斯[13]先生,又可以算得上这些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力求更加接近生活,更真诚也更准确地将吸引他们、感动他们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甚至不惜将连小说家通常所奉行的传统也大都弃之不顾。让我们将那些落在心灵上的原子如实记下,依照它们纷纷落下的顺序,依照它们留给心灵的模样,每种情形、每桩小事,也都原原本本地记下,且不管看上去是多么支离破碎、不相协调。切不可想当然地以为,通常所谓的大事较通常所谓的小事之中,会蕴含更为丰富而圆满的生活。无论是谁,但凡读过《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或是那部正在《小评论》上刊出,要有趣得多的作品——《尤利西斯》[14],都不免会大胆地提出诸如此类的理论,来揣测乔伊斯先生的意图。在我们而言,仅凭眼前这些未竟的章节就妄下结论,未免是有些冒昧,并无十足的把握。且不去管终篇之后的整体用意究竟为何,毋庸置疑的是,这是出于作者最大的诚意,而最终的结果,虽然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艰深难读、令人不快,但其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乔伊斯先生,与那几位被我们叫做物质主义者的作家正相反,他是精神主义的。他不惜一切,也要将我们心灵深处闪烁的火光呈现出来,无数的信息都借由这团从我们心底燃起的火焰,在我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为了能将这火光保存下来,乔伊斯先生鼓足了勇气,只要在他看来是属于外部世界的,不管那是能添上几分真实,还是可以增加些连贯,或是诸如此类,曾让一代一代的读者在他看不到、摸不着、需要发挥想象力之时,辨明了方向的航标,都被他一概抛弃。譬如,在公墓内的那个场景,如此光芒四射又粗陋不堪,看似语无伦次,但在电光火石的一闪中,又是如此意味深长。毫无疑问,这正接近了心灵的本质。不管怎样,初次读到这样的描写,很难让人不为这样一部杰作而喝彩。如果我们想得到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么这确实就是它了。倘若我们还想再说上几句,说一说如此新颖独到的作品为什么还是比不上《青春》[15]或是《卡斯特桥市长》[16],我们也会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之所以拿这两部作品来做比较,是因为必须和高明之作放在一起才知道短长,而之所以比不上,是因为作者的思想相较而言还略显贫乏。我们当然可以就这么说说便敷衍了事,但也还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下去,这就好比待在一个明亮却狭窄的房间里,让人只觉得门窗紧闭、空间局促,施展不开拳脚、没有行动的自由,我们是不是不应只归结为思想上受到了束缚,也要问一问是否也是因为方法造成了局限呢?是不是方法束住了创造力的手脚?是不是因为方法不当,我们才失去了欢乐,觉得心胸狭隘,只以自我为中心?尽管这个自我感觉敏锐,以至于浑身颤抖,可对于超出自身之外的世界,他却不理不睬,更不用说去描写刻画了。是不是出于教诲的目的,把重点放在了粗鄙下流的事情上,所以这才显得多了些锋芒、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还是仅仅因为但凡这样独辟蹊径的努力都更容易,尤其是在同时代的人眼里,挑得出缺点而非发现她的长处?不管怎样,置身事外而空谈“方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如果是作家,那么任何方法,只要可以用来表达我们所想要表达的东西,便都是对的;我们若是读者,那么只要可以让我们更为接近作者的意图也都不错。而这种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可以让我们更接近我们打算称之为生活的那样东西。打开《尤利西斯》不是才让人明白,原来生活中有那么多东西一直被排除在外、视而不见吗?而翻开《项狄传》[17],或者是《潘登尼斯》[18],不也是让人大吃一惊,并且心悦诚服,相信了生活尚有其他方面,而且还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不管怎样,小说家现在所要面对的问题,且要让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古已有之,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他要写的东西。他一定要有勇气大声宣布,现在他的兴趣已经不在“这儿”,而在“那儿”了:他的作品,必须完全来自“那儿”。对于现代人来说,“那儿”,也就是兴趣之所在,极为可能是在心灵的幽深昏暗之处。这么一来,重点便立刻落在了别处,落在了某些长久以来被忽视了的地方,那就有必要马上勾勒出这种新的形式来,虽然这对我们而言,尚且难以捉摸,而对于我们的前辈来说,就已经无法理解了。除了一个现代人,或者说,除了一个俄国人之外,就再没有人能体会得到契诃夫[19]在他的短篇小说《古塞夫》里所描写情形的趣味了。几个生了病的俄国士兵躺在船上被送回家乡。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零星的谈话和片断的思绪,然后其中一个死了,被抬了出去。谈话又继续了一阵,直到古塞夫自己也死了,看上去就“像一根胡萝卜或者白萝卜”,被扔下了海。小说的重心放在了让人出乎意料之处,以至于乍一看还以为根本就没有重心。而接下来,等到双眼渐渐适应了微弱的灯光,认出这间屋子里都放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才明白过来,这个故事是如此地完整,如此地意味深长,而契诃夫又是如此忠实于自己的眼界,他把自己看到的这个、那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凑在了一起,写出了一种新的东西。但却不能说,“这是幕喜剧”,或者“那是场悲剧”,因为短篇小说就我们的所学来说理应简练,还要有个结论,而我们并不能确定,这篇既不明确又不下任何结论的作品是否还应称之为短篇小说。
即使是对于现代英国小说最初步的评论,也很难对俄国的影响避而不谈,但一谈到俄国人,就难免会让人觉得,写文章评论小说,而不谈他们的小说,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想对灵魂与内心有任何的了解,不从他们那里,又从哪里可以找得到如此深刻的描写呢?倘若我们对自己的物质主义心生腻烦,他们中哪怕是最不足道的小说家,也天生就对人类的精神怀着自然的崇敬。“学会让自己与人为亲……但莫让同情出自思考——因为思考同情自然简单——要让它发自内心,以爱待他们。”[20]似乎每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都让我们看到了圣徒的身影,如果说同情他人的疾苦、爱他们、努力去达到那值得心灵孜孜以求的目标便可以成就圣徒的话。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种品质,让我们深感自己由于缺乏信仰而浅薄无聊,也让我们的不少名著都成了华而不实、花哨的点缀。俄国人的心胸,如此宽广而富于同情,所以他们的结论,大概难免会走向莫大的悲伤。其实,我们大可以更确切地说,俄国人的心胸,并不适合得出结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没有答案。如果老老实实地观察人生,就会发现,生活的问题接二连三,在我们无望的追问中,直至故事结束,这些问题依然在我们心中回荡,并生出最后会让我们深恶痛疾的绝望来。或许他们是对的,毫无疑问他们看得比我们远,眼前也并没有我们那样重重的障碍。但或许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的东西,不然的话,何以他们抗议的声音能与我们的忧心忡忡相共鸣呢?这抗议的声音来自另一个古老的文明,看来它在我们身上培养出的,是享受和好斗的天性,而不是容忍和理解。英国的小说从斯特恩到梅瑞狄斯[21],都见证了我们生来便对幽默和喜剧、对山河的壮丽、对运用才智以及肉体之美情有独钟。而将这样两种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小说放在一起,想要比较出什么结果来,是徒劳无益的。只不过,他们的确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他们的观点:小说这一门艺术面对的是无限的可能,并且提醒了我们,世界是广袤无垠的,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尝试,哪怕是最疯狂的尝试——是被禁止的,除了虚情与假意。“小说的恰当题材”并不存在,每样东西都是小说的恰当题材,每一种感觉,每一个念头,我们头脑和心灵中的每一种品质,没有哪一种印象和知觉是不恰当的。而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小说的艺术活生生地站到了我们当中,那么不用说,她一定也会命令我们对她不仅要爱要敬仰,也同样要对她声色俱厉、拳脚相向,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会重焕青春、威仪永驻。
注释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10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标题略有不同。
[2]菲尔丁(Henry Fielding),18世纪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汤姆·琼斯》等。
[3]简·奥斯汀(Jane Austen),英国女性小说家,代表作有《傲慢与偏见》等。
[4]威尔斯(H.G.Wells),20世纪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尤以科幻小说闻名,代表作有《时间机器》等。
[5]贝内特(Arnold Bennett),20世纪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老妇谭》等。
[6]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20世纪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福尔赛世家》等。
[7]哈代(Thomas Hardy),英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德伯家的苔丝》等。
[8]康拉德(Joseph Conrad),波兰裔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黑暗深处》等。
[9]哈得孙(W.H.Hudson),英国自然学家、小说家,代表作有《绿舍》等。
[10]《老妇谭》,1908年出版,乔治·坎农、艾德文·克莱汉格均为贝内特小说《克莱汉格》三部曲中的人物。
[11]五镇,贝内特小说中的地名。
[12]琼和彼得,威尔斯小说《琼恩和彼得》中的人物。
[13]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爱尔兰小说家,代表作有《尤利西斯》等。
[14]《小评论》,美国杂志名。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的部分内容曾于1918年至1920年间在此刊陆续发表。其实,早在1918年4月,哈里特·韦弗(Harriet Weaver)就曾希望伍尔夫夫妇能在霍加斯出版社出版整本的《尤利西斯》,可惜出于一些法律和实际的原因,未能出版。
[15]《青春》是康拉德的短篇小说。
[16]《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的代表作之一。
[17]《项狄传》全名《特里斯特拉姆·项狄的生平与见解》,为英国小说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所著;
[18]《潘登尼斯》是英国小说家萨克雷(W.M.Thackeray)所著。
[19]契诃夫(Anton Chekov),俄国短篇小说家、戏剧家。代表作有《变色龙》《套中人》等。
[20]此段话引自短篇小说集《乡村牧师及其他》中的《乡村牧师》,作者艾琳娜·米丽什娜(Elena Militsina)。
[21]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9世纪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利己主义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