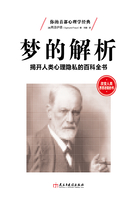
第13章 梦的素材与根源(2)
由于再讨论下去似乎与这梦的解析无甚联系,我们的分析工作就告一段落,不多细谈,我仅想在此指出我们演绎的过程是如此地由“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事实上,我与柯尼斯坦所谈的内容,在此我仅提出了某一部分而已,而再对这些谈话细细品味,才使我对这个梦的意义豁然开朗。我思路进行的全过程正如以下所列:“由我个人的喜好而至我妻子的喜好、古柯碱、接受医界同行的治疗导致的尴尬、我对学术专论的喜好、以及我对某些问题的忽视,就如植物学而言——这些再加上我当晚与柯尼斯坦的部分对话,由此,我们又再度证实了,梦是如此地为自我的理想与利益想尽办法(就如以前所分析过的伊玛的打针)。假如我们再就梦的论题继续推演下去,并将这两个梦作为参照,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讨论:一个与做梦者本身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常常一变就产生了确切的意义。现在这梦显示了这样的意义:“我曾经的确发表过许多(有关古柯碱)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就像我曾经表示的“自诩”:“我毕竟是一个工作勤奋、做事严谨的好学生”,而这两句话具有一个含意——“我的确值得如此自诩”。我之所以提到这梦,主要是要讨论梦是如何由前一天的活动所导致的,因此,以下不再对这梦作进一步解析。本来我认为梦的内容只与一种白天的印象有明显关系,但当我进行了以上的解析之后,我才发现另一个经验,也很显然地可以看作是这梦的第二个来源,而梦中所出现的第一个印象,反而往往无甚关系而为较次要的遭遇。“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这样的开头确实曾使我愣了一会儿,且那内容丝毫引不起我们任何兴趣,但第二个经验却具有着重大的心理价值——“我与挚友,一位眼科医师热心地讨论了个把钟头,而这话题使我俩很有感触,特别使我触动了一些久藏内心的回忆。而且,这对话又由于某位朋友的介入而中止”。现在,且让我们仔细比较这两件白天所发生的事,另外,它们与当晚所做的这个梦又有何关联呢?”
在梦的“显意”里,我发觉,它只不过提及了较无关系的昼间印象。因此,我能够这样重申:“梦的内容采用了那些无关大局的经历,相反地,一旦经过梦的解析之后,我们才能发现注意力所集中的就是最重要、最合理的核心经验。假如我的梦析确实是以梦的隐意沿着正确的方法所作出的研判,那么,我能够说,我无意间又获得了一大收获。我现在确信那些认为“梦只是白天生活琐碎经验的重现”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而我还必须驳斥那些认为“白天清醒时期的精神生活并不延续到梦中”的学说。还有,认为“梦是我们的精神能量对芝麻小事的浪费”也是不堪一击的邪说。与此恰恰相反,其实在白天最引起我们注意的印象,完全掌握住了我们当晚的梦思。而我们在梦中对这些事的关心,完全是提供了我们白天思考的资料。”
至于我梦见的为何总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印象,而对那些真正令我激动得足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印象,却反倒隐藏不见,我认为最好的解释方法,就是再运用“梦的改装”的现象中所提过的,心理力量中的“审查制度”来作一番阐释。有关那本樱草属学术专论的记忆,使我联想到与我朋友的谈话,如同我那病人的女友在梦中不能吃到晚餐,代表着熏鲑的暗示一样。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在“这本学术专论”与“和眼科医生朋友的对话”,这两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经历间,到底是用什么关系连在一起的?以“吃不成的晚餐”的梦而言,那两个印象间的关系却还瞧得出来,我那病人的女友最喜欢熏鲑,多少可由她女友的人格在她心中产生的反应而流露出蛛丝马迹。可是,在我们这个新例子里面,却是两个毫无关联的印象。第一眼看上去,除了说“那都是在同一天发生的经验”之外,确实找不出共同点。那本专论我是在早上看到的,而与朋友的对话是在当天晚上。而由分析所得的答案是这样的:“这两个印象的关系在于两者所含的‘意念内容’,而不是在于对印象的表面叙述。”在我分析的过程中,我曾经尤其地强调挑出那些连接的关键——某些别的外加的影响,通过L夫人的生日被遗忘,才致使关于十字花科的学术专论和我妻子最喜爱菊花一事扯上关系。但我不相信,仅仅这些鸡毛小事就能够引发一个梦。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所说的:“主啊!要告诉我们这些,并不一定要那些鬼魂由坟墓中跳出来!”还是让我们再自己往下看吧!在更加仔细地分析下,我看到那个打断我与柯尼斯坦谈话的,是Gartner(格尔特聂)的教授,而且Gartner这个德文词意即“园丁”。此外我当时曾恭维他太太的花容玉貌("Blooming" appearance)。确实,我现在已想起那天在我们的对话中,曾以一位叫做弗罗拉[8]的女病人作为主要话题,显然由这些关键把讳莫如深的植物学和当天另外发生的,真正比较有意义的兴奋印象联系起来了。此外还须提到某些关系的成立,比如,古柯碱的一段,就十分确切地把柯尼斯坦医师与我的植物学方面的学术论作联系在一起,也由此使这两个“意念的内容”熔于一体。因此,可以这么说,第一个经验实际上是用来引导出第二个经验的。
假如有人指责我这种解释是片面的武断臆测,甚至是故意编造出来的话,我是早作了心理准备的。假如“格尔特聂”教授花容玉貌的太太不出现的话,再假如我们所讨论的那女病人叫安娜,而并非弗罗拉的话,答案仍是可以找到的;假如这些念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的话,在别的方面或许还是能够有所发现的。实际上这类关系并不难找,就如我们平时常用以自娱的幽默问话或双关语一样,人类智慧的能量毕竟是无限的。更进一步说:当在同一天内发生的两个印象之中可找出一个能够利用的关系时,那么,这梦很有可能是循着另一途径形成的。或许在白天时另一些同样次要的印象涌上心头,只是当时被遗忘了,但其中某一个却在梦中取代了“学术专论”这一印象,而通过这个取代物才找出了与朋友对话的联系。因为在这个梦中,我们找不出比“学术专论”这个印象更恰当的可作为分析的关键,因此,很显然它是最适合此目的了。诚然,我们不必如拉辛[9]笔下“狡猾的小汉斯”一样诧异地发现:“原来只有世界上的富人才是非常有钱的!”
但是,依循我以上的说法,那些无甚紧要的经验,怎样在梦中代替对心理上更具重要性的经验,这一定很难被普通人所接受。所以,我会在此后各章再多找机会探讨,以期能使这一理论更为合理。可是就我个人而言,由无数的梦的解析所取得的经验令我确信,这种分析方法所获得的结果的确是有价值的。在一步紧接一步的解析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梦的形成曾经产生了“置换”现象——用心理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具有较弱潜能的意念,只有从最初具有比较强潜能的意念那里逐渐吸取能量,直至某种强度才能脱颖而出,浮现到意识界来。此种转移现象实际上在我们日常言行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一个孤独的老处女可能几近疯狂地喜爱某种动物,一个单身男子会变成一个热心的收集狂,一个老兵会因为保全一小块有色的布条——他的旗帜——而抛洒热血,深陷于爱情中的男女会由于握手稍久一点,而感到非常的兴奋,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仅仅由于丢了手帕而雷霆大发……这些都是足以令我们置信的心理转移的实例。但是,如果我们同样地用这种基本原则来证实自己的意念在意识界的浮现或抑压——也就是说,一切我们想到的事都得经过这种下意识的过程而产生的话,我想我们或多或少总会有种“果真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的思考过程也太不可思议、太不正常了”的想法;而且,如果我们在清醒状态下意识到这种心理过程,相信我们定会感到这些想法的荒谬,但之后逐渐地再经过一些讨论,我们就会发觉梦里所作的转移现象的心理运作过程,其实决不可能是不正常的程序,只是比一般较原始的正常性质略有个别不同罢了。
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梦之所以以这类芝麻小事作为内容,事实上说白了就是一种“梦的改装”经过了“转移作用”的表现。而且,我们也应该想到,梦之所以被改装是因为两种前述的心理步骤之中的审查制度所导致的,因此,不难预料到,经过梦之解析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梦切实有意义的来源,事实上是白天的那些经历,由此种记忆再将重点转移到某些看来无关紧要的记忆上。然而,这观点与罗伯特的理论刚好完全相反,但我确信,他的理论事实上对我们说来毫无价值可言,罗伯特所要解释的事实其实本来就不存在,他的假设完全是因不能从梦的“显意”看出内容的真正意义所引发的误解。对罗伯特的辩驳,我还有以下几句话:果真按照他所说的,“梦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不同寻常的精神活动,将白天记忆中的剩余残渣,在梦中逐个予以‘驱除’”,那么,我们的睡眠就显而易见地成了一件沉重的工作,而且,甚至还比我们清醒时的思考更加让人心烦。因为白昼十几个小时所留给我们的琐碎感受之多,不用说,即使你整个夜晚都在“驱除”它们,也是远远不够用的,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认为要忘掉这么多残渣式的印象,竟能一点也不消耗我们的精神能量。
再则,当我们要批驳罗伯特的理论时,仍存在着还须再探讨之处——我们始终未解释过当天乃至前一天的毫无关系的感受,竟会经常构成梦的内容。这种感受往往不能从一开始就与潜意识里的梦的真正来源找出联系,就上面所作的探讨,我们能够看得出梦是一步一步地朝着有意识的转移方向在蜕变,因此,要打开这种“最近但没有紧切关系的感受”及它的“真正来源”,只有期待某种关键性的发现。也就是说,这所谓无甚关系的感受仍必须具有某种合理的方面,不然,那就真的要像梦中运行那般漂浮不定,难以确定了。
或许用以下的经验能够给我们一些解释:假如一天当中发生了两件或两件以上能够导致我们的梦的经验时,梦就会将两件经验综合成一个完整经验:它永远遵循着这种“强制规则”,而把它们综合成一个整体。例如,在一个夏季的午后,我在火车上邂逅了两位朋友,但他们彼此间却并不相识。一位是十分得人心的同事,另一位则是我常去为他们看病的名门之后。我替他们双方作了介绍,但在旅途中,他们却一直只是分别与我攀谈而始终不能融洽相处,因此我不得不与这一位说这个,再与另一位谈那个,实在是吃力。记得当时,我曾对我那位同事提及请他为某位新进人物加以推荐。而那位同事却回答说,他是深信这位年轻人的能力的,只不过,这位新人的那副尊容实在难以得人器重。而我则附和他说:“也正是由于这点,我才会认为他最需要你的推荐。”没多久,我又与另一位聊了起来,我问到他叔母(一位我的病人的母亲)的健康近况,听说当时她由于极度虚弱而病死了,就在这旅程的夜晚,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我梦到那位我希望能够得到青睐的年轻人,正跻身于一间时髦的客厅内,与一大群有身份的大人物们亲密相处。之后,我得到消息说,当时正举行着我另一位旅伴的叔母的追悼仪式(在梦中这老妇人已死去,我必须承认,我始终就与这老妇人搞不好关系)。如此,我便将白昼的两个经验感受于梦中综合而构成一件单纯的经验。
鉴于无数次同样的经验,我将合理地推出一个原则——梦的形式受到某种强制规则的作用,将一切能够导致梦的刺激来源综合构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在我之前,像德拉格、德尔勃夫等人,也均说到过,梦是一种倾向,常把多种有兴致的印象浓缩为一个事件。在下面一章里(关于梦的功能),我们将要谈到,这种综合为一的强制规则,事实上是一种“原本精神步骤”的“凝缩作用”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须再考虑另一个问题:由解析所发现的这些导致梦的刺激根源,是否必定都是近期的(而且极有意义的)事件?或者是,就做梦者心理上来说,只要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一连串思绪,便能够不拘时限,只要一想到这事就足以引发梦的形成?通过无数次的解析经验,我所得出的结论是:梦的刺激根源,完全是一种主观心理的运作,根据当天的精神活动,将昔日的刺激变得像刚刚发生的那般新鲜。
现在,或许已到了我们该将梦的根源所运作的各种情况,进行系统化整理的时机了。
梦的根源包含:
(1)一种近期发生并且在心理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并非直接表现于梦中。例如,有关伊玛打针的梦,以及把我的朋友当成我叔叔的梦。
(2)若干个近期发生并且具有意义的事实,在梦中综合成一个整体。例如,把那年轻医生和老妇人的丧事追悼仪式合在一起的梦。
(3)一个或数个近期发生且具有意义的事件,在梦中以一个同时发生的无关紧要的印象来表现。例如,有关植物专论的梦。
(4)一个对做梦者本身十分具有意义的经验(经过回忆及一连串的思绪),却经常在梦中以别的近期发生却无甚关系的印象作为其表现内容。(在一切我分析过的病人里,以这一类的梦为最多。)